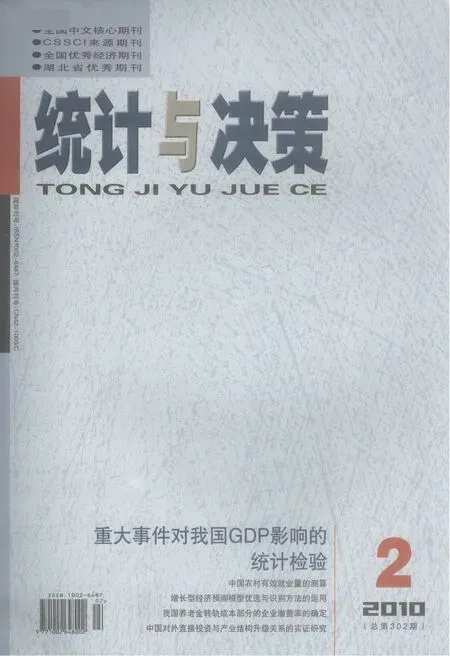我國養老金轉軌成本部分的企業繳費率的確定
唐遠志,馬力佳
(1.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信息中心,北京 100716;2.中國石油陜西銷售公司,西安 710049)
0 引言
1997年我國出臺的 《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明確了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向,開始了從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的轉變。但是在改革后的近十年內,全國企業養老金的繳費情況卻不容樂觀,1998年全國企業累計欠繳基本養老保險費 318億元,1999年達 388億元,2000年 6月底達414億元,到2003年6月共計欠繳436億元,欠費企業達到30萬戶,欠費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企業達到200多家[1]。
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之一就是企業的繳費負擔比例設計不合理[2]。養老保險改革后,我國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包含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兩部分,其中社會統籌可分為三部分:“新人”的基本養老金,“中人”的基本養老金和過渡性養老金,以及“老人”的全額養老金。這三部分中,除了“新人”的基本養老金和“中人”的部分基本養老金之外,其余均可視為制度轉軌成本[3],即政府過去在現收現付制度下已經積累起來的養老金承諾[4]。理論上,轉軌成本應該由政府承擔,但是中國在進行養老金改革時,沒有采取專門方式進行處理,而是期冀通過加大企業統籌費率的方式逐步將其消化[5],即參保企業不僅要繳納基本養老金,還要承擔制度轉軌成本。由于承擔轉軌成本不是企業應盡的義務,因此企業會因繳費能力不足或抵觸等原因而欠繳。綜上所述,在充分考慮企業承受能力的基礎上,確定出企業可以接納的轉軌成本繳費率就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目前國內已有的繳費能力計算方法大致包括繳費率精算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養老金繳費率精算模型基本都是從既定替代率出發倒推進行繳費率的測算,沒有論證企業對該繳費率的承受能力;而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可以測算企業的最大繳費能力,但無法確定準確的繳費率。針對以上問題,本文將在企業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對轉軌成本繳費率進行準確計算(由于轉軌成本只是養老金體系中的一部分,因此不存在達到既定養老金替代率的前提要求)。
1 模型應用的理論基礎
1.1 基本養老金中轉軌成本部分的準公共產品屬性分析
從養老金的運行機制來看,養老金統籌部分的繳費來源于當期參保企業,參保企業將養老金統一上繳到相關部門,再由相關部門向參保企業的職工統一發放,這一現收現付的過程體現了養老金的“代際間互濟”,同時也體現了養老金對非勞動者俱樂部成員的排他性及其對內部成員的非排他性,即統籌部分養老金可以被界定為一種價格排他性的公共產品,或俱樂部產品[6];而轉軌成本作為統籌養老金的一部分,也相應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準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涉及提供和生產兩個環節,由于養老金是貨幣,不存在生產步驟,因此本文僅涉及公共產品的提供環節。準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包括私人、集團和政府,當企業是作為市場上分散的決策主體參與公共產品提供時,企業就是“私人”[7]。相應的,各參保企業在進行養老金繳費時就是分散的決策主體,因此本文認為在養老金繳費過程中,企業可以被界定為“私人”,即企業的養老保險繳費可以被認為是準公共產品的私人供給。
1.2 以企業繳費前利潤作為轉軌成本部分繳費基數的必要性
目前對于轉軌成本部分繳費基數的選擇有兩種思路,第一種思路默認轉軌成本的繳費基數就是當前我國政府規定的企業職工工資總額;另一種思路則認為轉軌成本的繳費基數應該是企業利潤[8]。本文認同第二種思路,認為養老金中的轉軌成本部分應以企業利潤為基數進行繳費(其它部分的繳費可以遵照國家既定方案不變),以企業繳費前利潤作為轉軌成本繳費基數有以下益處:(1)緩解政府和企業的利益沖突。(2)減少養老金的利益外溢。(3)體現企業之間的互濟性和公平性。
2 模型介紹
“公共產品私人聯合提供模型”是基于博弈方法的一種公共產品私人供給模型。與已有的模型相比,“公共產品私人聯合提供模型”充分考慮了企業的承受能力,通過供給的各個“私人”之間的博弈,在供給者自身效用最大的前提下,達到了一個基于財富的公共產品的最優供給率,在本文中即為以企業利潤為基數的轉軌成本繳費率,此時可以達到參保企業群體的帕累托最優和企業理性的統一[9],并且這個繳費率是企業可以承受的。
模型的具體推導過程如下[9]:假設需要某一公共產品的群體中有若干局中人(在此為養老金繳費企業①由于《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針對的是城鎮職工,因此下文中的企業均指城鎮企業,職工也均指城鎮職工。),其中某一個企業i的財富ωi(本文中為企業的繳費前利潤)分為兩部分:自己使用的財富部分其數額為yi(本文中為企業的繳費后利潤),愿意繳給公共產品的數額為Bi(本文中為企業的轉軌成本繳費),同時其所需要的公共產品的數量為X(本文中為養老金轉軌成本,即企業 “中人”的過渡性養老金和 “老人”的基本養老金,為了方便起見,下文簡稱為“養老金”),即每一個企業都提出一個數對(Bi,Xi)。并假設即使傾其所有,企業擁有公共產品也比沒有公共產品好。此時這個企業的效用函數表達式為ui(yi,X)。
由于公共產品而使企業i得到的效用為:

當效用最大時有:

為了計算方便,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數表達式的基礎上,我們將企業i的效用表達式記為

其中,αi為企業i自己使用的財富的效用彈性,在本文中為企業繳費后剩余利潤的效用彈性;βi為企業i公共產品的效用彈性,在本文中相應為養老金給企業帶來的好處的效用彈性(養老保險的提供和使用現狀是“企業繳費,職工享受”,養老金使職工老有所養,所以職工愿意留在企業為企業創造產出,企業由此獲得了間接好處,文中β即指養老金為企業帶來的間接好處的效用彈性)。
當企業效用U最大時,由以上的推導可計算得出企業的公共產品繳費Bi:

即用“公共產品私人聯合提供模型”求出的是以企業繳費前利潤為基數的最優繳費率。
3 變量計算
3.1 β的計算
首先需要說明,由于本文不是針對某一個企業i,而是針對全國企業進行測算,因此以上所有變量均為全國企業的平均值。
由于養老金使職工老有所養,所以職工愿意留在企業為企業創造產出,企業因此獲得了間接好處。本文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采用“企業產出”和“資本要素投入”來衡量“養老金為企業帶來的好處”。
由于我國的養老金基本不存在投資收益,因此本文認為“全國職工所得的養老金”在數量上等于 “全國企業為養老金進行的繳費”加上“國家補貼”,而“國家補貼”不是公共產品,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所以本文用“全國企業的養老金繳費”和“全國企業產出”來衡量β。計算步驟如下: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

其中,A為系數;
Y為產出,本文界定為全國第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②由于本文僅涉及城鎮企業,而第一產業為農林牧副漁,多在農村地區,因此本文采用國內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之和,其間存在的誤差暫時忽略。;
L為勞動要素投入,本文界定為全國城鎮職工工資,城鎮企業養老金繳費與其它社會保障繳費總額;
K為資本要素投入,本文界定為全國城鎮投資總額;
a為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
b為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
目前我國企業平均養老保險繳費是以職工工資總額為繳費基數,因此若假設養老金繳費為C,則職工工資總額可以表示為t1C(t1>1);并且由于其它社會保障繳費也是以職工工資總額為繳費基數,因此其它社會保障繳費和養老金繳費也可以相互換算,即其它社會保障繳費可以表示為t2C,代入公式(4)可得:

養老保險的效用彈性β的值即為這個公式中Y對C的彈性系數。按照彈性系數公式β=(?Y/?C)(C/Y),我們可以求得β=a,因此我們需要求a的值。
對公式(4)作對數變換,得 lnY=lnA+alnL+blnK,Y,L,K的值見表1。
應用SPSS對表1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到如下結果:

3.2 α的計算
經濟的穩步發展必須維持必要的資本積累,這是企業擴大再生產最基本的要求,我國企業的投資率大多維持在30~40%之間,也就是說,企業繳費后利潤被分為了兩部分:其中最少應有30%的部分轉化為資本進行投資[9],剩下的部分就作為“企業剩余利潤”留在企業。下面應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數計算企業繳費后利潤被分為兩部分后為企業帶來效用的彈性。具體表達式如下:

其中,d為投資的彈性系數;e為企業剩余利潤的彈性系數。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計算出企業投資K的彈性系數為d=0.237。由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效用目標比較唯一,就是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因此我們可以直接將“企業剩余利潤”和“企業效用”等同起來,即企業效用=企業剩余利潤,企業剩余利潤的效用彈性為1,即e=1。將d=0.237和e=1代入公式(6)得:


表1 全國統計數據 (億元)
企業繳費后剩余利潤y的效用彈性α的值即為這個公式中y對Uy的彈性系數。按照彈性系數計算公式可得α=(?Uy/?y)(y/Uy)=1.237。
3.3 B的計算
將 α=1.237,β=0.61 代入公式(3)得:

即以企業利潤為基數的轉軌成本繳費率約為企業繳費前利潤的33%。
4 結果分析
下面對上文計算出的轉軌成本繳費率和我國實際轉軌成本繳費率進行比較。由于轉軌成本繳費只是養老金繳費的一部分,因此企業的實際轉軌成本繳費率應小于企業的全部養老金繳費率,實際轉軌成本繳費率的計算方法如下:
轉軌成本繳費率=(轉軌成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收入)×養老金實際繳費率
而當前我國企業養老金平均繳費率約為職工工資總額的24%,因此有:
轉軌成本繳費率=(轉軌成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收入)×24%
王曉軍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我國的養老金轉軌成本實質上就是隱性債務,因為過去的現收現付制度存在隱性債務才使新建立的基金制度必須有償還這些債務的責任,并構成新制度建立必須支付的成本,盡管成本支出的模式可能有很大差別,但其在轉軌時的精算現值就是當時的隱性債務 (王曉軍,2002),并測算出我國現收現付制下債務的積累(見表 2)[10]。

表2 現收現付制下債務的積累 單位:億元
假設在1997至2050這55年之間我國逐步消化債務積累,則平均每年的轉軌成本繳費應為537462/55≈9772.4億元,則企業的轉軌成本繳費率計算結果見表3。

表3 我國實際轉軌成本部分的企業繳費率表
由表3我們可以看出,當前企業的轉軌成本繳費壓力非常巨大,尤其在1997至2000年時,養老金制度轉軌剛剛開始,繳費體制不夠健全,因此轉軌成本繳費率已高達企業無法承受的地步;從2001年開始,雖然繳費率逐漸趨于正常,但仍然過高。據測算,企業每銷售100元的產品,就會支付19.8元的職工工資G,并得到5.6元的利潤ω(穆懷中,劉鈞,2004)。由此可將本文的計算結果換算得出0.33ω≈0.093G,即本文計算的企業轉軌成本繳費率大約可換算為職工工資總額的9.3%。由此可見,本文計算出的繳費率遠遠低于現在實際的企業轉軌成本繳費率,這也反映了現在企業所承擔的轉軌成本繳費的沉重負擔。
綜上,政府應該將養老金制度轉軌成本進行分攤,通過其它途徑更好地解決轉軌成本問題。并且除了目前已有的懲治措施,政府還應對養老保險征繳制度(如激勵措施等)進行完善規劃。由于公共產品的消費者一般是分散的,消費者容易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因此除了單方面對企業采取措施,政府還應該為消費者(參加養老保險的職工)提供信息以及其它必要支持[11],使參保職工可以更好地為自己維權。
5 結論
當前基于工資的轉軌成本繳費沒有考慮企業盈利能力,導致企業繳費負擔過重和欠繳現象,引發了政府和企業的利益沖突、養老金利益外溢以及公平性缺失等問題,而以企業利潤作為轉軌成本的繳費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些問題。
本文從養老保險統籌部分的準公共產品屬性出發,充分考慮企業的承受能力,用“公共產品私人聯合提供模型”確定了占企業利潤33%的轉軌成本部分繳費率,并進行了結果分析,得出現行轉軌成本部分繳費率偏高的結論。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確定的占企業利潤33%的轉軌成本繳費率僅僅針對當前。隨著時間的推移,“中人”和“老人”的數量將逐年減少,制度轉軌成本也將相應遞減,故從長期角度看,轉軌成本繳費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應該考慮人口變化等因素對繳費率的影響。
[1]王芳.企業欠繳養老保險費現象成因剖析[J].經濟研究導刊,2006,(1).
[2]張立光,邱長溶.我國養老社會保險逃費行為的成因及對策研究[J].財貿經濟,2003,(9).
[3]黎民,馬立軍.“雙基數”征繳:統籌養老金籌措的新思路[J].中國軟科學,2004,(3).
[4]孫祁祥.“空賬”與轉軌成本——中國養老保險體制改革的效應分析[J].經濟研究,2001,(5).
[5]宋曉梧等.解決隱性債務問題,深化養老保險體制改革[J].中國經濟時報,2000,(5).
[6]席恒,劉德浩.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一個公司治理理論的分析框 架 [EB/OL].http://www.ccswf.org.tw/2005paper/annuity/xi.doc,2005-7-14.
[7]李成威.公共產品的需求與供給——評價與激勵[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
[8]陳武平.公共產品成本的一種分配機制及其實驗驗證[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1).
[9]劉鈞.社會保險繳費水平的確定:理論與實證分析[J].財經研究,2004,(2).
[10]王曉軍.對我國養老金制度債務水平的估計與預測[J].測預,2002,(1).
[11]卓成剛,曾偉.試論公共產品的市場供給方式[J].中國行政管理,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