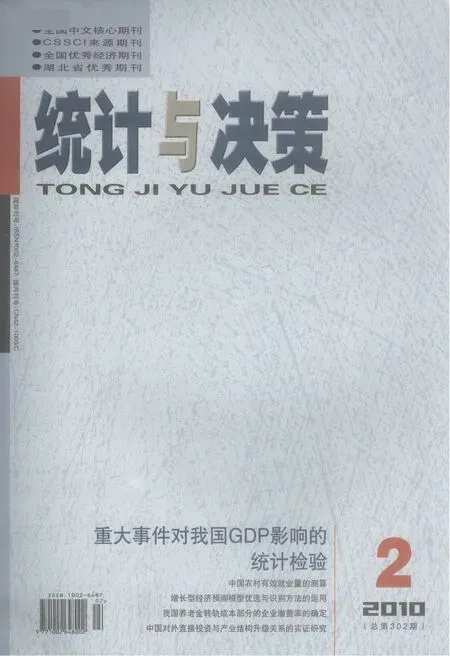西北地區與全國經濟差異的貨幣經濟因素的實證分析
宋翠玲
(1.蘇州大學 商學院,江蘇 鎮江 212013;2.江蘇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鎮江 212003)
我國西部地區與東部比較在改革以后經濟差距明顯呈擴大趨勢,區域間經濟發展嚴重失衡已經成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在當代,金融運行、金融支持已成為經濟增長與發展的不可忽視的推動力量,從金融理論的視角觀察西部經濟問題,麥金農所稱欠發達經濟體存在資本邊際收益遞增的投資與技術推動的效應似乎沒有發揮出來,這促使人們要從總體資本的規模、籌融資的管道、配置資金的主體探討西部金融問題,尋求約束西部經濟發展的貨幣經濟因素。[1]我們以西北作為重要個案分析西部與全國(也實際是與東部)經濟發展差距的形成因素,并特別關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情況。
1 研究方法及變量的選取
本文的分析同時采用Granger檢驗與多元回歸分析以增強實證研究結論的可信度,在兩種計量方法所抽象出來的結論之間進行比較,以Granger檢驗判明變量間因果關系,以多元回歸分析測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子大小。所選擇的金融變量與經濟總量指標分別為金融機構信貸規模和國內生產總值(GDP)。
(1)在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問題上,存在著兩種觀點:一種是“需求追隨論”,一種是“供給引導論”。帕特里克在他的著作《不發達國家中的經濟和金融發展》一文中首次提出這兩種理論。銀行信貸作為金融供給的一個標志,既可以是超前于經濟增長作為“第一推動力量”,也可能是由于適應已經實現的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需求產生的金融供給 “跟進”的一種被動式表現。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經濟發展產生對金融服務的“有效”需求,促進金融發展;另一方面,金融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促進經濟發展。然而,當經濟發展較為落后時,不能產生對金融服務的“有效”需求,不能促進金融發展;反過來,落后的金融服務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陷入惡性循環之中。我們的猜測是在西部存在金融抑制,金融機構信貸規模對經濟增長陷于不適的經濟狀態,即在時間繼起的結點上金融機構信貸落后于經濟增長,從統計分析上有可能經濟增長作為金融機構信貸提供的原因。當然,這一猜測有待驗證。
(2)金融機構信貸規模不僅可以作為金融部門供給行為的適當量度指標,也可以作為貨幣政策伸縮的主要標志。我國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為m1、m2、現金、貸款規模等一組指標,其中貸款規模一直是央行調控和監測的重點。[2]1993年我國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由貸款規模轉向貨幣供應量,但信貸總量仍然是重要指標。1993~1996年底,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是抑制通貨膨脹,調控方式以貸款限額為主。1998年央行取消對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限制,擴大公開市場業務操作,但當時的背景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經濟增長受到嚴重需求約束,出現貨幣與信貸緊縮,各國有銀行完不成信貸額度,央行信貸規模已失去了意義。2003年,貨幣供給增長超出目標區,貸款投放過渡集中于房地產、汽車等行業,貨幣管理當局事實上又恢復了信貸規模控制。
金融機構信貸也是我國20世紀80年代至今貨幣政策主要傳導渠道。在我國,利率市場化還帶有官定利率的烙印,有管理的人民幣匯率體系仍然主要釘住美元,再加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自由兌換,所以貨幣政策傳導的利率與匯率管道基本上不存在,股市規模雖然已經有所擴大,然而所謂的財富效應渠道影響仍然甚微。信貸融資依然是當前企業融資的主要途徑,2008年我國銀行貸款增加額為58358.64億元,上市公司境內市場籌資額為3396億元,僅占貸款余額的5.82%。1994年該比例為1.91%,2007年曾空前達到23.8%,后由于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該比例下降。不管怎樣,使用貸款規模比之m1、m2更能代表生產部門對貨幣資金的實際運作。
(3)對于在一國內部不同行業或經濟區范圍里使用GDP指標,一些學者已經提出質疑,原因有經濟和政治兩方面因素。但鑒于現有歷史數據中與全國GDP對應的各行政區經濟指標也使用了GDP,我們也只能使用現有標準的數據。
2 金融變量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主要分析時段切入點為1990年。考慮到進行因果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技術上的要求,盡管我國真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開始于1984年中央銀行的成立,但1978年以來貸款規模一直是國家調節經濟的重要手段,因此,序列數據選自1979~2007年度,通過延伸時間跨度增強樣本期間分析的可置信度。
2.1 Granger檢驗結果
表1中DK代表歷年金融機構的貸款規模,Y指國內生產總值,wn下標均指西北地區。貸款規模(DK、DKwn)和國內生產總值(Y、Ywn)均為名義值,各變量前加L表示各變量的自然對數值。由于Grange檢驗對分析中所用的滯后項數非常敏感,因此我們本著寧多勿少的原則,以AIC信息量為準則,選取2期滯后期,對貸款規模與經濟增長進行檢驗。由檢驗結果可知,全國貸款規模與國民經濟增長存在雙向因果關系,處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中。而在西北,經濟增長對貸款規模有明顯的影響,貸款規模則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即在時間繼起的結點上金融機構信貸落后于經濟增長,這實際上證實了我們的猜測,在西北地區存在著金融抑制。
2.2 多元回歸分析的模型設定及檢驗結果

表1 貸款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表2 貸款規模與經濟增長的多元回歸分析結果
為具體比較金融變量在西北地區和全國的影響效果,對金融機構的信貸規模與經濟增長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設定模型為:

模型的選擇以ACI信息標準為準則,式中馬爾可夫一階自回歸模式AR⑴和二階自回歸模式AR⑵用來消除自相關(采用最小二乘法)。回歸結果如下:
由表2回歸結果可看出,(1)兩個模型的F檢驗都通過,DW值都處于合理水平,調整后的R2顯示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很高。(2)西部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系數為0.358862,低于全國同一指標0.411429。(3)西北貸款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0.461987,全國貸款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0.424010,相比之下,西北地區貸款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地強于全國。
3 對檢驗結果的經濟解釋
3.1 西北地區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弱于全國
原因主要在于:(1)西北地區市場化進展緩慢,企業自籌資金能力低,固定資產投資中國家投資占有較大比重。1990年以來,西北投資中來源于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例一直高于全國;(2)由于財政投資及國債投資集中于基礎設施、生態環境改造等非運營項目領域,表現為西北地區基本建設比例遠遠高于全國同一水平,就必然導致西北地區投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因子低于全國;也可能是政府投資的前、后向關聯效應較低,政府投資改善了基礎設施等硬環境,但促進市場化改革的政策體系創新跟不上,面向私人投資的公共服務體系不健全,商業銀行體系的金融供給不足;(3)西北地區產出構成中農業及工業初級產品占比較高,而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只能形成西北地區經濟發展中的“飛地”。[4]
3.2 西北地區貸款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地強于全國
這一結果并不能說明西部對銀行資金使用效率高于全國,只能說明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對金融機構貸款的依賴性強。原因是東部進而全國資金自給能力優于西部,區域資金自給能力直接決定了該地區的經濟活力和增長速度。區際優惠政策的實施及投融資體制的差異是區際資金自給能力差異的主因。
(1)優惠政策為區際間資本自我積累差異的重要啟動因素
優惠政策先行歷來是各國區域開放發展的重要啟動力,我國大多數改革政策及措施均在東部地區試驗先行。經濟特區均設在深圳、珠海、汕頭、海南等東部沿海城市,各類國家級開發區共360多個,沿海地區占85.3%,而西部地區只占6.2%。國家給予東部地區以稅收減免、減少財政上繳比例、擴大項目審批權和外匯審批權、外匯留成權,建立股票、證券市場等特殊政策待遇。根據地理區位優勢和世界經濟向亞太地區轉移的趨勢,優惠措施率先在東部地區實行無疑是明智之舉,但同時也使東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大大優于西部地區,吸引西北地區生產要素包括資金、人力資本等要素大量流入,加劇了西北地區資金不足的局面。這些優惠政策的推行,適應了當時東部地區面臨的宏觀經濟環境,與當地原有的商品經濟意識相契合,起到了加速東部市場化進程的催化劑作用。相反,西北地區恰恰就缺少這樣的“父愛”,在客觀上受到政策歧視。其結果促進了東部沿海省份資本積累和福利水平的提高,然而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區私人借方資本積累以及福利水平的提高都有很大局限。
(2)區際間投融資體制的差異
區際間資本市場發展程度進一步說明區際間投融資市場化程度的差異。我國股票市場發展迅速,但無論是籌資額還是上市公司數都呈現出明顯的向東部地區的傾斜。2005年,從股本結構看,在全國總股份數7649.61億中,西北五省總股份數286.86億,僅占3.75%(江蘇省總股份數為371.13億)。同年度,西北五省股東權益總額579.97億元,不及江蘇省一省的股東權益總額1078.96億元,占全國股東權益總額424708.5億元的0.1366%。到2007年底,從在我國股票市場上市的公司的地域分布看,在我國1550家上市公司中,西北五省只有99家,僅占全國總額的6.4286%,還不及江蘇一省的上市公司數目116家。
西北地區國家投資占有較大比重,資本市場發展程度弱于全國,說明了西北地區資本市場較不發達、融資較少的狀況。也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在我國由市場主導的資金流動主要流向東部地區,而由政府主導的資金流動主要向西部傾斜。
綜上所述,東部沿海地區在優惠政策下優先發展起來,提高了居民的福利水平,市場化的投融資體制和自我積累的提高相結合,區域資金自給能力直接決定了該地區的經濟活力。然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落后,后期的優惠政策實際限于步東部后塵,帶有政策補修和趨同情況,并未體現出實質性優惠,在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北地區私人借貸資本積累以及福利水平的提高都很局限,較低的自我積累及非市場化的投融資體制制約下,在帶動西部經濟發展方面所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在這一背景下,西北地區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正規金融機構。所以西北地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較大的影響。而在東部地區,區域自給能力高帶動經濟發展,因此在全國的模型中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小。
4 相關政策建議
西部經濟發展如離開金融發展和支持將是一種跛足的發展,西部市場體系如離開健全金融組織的活動將失去核心內容。[5]羅伯特·M·湯森德認為生產者、交易者之間的相互聯系與依賴程度或“內聯度”改變將產生人均收入與資產規模的協同效應。金融供給的增加將改變經濟體系中的 “內聯度”,其機制是通過擴展社會債權-債務關系和支付鏈。[6]統籌與協調區域經濟發展,必須對區域性金融貨幣政策做出安排。鑒于本文的分析,我們建議:借鑒經濟發達國家金融區域化政策,在統一的市場趨向和基本的政策框架下構建統籌、協調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區域化金融貨幣政策成為必然的路徑選擇。其具體構建需要從培育區域金融組織體系、實施差別化金融管理政策、構建區域金融市場和制定區域金融立法等方面入手。
[1][美]羅納德·I·麥金農.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M].上海:三聯出版社,1993.
[2]蘇亮瑜.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及盯住目標選擇[J].北京:金融研究,2000,(9).
[3]www.bjinfobank.com,《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2007.
[4]宋翠玲.對我國區際經濟與金融差距關聯性的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10).
[5]劉明,宋翠玲.信貸、投資與人均收入的非一致性變動[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4,(6).
[6][美]Robert·M·Townsend.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Activ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