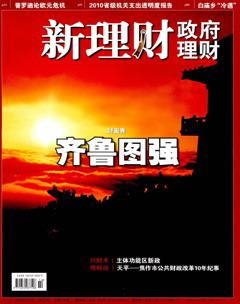江陰:“養”大社會財富
龔成鈺
江陰,一座位于長江邊的小縣城,如何能夠以全國萬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創造了全國百分之一的上市公司,二百五十分之一的GDP,三百分之一的財政收入、五十分之一的“中國500強企業”?連續七年蟬聯全國縣域經濟百強第一,江陰是如何開始財富積累得?什么樣的財政政策幫助江陰緊緊抓住了歷史契機,成就了當初這座小縣城的財富增長傳奇?
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后天積聚的濃郁的商業氣氛,最重要的是,江陰的原始財富積累還得得益于當時的財政部門吃透兩頭,制定了正確的財政政策,明晰自己的定位,及時轉換角色,推動了江陰的財富積聚。
財政比銀行還有錢
江陰的社會財富積累速度之快,至今都令很多地方的政府官員嘆為觀止,也自愧不如。顧金玉曾是這個傳奇的歷史見證人與參與者,他自1984年起就任職江陰財政局副局長、局長、地稅局局長,在財稅系統堅守了13年之久,經歷并親手推動過江陰的原始財富積累,對于江陰的生財之道他有著自己獨特而深刻的認知。
“江陰是一個完全依靠內生性的原始積累發展起來的地區,地域文化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顧金玉認為,“這跟江陰特殊的地理人文環境有著很大的關聯。” 江陰地處江尾海頭,長江咽喉,自古就是江防要塞、兵家必爭之地。盛唐時期,江陰更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埠。宋代政治家王安石當年巡視江陰黃田港時賦詩贊道:“黃田港口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賈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由此可知,江陰人長于經商之道,是頗有歷史淵源的。
顧金玉回憶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江陰就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地方,當時有四、五十家鄉鎮集體企業,但總量比較小,只有幾千萬的財政收入。但那幾年的經濟發展以每年20%的速度上升,在他退下來的1997年底,財政收入已經有十幾個億了。
可以說,江陰的快速發展得益于當時的財政政策。當時地方財政是大包干,企業交稅也是包干制,每年都有一個定額,根據國家下達的任務,企業承擔一定的任務指標。企業貸款也有財政信用擔保,只需要財政部門出一個貸款證明即可。
由于財政本身不借款,政府的負債自然也就不多,對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的投入壓力也不是很大。企業也主要由五大行業總公司調度,交稅都由各行業總公司負責,每年給企業下達指標任務。
財政當時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稅前還貸,企業借貸發展。年底除了給國家上交外,企業自已留足6%,剩下的全部用于償還銀行貸款,并在會計核算中直接計入生產成本。
1993年分稅制以后,江陰還延續包干制直到2000年。當時,顧金玉還兼任江陰地稅局局長,他說:“當時財政還有一個辦法就是自已放了很多小額貸款,我們當時有一千多萬財政資金,后來我們成立了一個內部銀行,每個科室都拿出一筆錢,在自已的系統里放貸款,從1992年開始的小打小鬧,到最后的運轉資本已經有了三個億。”
“我們那時候比銀行還有錢。” 言語間,顧金玉的臉上充滿了自豪感。
財富留在企業 財政不爭第一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緊跟國家形勢,采取了一些對自已發展有利的政策措施。我們過去講要吃透兩頭,一個是吃透上面的政策,一個是吃透下面的實情,根據這樣的情況才有了相應的對策。”顧金玉說。“我們采取了放水養‘錢的政策。財政的作用主要是調劑,保證完成國家的下達的任務,留足企業發展的資金。”顧金玉說。
“當時的政策相對比較寬松,我們采取‘放水養錢,把財富留在企業,財政不去拿企業的錢。比如,我們的江北靖江工業園區,財政2003年以來都沒有拿過園區一分錢,財政、稅務各個部門都在那邊成立辦事處,只搞服務不拿錢,園區今年的產值能達到28個億。”
“財富大部分都留在企業了,財政對這些企業的監管一個是按照國家的稅收上稅,一個就是各個行業公司的管理,財政對企業只進行審計。” 顧金玉回憶說:“我們以前的老書記經常講,別的部門可以得紅旗,你們財政不能得,如果得紅旗,我就給你們拔旗。他講上面是個無底洞,下面也是無底洞,老百姓對政府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就需要財政來進行合情合理的調劑。”
據稱,當時江陰的40多家企業主要以技術加工工業為主,化工、紡織、冶金三分天下。但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擴大規模,依靠傳統的放水養‘錢的政策,對企業而言已經是“小打小鬧”了,政府就開始鼓勵企業到資本市場去尋找更多的資金,并陸續將原有的鄉鎮集體企業全部改制為民營企業。
1997年2月,興澄股份作為首家上市公司在深交所上市以來,截至目前,江陰的上市公司已經達到了23家。上市公司數量和募集資金總量在全國縣級市中位居榜首,在國內資本市場中形成了備受矚目的“江陰板塊”。
可以說,深諳市場經營之道的江陰地方政府和企業家,共同謀劃了一場從產品經營到資本經營的跨越。企業也利用從資本市場募集的大量資金,加快了技術改造和產業結構升級,實現了超常規、裂變式發展。
江陰在起步階段通過放水養“錢”積累財富,再通過上市來籌集資金,并將地方資本放大得以快速的發展,是否能夠在國內后發展地區進行復制?顧金玉說:“江陰的發展方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可能簡單地復制。而對于后發展地區,一是上面的政策一定要寬,二是地方的發展要對路,三要逐步培育自已的資源優勢,包括人力資源。”
記者手記
民富才是真正的幸福
人類的文明史其實就是一個財富的原始積累過程。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的社會環境,還有特定的區域文化等因素,必然會催生出一些特定的事物來。
如今,當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在上世紀成功跨越了“畫地為牢”的計劃經濟時期,進入了一個開放的商品化市場經濟時代,這也意味著一個社會財富的原始積累過程的開始。而那些走在時代前面的先行者們,已然成為了現實社會中的富裕群體。
其中,必然也有很多令后來者詬病之處,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因噎廢食,去蕪存菁的有益借鑒,也能讓后來者不再去重復那些已經發生過的錯誤。
華夏A股第一縣、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第一名、江蘇省首批全面小康達標縣的諸多美譽,更有華夏第一村的華西村、中國百強村第三名的長江村等具有社會標桿意義的新型農村經濟體,令人嘆為觀止之余,不得不如此慨嘆:當地方政府改變了唯我的經濟增長觀,而將社會發展觀作為地方經濟持續發展的長遠謀劃,這里所發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
然而,富裕如此的江陰也不得不直面一個當下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如何更好地進行財富的公平分配?我們發現,江陰已經進入了一個難以避免的社會發展“瓶頸”階段:企業資產屬性理不清、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矛盾在不斷地聚集。
“華西村總體來講很富,但是錢并沒有到老百姓的手里,錢都在華西集團自已的小銀行里面,大家都感到很渺茫,沒有安全感,沒有歸屬感。”在我們的談話中,顧金玉如是說
如此,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也隨之產生:由個人集權控制下的集體財富積累方式,在某種意義上,對集體財富所有者之一的普通人是否意味著一種“掠奪”和“侵占”?
華西村的金塔頂端只站著一個人,長江村高聳的巨型石碑上也只有一個人的名字,一個人也只能證明一個個體存在的價值,當一群人無奈地被服從、被管理,他們存在的價值也只是增加了一個人的價值而已。
當財富積累完成之后,需要一個平等存在的個人價值之上的幸福感,村強民富只是一個被披上了幸福外衣的稱謂,真正的幸福,應該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滿足和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