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對(duì)待師生與權(quán)貴的不同面孔
○唐小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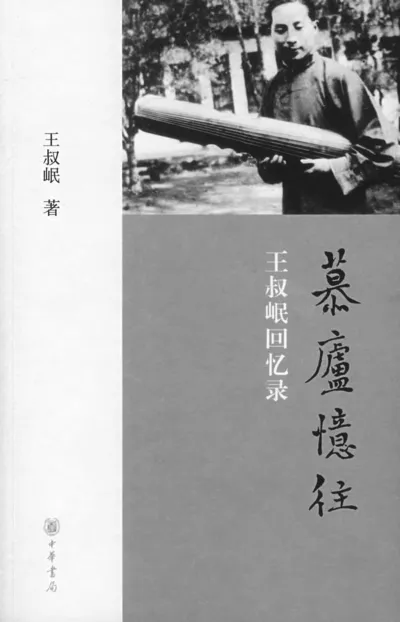
《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王叔岷著,中華書(shū)局2007年9月,32.00元
近日在長(zhǎng)沙一特價(jià)書(shū)店撿得中華書(shū)局版《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閑讀之際,對(duì)于莊子研究專(zhuān)家王叔岷記憶里的傅斯年形象尤感興味。
出生書(shū)香世家的王叔岷本來(lái)是文勝于質(zhì)的人,懷抱古琴,性喜詩(shī)詞,骨子里是浪漫主義詩(shī)人;若不是青年時(shí)代偶遇傅斯年而走向?qū)W術(shù)之途,也許其人生之路會(huì)是另一番風(fēng)景。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去世后,作為傅斯年入室弟子的王叔岷曾寫(xiě)下情深意篤的詩(shī)歌:“十年親炙副心期,孤島弦歌未忍離。點(diǎn)檢縹緗余慟在,千秋風(fēng)義憶吾師!”王叔岷先生坦承,自1941年進(jìn)入北京大學(xué)文科研究所(時(shí)因抗戰(zhàn)內(nèi)遷到長(zhǎng)江北岸四川省南溪縣李莊鎮(zhèn)),到1951年在臺(tái)灣大學(xué)中文系執(zhí)教的這10年,他在為人、處世、治學(xué)等方面均深受傅斯年先生的影響。
王叔岷與傅斯年初識(shí)于1941年的四川李莊鎮(zhèn)。當(dāng)時(shí)傅斯年任歷史語(yǔ)言研究所所長(zhǎng),而王叔岷剛剛被附屬于該所的北大文科研究所錄取為研究生。傅斯年常駐重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協(xié)助政府及教育學(xué)術(shù)界處理要?jiǎng)?wù),秋冬之際回李莊。王叔岷與傅斯年的第一次見(jiàn)面可以說(shuō)影響了其學(xué)術(shù)的取向:“我第一次見(jiàn)到傅先生,將寫(xiě)的詩(shī)文呈上,向他請(qǐng)教,他說(shuō)說(shuō)笑笑,學(xué)識(shí)之淵博,言談之風(fēng)趣,氣度之高昂,我震驚而敬慕;我奇怪,傅先生并不老,怎么頭發(fā)都花白了!(那時(shí)傅先生才46歲)既而傅先生問(wèn)我:‘你將研究何書(shū)?’答云:‘《莊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誦《齊物論》最后‘昔者莊周夢(mèng)為蝴蝶’章,一付怡然自得的樣子。傅先生忽又嚴(yán)肅地說(shuō):‘研究《莊子》當(dāng)從校勘訓(xùn)詁入手,才切實(shí)。’怎么研究空靈超脫的《莊子》,要從校勘訓(xùn)詁入手?我懷疑有這個(gè)必要嗎?傅先生繼續(xù)翻翻我寫(xiě)的詩(shī),又說(shuō):‘要把才子氣洗干凈,三年之內(nèi)不許發(fā)表文章。’我當(dāng)時(shí)很不自在,又無(wú)可奈何,既然來(lái)到研究所,只得決心下苦功,從基礎(chǔ)功夫研究《莊子》。”傅斯年閱人無(wú)數(shù),初次見(jiàn)面,就察覺(jué)到了王叔岷身上的才子氣,也就是孤芳自賞甚至恃才傲物的文人氣,文人之文與學(xué)者之文殊異,一生強(qiáng)調(diào)史學(xué)就是史料學(xué)的傅斯年自然不會(huì)讓自己的學(xué)生“誤入歧途”,因此對(duì)王叔岷來(lái)個(gè)當(dāng)頭棒喝,并且硬性規(guī)定其三年之內(nèi)不許發(fā)表文章(這其實(shí)是民國(guó)很多學(xué)者在指導(dǎo)學(xué)生時(shí)的行規(guī),流風(fēng)所及,遲至1980年代,老一代學(xué)者王瑤、馮契等一樣勸誡學(xué)生別急于出成果,要養(yǎng)浩然之氣),并給王開(kāi)出對(duì)癥下藥的處方,即坐冷板凳,從校勘訓(xùn)詁等樸學(xué)途徑入手研究莊子。王此前率性風(fēng)流,寫(xiě)詩(shī)填詞不亦樂(lè)乎,如今則在傅斯年規(guī)勸下別辟新途。從王叔岷后來(lái)治莊子的卓有所成,可見(jiàn)傅斯年的識(shí)人之慧。
抗戰(zhàn)結(jié)束,歷史語(yǔ)言研究所遷返南京,研究生畢業(yè)后留在史語(yǔ)所任助理研究員的王叔岷也就搬到南京的峨眉新村。胡適從駐美國(guó)大使卸任回國(guó)后,代理北京大學(xué)校長(zhǎng)一職的傅斯年也就回到南京指導(dǎo)史語(yǔ)所的學(xué)術(shù)工作。一天,傅斯年處理所務(wù)之暇,要王叔岷去討論其著作《莊子校釋》出版的問(wèn)題。傅斯年讓王叔岷將有重要?jiǎng)?chuàng)見(jiàn)的地方標(biāo)識(shí)出來(lái),閱讀之后頗為欣賞。傅斯年提出給王書(shū)寫(xiě)序。王叔岷回憶當(dāng)時(shí)的情景是:“我遲疑一下,說(shuō):‘不必。’隔幾天傅先生見(jiàn)到我,又說(shuō):‘我跟你寫(xiě)篇序,我跟你先商量如何寫(xiě)。’我依舊說(shuō):‘不必,我自己負(fù)責(zé)。’傅先生愛(ài)護(hù)學(xué)生,顧慮年輕人的著作無(wú)人注意,所以才一再說(shuō)跟我寫(xiě)序,我當(dāng)然感激之至。但是我想,一方面我的著作,好壞應(yīng)由自己負(fù)責(zé),不必要前輩夸贊;一方面《莊子校釋》是我第一部從事樸學(xué)的嘗試之作,萬(wàn)一錯(cuò)誤過(guò)多,豈不累及前輩。所以我不敢接受。”以“霸道”聞名學(xué)界的傅斯年激賞學(xué)生,并一再放低姿態(tài)愿為學(xué)生“做嫁衣裳”,居然被王叔岷這毛頭小伙一口拒絕。不過(guò)細(xì)細(xì)咀嚼王拒絕其師作序的理由,卻又不得不感慨民國(guó)時(shí)期學(xué)風(fēng)之清正。名家寫(xiě)序,錦上添花,正可迎合青年人內(nèi)心中熾熱的名望欲,但竟不被剛剛出道的王叔岷放在心上,看在眼里,其學(xué)術(shù)上的自主與風(fēng)骨可見(jiàn)一斑,或許也得自研究對(duì)象莊子的流風(fēng)余韻?而王叔岷文責(zé)自負(fù),擔(dān)憂(yōu)累及乃師的情懷,更讓我們慨嘆那時(shí)候師生之間至情至性的交誼。其時(shí)雖然西方大學(xué)制度引入中國(guó)已然半個(gè)世紀(jì),但在研究生(尤其是文史哲等傳統(tǒng)學(xué)科)培養(yǎng)方面,仍可窺見(jiàn)傳統(tǒng)書(shū)院師徒制之遺澤。更難得的是,兩次在學(xué)生那里碰冷釘子的傅斯年毫不為之掛懷,熱情推薦《莊子校釋》給上海商務(wù)印書(shū)館出版。
1949年,傅斯年隨蔣介石政權(quán)遷移到臺(tái)灣,并出任臺(tái)灣大學(xué)校長(zhǎng)。傅斯年從實(shí)際出發(fā),增建臨時(shí)教室及宿舍,聘請(qǐng)優(yōu)良教師,補(bǔ)充圖書(shū)儀器。校外有些人故意攻擊傅斯年,說(shuō)花了政府那么多錢(qián),表面看不出什么成績(jī)。當(dāng)時(shí)臺(tái)灣政壇的大佬陳誠(chéng)半開(kāi)玩笑向傅斯年說(shuō):“你也買(mǎi)點(diǎn)石灰,把臺(tái)大粉刷粉刷哩。”傅斯年笑著回答說(shuō):“還好,他們沒(méi)有攻擊我貪污。”據(jù)時(shí)任臺(tái)灣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的王叔岷回憶,當(dāng)時(shí)有些達(dá)官貴人并無(wú)學(xué)術(shù)成就,想進(jìn)臺(tái)大教書(shū),傅斯年立予拒絕。“有次沈剛伯(時(shí)任臺(tái)大文學(xué)院長(zhǎng))先生笑兮兮地跑回文學(xué)院,說(shuō):‘你們快去看!’原來(lái)傅先生正接見(jiàn)一位貴人,傅先生口銜煙斗,兩足放在辦公桌上,侃侃而談,那位貴人恭恭敬敬坐著在聽(tīng)。”學(xué)人在政客面前的風(fēng)骨由此可見(jiàn)。被稱(chēng)為傅大炮的傅斯年先生一生正直,抗戰(zhàn)后的《這個(gè)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kāi)不可》更是震驚時(shí)人,沒(méi)有這種風(fēng)骨與自主,學(xué)術(shù)便很可能被權(quán)力侵蝕甚至收編,這樣一來(lái),學(xué)術(shù)便無(wú)自由可言,學(xué)人更無(wú)自尊可言。這種風(fēng)骨,既可以理解是傳統(tǒng)士大夫精神的賡續(xù),也可以解讀成留學(xué)歐洲的傅斯年將西方知識(shí)傳統(tǒng)中的為學(xué)術(shù)而學(xué)術(shù)的獨(dú)立精神引入了華夏。更重要的是傅斯年在北京大學(xué)求學(xué)時(shí),正逢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鼎盛時(shí)期。那是一個(gè)依胡適所言“重新估定一切價(jià)值”的百家爭(zhēng)鳴時(shí)期,實(shí)驗(yàn)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師長(zhǎng)輩倡導(dǎo)的現(xiàn)代思潮給了傅斯年精神上的滋養(yǎng)。內(nèi)心世界的豐富,決定了個(gè)體的人格獨(dú)立性。相對(duì)于在權(quán)力面前的錚錚傲骨,傅斯年在師生面前卻是溫柔敦厚,見(jiàn)到教師非常親切,而“對(duì)學(xué)生最?lèi)?ài)護(hù),任何時(shí)間都可以接見(jiàn)”。
傅斯年骨子里是一個(gè)自由主義者,但其行事方式常涉嫌乾綱獨(dú)斷之“獨(dú)裁”,處事有擔(dān)當(dāng),也有魄力,這似是中國(guó)國(guó)情所決定;不過(guò),這種行事方式也招致諸多批評(píng),比如認(rèn)為傅斯年跋扈者不乏其人。與傅斯年情同父子的王叔岷卻不這樣看,他認(rèn)為:“表面上看來(lái)是跋扈,可是,傅先生的跋扈是為公,不是為私,是為人,不是為己。他舍己為人,不怕別人批評(píng),這點(diǎn)要弄清楚。”王叔岷所憶及的一件小事可資印證傅斯年的公私觀(guān)及其實(shí)踐。1950年代的臺(tái)灣大學(xué),只有校長(zhǎng)與總務(wù)長(zhǎng)才有汽車(chē),當(dāng)時(shí)傅斯年的太太在外文系教書(shū),到校及返家都搭公共汽車(chē)。總務(wù)長(zhǎng)太太去世后,追逐文學(xué)院一位護(hù)士小姐,假日載她外出兜風(fēng)。傅斯年知道了,警告他:“你要知道,汽油是人民的血汗!”正是在傅斯年的領(lǐng)導(dǎo)和影響下,篳路藍(lán)縷的臺(tái)灣大學(xué)校風(fēng)正氣盎然,聲望日益提升,學(xué)術(shù)水準(zhǔn)更是蒸蒸日上,成為延續(xù)20世紀(jì)二三十年代學(xué)術(shù)血脈之正統(tǒng)的高等學(xué)府,為臺(tái)灣的政治轉(zhuǎn)型、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學(xué)術(shù)繁榮培養(yǎng)了一大批人才。
王叔岷在傅斯年先生去世后所寫(xiě)的一篇哀悼短文中的一段話(huà)很精到地概括了傅斯年的人格與人生:“并世學(xué)有成者不乏其人,然多趨于鬻聲釣譽(yù),未必有骨氣也;有骨氣者,又多流于孤介冷辭,未必有魄力也;魄力、骨氣、治學(xué),三者兼?zhèn)洌湮┟险鎺熀酰 币詡鹘y(tǒng)之標(biāo)準(zhǔn),傅斯年先生一生在道德、學(xué)問(wèn)與事功三個(gè)領(lǐng)域都卓有成就,可謂后世學(xué)人難望其項(xiàng)背也。不過(guò)細(xì)細(xì)想來(lái),正如愛(ài)因斯坦在《悼念瑪麗·居里》文中所言:“第一流人物對(duì)于時(shí)代和歷史進(jìn)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zhì)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它們?nèi)Q于品格的程度,也遠(yuǎn)超過(guò)通常所認(rèn)為的那樣。”細(xì)繹傅斯年的一生,其獨(dú)立之人格、偉岸之精神也許相對(duì)其學(xué)術(shù)造詣和事業(yè)成就,更能在歷史長(zhǎng)河里熠熠生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