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眼看李白》:文化大散文的佳作
○郝 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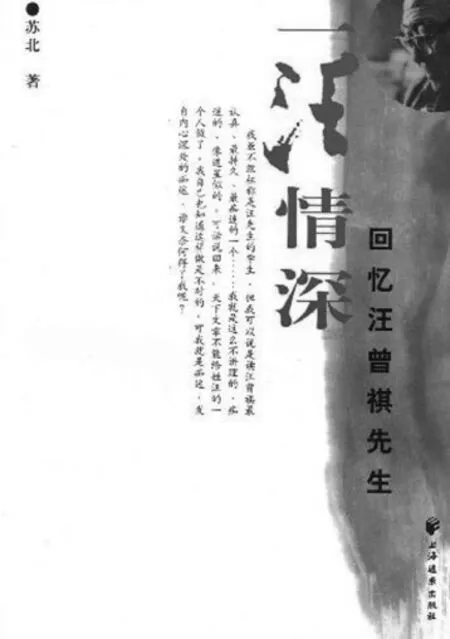
《一汪情深——回憶汪曾祺先生》,蘇北著,上海遠(yuǎn)東出版社2009年4月,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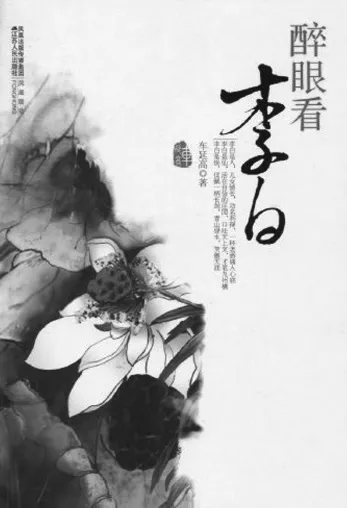
《醉眼看李白》,車延高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25.00元
文化散文在10年前曾一度盛行,后來就漸漸冷落。大致原因除了網(wǎng)絡(luò)以及新媒體的視像化閱讀沖擊之外,文化散文本身的創(chuàng)新力不足也是更為內(nèi)在的癥結(jié)。10年后的今天,文化大散文似乎又在開始聚集人氣。我的理由是兩本比較看好的書的出版:一本是蘇北為汪曾祺作的《一汪情深》,另一本就是2009年連載于《十月》、而今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車延高的《醉眼看李白》。
這兩本書的共同點(diǎn)是用散文的形式集中撰述一個文學(xué)人物,而明顯的區(qū)別是蘇北完全是紀(jì)實(shí)的,寫的都是汪曾祺真實(shí)的生活細(xì)節(jié);而車延高則更多是“醉眼”中的想象,筆端流出多是根據(jù)自己對于李白作品和有關(guān)資料以及傳聞的解讀,描述的是其內(nèi)心中的那個詩仙。車延高作為詩人(雖然他一直自稱為“業(yè)余詩人”,其實(shí)古往今來從沒有職業(yè)意義上的專業(yè)詩人),以其充沛的詩心,努力靠近那位千古詩仙的詩魂。文中許多對于李白的理解和闡釋,我以為都有相當(dāng)可延伸的思考性。車延高能夠把讀者的思緒調(diào)動起來,能夠讓讀者隨之而馳騁想象,去認(rèn)識一個也許很不一樣的李白,這就是這部文化散文的重要藝術(shù)價值。但由于作品大都是基于作者的想象,屬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所以,有時候就會讓人覺得一些情節(jié)和說法有主觀臆斷之嫌,于是就有學(xué)者和網(wǎng)友對其中的一些觀點(diǎn)產(chǎn)生了質(zhì)疑。我的看法是:對于這種文化散文,一定不能用學(xué)術(shù)考證的標(biāo)準(zhǔn)去要求和衡量。尤其是詩人對于相隔千年詩人的理解,或者詩人之間詩心的交流,怎么可能像學(xué)術(shù)論文或者考證史料那樣科學(xué)和嚴(yán)謹(jǐn)呢?10年前我就表達(dá)過這樣的觀點(diǎn):“如果一定要求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散文作品中沒有一點(diǎn)歷史的‘硬傷’,那么,你們專門研究歷史的專家們,對所有歷史的每一個細(xì)節(jié)都搞得那么一清二楚,沒有任何漏洞了嗎?”(文見《中華文學(xué)選刊》2000年第6期)當(dāng)然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不能過于主觀地歪曲歷史、臆造事實(shí),但是,“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李白”這樣的創(chuàng)造性解讀是應(yīng)該完全可理解的。況且,車延高散文中對詩仙李白的許多想象性追問和解答,我覺得都確實(shí)道出了我多年的疑問和心聲。比如李白多年仗劍去國四海漂流,那他究竟以何為生?這就曾經(jīng)是我讀了很多李白的詩和故事之后一直存疑的一個問題。車延高散文中對李白家鄉(xiāng)身世的分析我覺得起碼是有一定道理和根據(jù)的。至于詩人和其同代詩人賀知章、杜甫等人的關(guān)系,以及到底李白能不能“斗酒詩百篇”的問題,文學(xué)的解釋完全可以有文學(xué)的規(guī)則。車延高散文,起碼讓我們多出一些有意義的思路。
車延高如此解讀和闡釋李白,我以為也是最有資格的。這不僅由于車延高本人非常具有詩人的天分,而且更在于他的確有著與李白近似的詩人的氣質(zhì)、詩人的性格、詩人的骨頭、詩人的“魂”。車延高的散文中經(jīng)常打打詩人的“誑語”。如:“不幸之不幸,今天遇上我這三‘瓶’過后盡開顏的朦朧后生,有了七分醉壯膽,只剩三分醒看人,飄飄若仙時,讓高低貴賤、身份等級一并去了云水間,世間只有天空大,能在我眼珠里站住腳的人,越來越少,目空一切的我四大皆空。”嚴(yán)酷的現(xiàn)實(shí)之中,我們這些被各種各樣利害關(guān)系所套牢和壓抑著的人們,是多么缺少這種目空一切的狂妄精神啊!讀了這樣的文句,真的讓人感到渾身舒爽。
其實(shí),車延高寫李白,真的并不是為寫李白而寫李白,其中很多時候都是在以古喻今、借古諷今,文中很多地方也都充滿了批判現(xiàn)實(shí)的精神。他甚至經(jīng)常采用魯迅慣用的“順手一擊”的戰(zhàn)法。如:“但愿某些站在泥土地上,卻把自己看得比泥土厚重,功名路上只為功名,整日琢磨如何化繭為蝶,一路飆升的咄咄逼人的新霸主候選人們能夠明白:世上沒有絕對的‘頂峰’,無論是自己造勢,耍一些伎倆把自己裝扮成頂峰;還是把別人推上頂峰,又借推別人把自己帶上頂峰。結(jié)果都是孤家寡人,‘高處不勝寒’。看似得到,實(shí)為失去。從此成了被懸崖峭壁呵護(hù)的心尖子。恰如定于荷角上的一只蜻蜓標(biāo)本,盡管很精彩,很奪目,很詩情畫意,但它終是一種喪失了活力的景致,倘若舍不得在打碎中重組或重建,留給人間的只能是一種無生命活力的僵死和‘單調(diào)’之美。”這樣的段落,就不僅僅是尖銳批判,而且充滿深刻的哲理意味!
在如今人心普遍浮躁的氛圍中,讀讀這樣的散文,真可以讓我們的心靈有所清醒和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