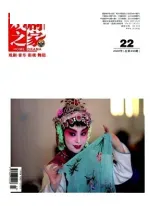也談“三種唱法說”
□牛俊霞
回顧我國的音樂領域,關于聲樂藝術的劃分方法,“三種唱法”——美聲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一直占天下獨尊的絕對權威地位。無論是在各種新聞媒體上,還是在各種演出、賽事中,也無論是業內的聲樂藝術家、聲樂理論家,還是業外的廣大觀眾或聽眾,更無論是專業的藝術表演團體,還是各類院校的聲樂系或專業,都一直使用著這一分法,并且習以為常、天經地義,很少有人對此提出過質疑。
然而,照我看來,這種分法并不科學,也不確切。從實質上說,并不是“唱法”,而是在風格基礎上形成的三大樂派。
如果從“唱法”上說,無論是美聲,還是民族、通俗,從總體上和實質上都是一致的,頂多是大同小異的。即都講究發聲、呼吸、共鳴、語言。僅從“唱法”上看,并無太大太多區別,只是發聲部位、共鳴調節、氣息控制略有差別而已,并不是各自本體屬性的差異。
從總體上說,美聲、民族、通俗的主要區別在于藝術風格,即美聲呈現音色優美、明亮、圓潤、豐滿,音與音的連接平滑勻凈,花腔裝飾樂句華麗靈活的藝術風格;民族聲樂呈現聲由情發、聲情并茂,以字行腔、字正腔圓,真聲為主、假聲為輔,清亮明晰、親切自然的藝術風格;通俗聲樂呈現追求自然樸實、動感隨意、載歌載舞、借助話筒的藝術風格。
而作為作家、藝術家在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創作個性與藝術特色的流派,主要是以不同的藝術風格來區分的,亦即相同的風格劃為一派。所以以筆者愚見,所謂“三種唱法”,并不是“唱法”,而是“三種流派”,即美聲樂派、民族樂派、通俗樂派。
就連我國的權威工具書《辭海》,也顯示出在這一問題上的自相矛盾之處:一方面,它沿用“三種唱法說”,將美聲樂派作為“美聲唱法”,列為詞條;另一方面,它又對這一詞條給出了這樣的釋義:“17、18 世紀形成于意大利的一種演唱風格……”(見《辭海》縮印本第2312 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年版)請問:到底是“唱法”還是“風格”?“唱法”怎么又是“風格”?這顯然陷入混亂之中。
細考“美聲唱法”的由來,并不源自意大利,都是我國翻譯惹的禍。所謂“美聲唱法”,并非原意,意大利語原詞是“Bell Canto”,Bell是美麗、美妙、美好之意;Canto是歌曲、歌唱之意,所以應譯成“美妙地歌唱”或“美麗的歌曲”,而與“唱法”毫不相干!硬譯成“美聲唱法”,不僅于理不通,曲解了意大利美聲樂派的原意,而且連累了我國的民族樂派與通俗樂派,都連帶成了不倫不類的“唱法”,真可謂貽害無窮!
其實,對于這種錯譯,我國的許多聲樂專家早就有所發現。著名聲樂藝術家與聲樂教育家郭淑珍在上世紀8 0年代就指出:演唱方法主要是一種生理機制,它雖然也包括一定的審美習慣在內,但用它來概括某一種民族的聲樂文化是過于狹隘的。“郭先生的這一觀點使我們想起了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的一句名言:文化解釋不應是生物解釋。……演唱方法,從某種程度上講永遠是一種暫時的方法,因為,無論什么唱法,它們所追求的科學的發聲原理是一致的。”(王次炤:《郭淑珍中國作品演唱和教學述評》,《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9 年第2 期第89 頁)尚家驤更直接指出:“Bell Canto這個意文詞的直譯應是‘美妙地歌唱’(兼有‘美麗的歌曲’的意思)在中國一直被譯作‘美聲唱法’。其實它不僅是一種發聲或歌唱的方法,而且還是一種歌唱的風格和流派。……其實譯成‘美聲唱法’不如譯成‘美聲學派’更為恰當,但‘美聲唱法’一詞在聲樂界久已流傳,故只得從俗,沿襲使用。”(《歐洲聲樂發展史》,香港上海書局出版)筆者贊成尚先生對“美聲唱法”錯譯的批評意見,也贊賞他所提出的“美聲學派”的藝術主張,但對于他的“只得從俗,沿襲使用”“美聲唱法”的觀點,實不敢茍同。在筆者看來,既然明知有錯,就應立即改正,而不應將錯就錯、以訛傳訛。
事實上也有人試圖予以改正,韓勛國在其編著的《歌唱教程》(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1 版)中就將“唱法”與“學派”合一,稱“美聲唱法流派”、“中國民族唱法學派”、“通俗歌曲演唱流派”。我認為這一折衷捏合的做法也并不可取,還是干脆徹底地將“三種唱法”改為“三種樂派”為好。筆者人微言輕,愿有關權威部門早日糾此錯誤,以利我國聲樂藝術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