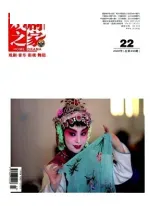舞蹈本性面面觀
□張志明
舞蹈就其本性而言,長于抒情而拙于敘事。舞蹈屬于動態的表現藝術,或者說屬于表情藝術。它擔負的使命不是摹擬(再現事物的外部特征),而是比擬(表現性格的內在實質);不是講述連貫、曲折的故事,而是通過某些“閃光點”塑造出鮮明的形象、抒發情感、烘托環境。舞蹈同樣要反映現實生活中的重大題材,但不能機械地照搬“真人真事”,而必須找到一個符合舞蹈藝術特性的“折射”角度。舞蹈不能直接表現“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崇高思想境界,但可以通過像《春蠶》這樣一個歌頌“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的精神的寓喻舞蹈,來對人們進行形象生動的思想教育。同樣,舞蹈無法(也不必要)編排說明月亮的自然屬性(大小、形狀、表面溫度等等)的舞蹈,但完全可以編出表現月光下人的感受——不同人在不同環境里從一輪明月得到的喜悅、惆悵、思鄉或在悲愴凄涼的心情的舞蹈節目。
對于舞蹈的抒情本質,古代已有探討。“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則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大序》)。這段話是大家都熟悉的,它說明古人懂得舞蹈發之內(有飽滿的激情),而形于外(找到完美的形式)的深刻道理。《樂紀》中“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的議論,進一步明確指出樂舞是從音樂得到啟發的,它的本源在于受到外界事物激發而生的思想感情。十八世紀法國著名舞蹈理論家諾維爾也發表過類似的意見:“要描繪的感情越強烈,就越難用語言來表達它,作為人類感情的頂峰的喊叫,也已顯得不夠,于是喊叫就被動作所取代。”
舞蹈沒有臺詞,抒發感情全靠人體的運動,即動作和姿態造型。為了淋漓盡致地表現主人公此時此地的內心體驗,編導要設計出典型的主題動作并由此出發進行變化。例如,傣族女子獨舞《水》的編導楊桂珍以傣族傳統孔雀舞步為基礎,把它放到原地快速旋轉中去做,表現少女在江邊洗發挽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個舞蹈樸素淡雅,但又充滿詩情畫意,沒有一句臺詞,但通過人體的運動,加上布景服裝的配合,我們可以確切地知道這是一位幸福地生活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傣族少女在盡情地抒懷。
采用比興、寓喻和聯想,也可以間接的方式表達作者的審美理想。賈作光在《海浪》這個舞蹈中,讓演員同時兼演海燕和海浪,時而海燕迎風展翅,勇敢地翱翔在洶涌起伏的海面上,時而又是海浪洶涌澎湃地向海燕撲來。演員身體的有節奏的、富有形式美的運動把這兩個形象展現得活靈活現,互相配合,構成了有機的整體。然而,編導的目的并不在于簡單摹擬海燕和海浪的外部特征,而是以海燕來襯托海浪的氣勢,努力使二者融合在海浪這一具體形象之中,表明“偉大的時代、偉大的祖國造就了這一代年輕人”這個哲理。編導依靠高超精湛的舞蹈形式,成功地表現了人的思想感情。
舞蹈沒有臺詞,乍看來似乎是個短處,其實不然,經過藝術家的精心設計,揚長避短。這個短處完全可以變成舞蹈藝術的一大特點。舞劇《天鵝湖》第二幕中王子與天鵝初次相遇時的一大段古典雙人舞細膩地通過舞蹈動作表現了奧杰塔從恐懼、提防、抵御到放心、信賴,繼而萌發愛情、靦腆含羞的復雜心理變化過程,其感染力大大勝于話劇的臺詞對白,稱得上“此時無聲勝有聲”。而這一切又都是通過不同節奏、不同力度、不同性格的人體動作姿態,特別是雙臂(翅膀)的變化多端的揮動和與之配合的頭部轉動來表現的。假如,把這一場戲改編成話劇,就會顯得蒼白無力,改編者只好另辟蹊徑來重新構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