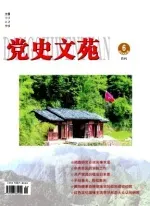金融危機導致美國話語失勢或霸權終結?
趙 斌
(湖北交通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9)
冷戰結束以來,關于美國單極時代的思考從未停止。2008年美國華爾街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大海嘯對美國這一極超帶來了全面的沖擊,亦再次讓美國霸權終結的話題擺置臺前。金融危機背景下,美國霸權是否真正走向歷史的終結,我們試圖從國際關系學界主流理論的反思中找到答案。
一、美國霸權論及其影響力控制力面臨的挑戰
談及國際政治中的霸權國,我們可以聯想到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描繪的雅典和斯巴達,也可以認為是17-18世紀號稱“日不落帝國”的不列顛英國,乃至我們更熱衷于討論的冷戰時期的美蘇,以及后冷戰時代的單極美國霸權。在國際關系研究上,一般人們講霸權時經常想到兩個例子,那就是19世紀的大英帝國及20世紀后半期以來的美國。講到這兩個霸權時,西方人愛用 “英國治下的和平”“美國治下的和平”兩個詞來形容。在這種霸權形勢下,那個惟一的超級大國經常覺得自己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決別國的問題,不與別國商量,起碼是不管別國愿不愿意。霸權國還為體系內的其他國家提供公共物品,這種公共物品即體系的穩定秩序。由于霸權國的存在,其他行為體(包括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都能享受到 “追隨”(或稱搭便車)的好處。因此,“霸權穩定論”一度甚囂塵上。“慈善的霸主”“仁慈的帝國”成了美國單極穩定論者的招牌口號。[1]
然而,在全球化時代,美國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面臨著全方位的挑戰。不論是盟國日本,還是被視作伙伴的歐盟,乃至一度被看成對手的俄羅斯與中國,都不同程度地被當成影響美國全球霸權之“非我”,從而逐漸社會化為美國政治精英和大眾的認知。庫普乾認為,美國時代行將終結,緣于統合中的歐洲作為歷史巨人的興起。[2]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著名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在其20世紀90年代末的力作《大棋局》中論述了關于在歐亞大陸防止一個反美同盟的出現。從其筆墨著力渲染的論斷來看,美國是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唯一的全球性霸權國。為了延續霸權地位,美國的目標自然是要在歐亞大棋局上防止一個反美聯盟的出現。冷戰后帝國式的俄羅斯和大中華的聯盟將可能是美國未來的主要敵手。[3]另外,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在其《大國的興衰》中預測美國霸權即將終結,其原因在于美國的過度擴張。[4]因此,美國霸權的終結論一度成為學界、政界、商界的熱議話題。
二、從話語霸權的主流理論中論證美國霸權終結與否
由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長期壟斷話語霸權的正是美國學派構建的主流理論,因之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主流話語的缺失中找尋到關于霸權終結與否的有力論據。
首先,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即是我們考察的主流話語之一,它與美國霸權的興衰可以說是同生共存的,我們可以把現實主義理論與論斷當作美國霸權的一面鏡子,從中清晰地看到美國霸權的歷史軌跡與理論烙印。該理論興起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20年危機中,以E.H.卡爾的《二十年危機》為代表,爾后漢斯·摩根索的權力政治論更是將現實主義推向主流理論的寶座,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則將其發展到頂峰,而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結構理論更是堪稱國際關系學中的牛頓定律。然而,我們回溯歷史,現實主義的興盛與美國霸權的歷史軌跡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說現實主義理論從來都是毫不掩飾美國霸權,并與霸權的興衰同呼吸、共命運。二戰的爆發一度宣告自由主義理想的破滅,美國政治精英們在現實主義理論對陣理想主義的反擊號角中加入了反法西斯戰爭;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格局,也一度因喬治·凱南為主要代表的“遏制”思潮找到了強有力的精神皈依;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海灣戰爭、阿富汗反恐戰爭、伊拉克戰爭,似乎現實主義理論的強勢總是與美國對外戰爭的勝利所表現出來的霸權行為形影不離。然而,現實主義這一主流話語,其理論的缺失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沃爾茲為代表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即以理論的解釋力著稱,卻由于其靜態性未能預見冷戰的結束;9.11事件以后,將現實主義理論發揮到極致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在面對21世紀的嶄新國際政治面貌時,其科學性和理論性亦難掩蒼白,不僅較之于傳統理論缺乏創新性,在闡述新時期美國霸權時也不免有些自嘲,稱美國只是西半球的一個地區霸權,而非全球霸主,也無所謂真正的全球霸權。現實主義理論的各個分支流派,在與其他學派交鋒的學理論爭中,時而耀眼,時而黯淡失色,尤其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及至九十年代末遭到來自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理論等全方位的挑戰。同樣,比照這一時期的史實,美國霸權若顯強勢張力,現實主義理論則更趨于壟斷話語霸權,而美國霸權逐漸式微,則批評理論爭鳴不斷。盡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活躍了思想,有助于學術進步和理論繁榮,然而,在筆者看來,這恰恰也可以從現實主義這一主流話語的失勢中,如同照鏡子一般明晰地反應出美國霸權的衰落,而現實主義理論這件美國霸權強勢時期必備的冷酷外衣也逐漸地被裝點成怪誕的禮服。我們仍然記得70年代初歐佩克石油戰帶給了西方自由世界長達十年的滯脹,美元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自由世界歐洲一體化對美國單極時代的新挑戰,這些都不是現實主義理論單槍匹馬可以應對的。如同金融危機這樣的歷來被現實主義視作“低級政治”的經濟議題,更是難以在其中找到只言片語。
其次,由于美國霸權的維持需要新的理論為其辯護,金融危機時期,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更有復蘇的理由。比如其核心理論如相互依存論,金融危機時世界經濟政治的相互依存表現得淋漓盡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在美國霸權的自我修復行為中得以印證,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宣稱,正是美國在金融危機中表現出來的脆弱性及此產生的非對稱相互依存導致美國處于“危機四伏”中,讓學界乃至政界急于驚呼美國霸權的終結,讓人遁入美國霸權歷史終結的幻境。因此,但凡我們耳邊響徹的“美國時代終結”“霸權終結”的論斷,無一不是受到現實主義理論啞火這一現狀的誤導,而事實上,終結的既不是現實主義理論,更不是美國的霸權,僅僅是脆弱性與敏感性相互依存不足以確證提供公共物品的霸權終結,因為尚無跡象出現體系內外的挑戰國。同時,軟權力因素的影響,由于仍然在全球化信息時代掌握著軟權力的優勢,美國霸權的影響力仍將持續,但由于受困于諸如金融危機等“低級政治”進程的束縛,其控制力在可見的將來會打折扣。
這一切都恰恰反應出了當前美國霸權的病態,其實不僅金融危機時期,應該確切地說是在冷戰的結束、蘇聯這一美國最強大的“非我”遭遇歷史終結后,美國卻陷入了帝國的迷思。體現在對外政策上,就是較多自由主義式的理性思考,而非現實主義的持續擴張,硬權力的聲勢還在,卻傾向于對軟權力的把持。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限于金融危機時期的窘迫環境,在面對傳統國際政治問題時表現得更加溫和,也更加注重軟權力的控制和影響。如能源戰略的調整和對伊斯蘭世界的政策,在金融危機時期這一大背景下,注定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對永葆美國霸權更具誘惑力和可實踐性,在主張多邊主義合作的當代世界,也更容易覓得國際合作,以形成維護美國霸權秩序的國際機制。
另外,建構主義之于文化、角色認知的理論似乎理應承擔起使該學派更具解釋力的話語使命,并突出人文關懷。文化霸權在美國霸權中的色彩較為黯淡,布熱津斯基認為文化優勢被美國所忽略。塞繆爾·亨廷頓也曾認為美國文化面臨著危機,并表現出了文化民族主義的焦慮。[5]金融危機條件下,美國的文化認同危機更為嚴重,而在這一情勢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建構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卻更有助于分析體系內其他大國的反應,即并沒有出現一呼百應的反美聯盟或霸權的挑戰者。危機中角色的認知,各國既不表現得像霍布斯文化中的“敵人”,也不再單純地再現洛克文化中“對手”角色的認知,而是部分地實現了類似康德文化的“朋友”特征,在體系中互助、共度難關,并且突出了國際關系中對于人文的關懷,如我國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債券,幫助美國人民度過危機,為走出金融危機重塑信心,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貢獻,則體現了這種建構主義式的人文關懷。
如上所述,金融危機時期的美國霸權面臨著的是其主流話語的失勢,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來的是霸權的病態,而非病危,更不是霸權的終結,任何一種國際關系理論都只能解釋國際社會生活的某一側面,而不能窮盡所有。在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當中,美國主流國際關系話語霸權的失勢及其理論的硬傷表現得更為明顯,需要對理論進行整合,方能全面理解之。現實主義這一主流話語的失勢也不能完全掩蓋其學理上的持久生命力。同樣,隨著美國在金融危機中逐步走出困境,其霸權國的姿態將改頭換面,理論上更偏向于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為其辯護,而對外政策中仍可映射出現實主義的大國政治魅影。換句話說,如果我們這時就斷定美國霸權終結了,那么,很可能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又重新燃起世界對美國單邊主義的關注(比如朝核危機、伊斯蘭世界與反恐),我們是否又該重新認同“美國霸權死灰復燃”呢?
三、金融危機下美國霸權時代不會終結
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霸權仍然表現出單極做大的傾向,體現在其控制力下降但影響力仍然強大,以及軟權力與硬實力的優勢。無政府狀態的體系結構下,由于代價過于高昂,且容易引起新的安全困境,增加多極化走勢下的不確定性,所以,各大國既不會也不愿輕易承擔制衡重任或扮演挑戰國身份。可以肯定的是,無政府體系部分呈現康德文化的屬性。話語霸權失勢是真,體系文化的霸權受到挑戰,極超霸權終結則言過其實。
任何提出體系外挑戰美國霸權,讓我國做反美先鋒的想法都過于激進。因為體系外的代價過于高昂,且容易反為掣肘,“中國威脅論”可能因之真的成了大國政治的悲劇。因此,審慎、隱忍的、體系內負責任參與,積極推進和諧多極新均勢的理念與外交出路方為上策。中國既做負責任的大國,又不可忽視現實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靈活外交;捍衛民族國家主權利益,避免“反成掣肘”“盲目當頭稱反美先鋒”的羈絆。鄧小平的“冷靜觀察、韜光養晦、決不當頭”仍然可以指導我們在金融危機時期應對“病態”的美國霸權時保持清醒和冷靜,從而努力實現我國的和平崛起,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
[1]參見Robert Gilpin.Warand Change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2]庫普乾在其《美國時代的終結——美國外交政策與21世紀的地緣政治》中揭示了冷戰喪鐘宣告的并非美國的最終勝利,而是其全球主導地位走向衰亡的開始。
[3]參見 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1997.
[4]參見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VintageClassics,1989.
[5]參見 Samuel Huntington.Who Are We:the Challenges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Simon?&Schuster,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