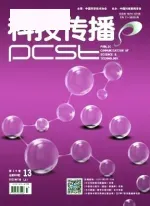從“諾貝爾科學(xué)獎頒獎典禮”看中國媒體的本土化策略
李 煒
中央電視臺科技專題部,北京 100859
2007年12月,第107屆諾貝爾獎頒發(fā)之際,首屆《諾貝爾科學(xué)之夜》特別節(jié)目在CCTV—10延時播出,主題晚會加上頒獎典禮總長4小時。不論觀眾在心中給該節(jié)目評分多少,對于科教頻道的管理者及節(jié)目制作者來說,《諾貝爾科學(xué)之夜》經(jīng)歷種種陣痛后得以誕生,足以令人欣慰。不論他的形貌是否優(yōu)雅高貴,不管他的振臂一呼是否高昂、激越,至少,他站在全球化的媒體大潮中,真真切切、擲地有聲地發(fā)出了中國人的聲音。面對別人的桂冠與榮耀,不再無地自容、內(nèi)心失衡,而以平和的心態(tài)表達(dá)了中國人團(tuán)結(jié)進(jìn)取、奮勇趕超的民族精神和良好的氣度修養(yǎng)。另一方面,《諾貝爾科學(xué)之夜》的播出,不止給中國大地帶來一場科學(xué)精神的洗禮,還給媒體管理者及從業(yè)人員帶來啟迪與思考,即,新傳播時代面對重大及突發(fā)國際事件,中國媒體該何去何從?
1 想并且敢發(fā)出聲音
為什么掩蓋、隱瞞 ?
在瑞典首都舉行的諾貝爾頒獎典禮以其百年傳統(tǒng)、至尊禮遇吸引著全球的目光,有條件的各國媒體都在紛紛直播或轉(zhuǎn)播這一人類文化的盛況。幾十年來,為何中國媒體慎之又慎,視為畏途?并且背轉(zhuǎn)身去,不予理睬。這與那見不到硝煙、卻無比持久的東西方文化戰(zhàn)密不可分。
上一代人忘不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十條誡命》中的那些字句:“盡量用物質(zhì)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jìn)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布。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等等。對于西方發(fā)達(dá)國家恃其文化強(qiáng)權(quán)加大對發(fā)展中國家信息和文化方面的滲透和控制,我們應(yīng)頭腦清醒、高度警惕,廣大民族文化,使之不被西方強(qiáng)勢文化“化”掉。
因此,重大國際事件出現(xiàn)時,媒體管理者往往擔(dān)心報道口徑的正確性,于是寧愿選擇保守、“穩(wěn)妥”的“安全”策略,將事件捂住不播,以防信息進(jìn)一步擴(kuò)散。多少年來,諾貝爾頒獎典禮遲遲不直播,與其帶有西方強(qiáng)勢文化的背景不無干系。
拋開它的國際背景不談,中國直播后會引發(fā)什么樣的輿論同樣令媒體擔(dān)憂。新中國建國近半個世紀(jì)了,科學(xué)家卻一直得不到諾貝爾獎,這是中國人的遺憾與痛處,也是我們不敢面對的事實。
“事件成就媒體”,沒有哪個媒體不希望在國際輿論中發(fā)出聲音,樹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但當(dāng)重大國際事件出現(xiàn)時,媒體在最該有所作為的時候,卻會遇到主客觀方面的重重障礙,無法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作為宣傳工具的定位,媒體常常要在遵循新聞傳播規(guī)律和遵守宣傳紀(jì)律上面對艱難抉擇。于是,雖然此前諾貝爾頒獎典禮頒發(fā)了106次,雖然地球早已變成了信息的村落,但是,當(dāng)全世界的目光都齊聚瑞典,星光璀璨的斯德哥爾摩音樂廳舞臺上,諾貝爾獎得主們周身光環(huán)、神采奕奕,在掌聲鮮花和榮譽(yù)的包裹中接受全球人的仰慕和敬意的時候,十三億多中國人集體缺席,喪失與世界先進(jìn)科學(xué)文化交流的大好時機(jī)。
新媒體時代,消息俯拾皆是:
面對重大國際事件,簡單的回避或隱瞞并不能解決問題。人們會通過其他渠道得到相關(guān)信息。
在互聯(lián)網(wǎng)還沒出現(xiàn)的年代,消息封鎖或許還有效。那時,從國外帶進(jìn)報紙或者收聽短波收音機(jī)都是非法的。重大事件發(fā)生后,人們都是從政府口中獲得信息。如今,網(wǎng)絡(luò)和衛(wèi)星電視的發(fā)展使封鎖新聞已經(jīng)變得非常困難。信息的傳播幾乎可以忽略時空限制,自由地跨越國界。同樣,在舊媒體上無法實現(xiàn)的言論自由也得到了空前展現(xiàn)。只要進(jìn)入網(wǎng)絡(luò),任何人都可以暢所欲言。互聯(lián)網(wǎng)的誕生和普及徹底消除了信息雙向流通的最后障礙。如今,阻擋信息的自由流通,如同螳臂擋車一樣荒唐可笑。這正是中國媒體所處的生態(tài)環(huán)境。
國內(nèi)媒體已不再是國人獲取世界信息的唯一來源,人們只要用google或baidu輸入關(guān)鍵字,瞬時就可搜到數(shù)以千萬計的有關(guān)諾貝爾獎的網(wǎng)頁。我們不可能阻攔讀者搜索網(wǎng)上信息,作為媒體人員,至少應(yīng)該做到讓大眾愿意看我們的報道,進(jìn)而能夠在不同立場的報道中作出選擇。傳播學(xué)中,“看到=相信”,要想讓人“相信”,就得先讓人“看到”。如果受眾對我們的媒體不屑一顧,又如何指望產(chǎn)生宣傳效果?
信息匱乏導(dǎo)致謠言滋長:
建設(shè)和諧有序的社會是我們的一貫愿望,但是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和人心安定,并不能靠掩蓋和回避事實來完成。當(dāng)重大事件發(fā)生時,如果主流媒體不去關(guān)注,不及時傳播真實、全面的信息,那么其他渠道的消息就會大有市場。這些報道可能并不真實,也許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有時甚至是惡意造謠。信息匱乏必然導(dǎo)致謠言滋長,最終給社會帶來不滿或恐慌。“非典”疫情初期的恐慌恰好說明了這個道理。因有關(guān)部門控制,對疫情的真相未能實事求是地進(jìn)行發(fā)布,于是在外國媒體對中國的疫情炒得沸沸揚(yáng)揚(yáng)的同時,中國主流媒體卻集體失聲。于是互聯(lián)網(wǎng)、手機(jī)短信傳播的各種訊息漫天飛舞,真真假假、混淆視聽,導(dǎo)致食品與藥物的搶購大潮,加劇了社會動蕩,誘發(fā)了恐慌的蔓延。
事實證明,采取掩蓋問題和回避矛盾的“鴕鳥政策”不僅于事無補(bǔ),反而會讓問題惡化,甚至走向愿望的反面。在重大國際事件發(fā)生時,如果中國主流媒體沒有采取行動、發(fā)出聲音,中國就失去了先發(fā)制人、引導(dǎo)輿論的先機(jī)。媒體管理者只有尊重公眾的知情權(quán),促進(jìn)政府與民眾進(jìn)行良好的溝通交流,在此基礎(chǔ)上達(dá)成理解與共識,才能真正地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與人心安定。
兩難抉擇,媒體怎么辦?
中國媒體要想在國際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就必須轉(zhuǎn)變自身的形象,讓國內(nèi)外受眾都覺得我們是可信、可敬的媒體。如果我們總是報喜不報憂,對負(fù)面問題避之唯恐不及,對國際上正在熱炒的敏感話題諱莫如深,不能及時、全面地報道受眾所關(guān)注的重大事件,一旦報道又總是帶著濃重的“宣傳”味兒,充斥著空洞乏味的說教,那么,我們不僅起不到在國際上塑造中國正面形象的效果,而且我們國內(nèi)的宣傳陣地也有可能被外國媒體占領(lǐng)。
新傳媒時代給新聞傳播帶來了新的游戲規(guī)則,在輕輕松松環(huán)繞全球的網(wǎng)絡(luò)、衛(wèi)星電視、手機(jī)等新媒體面前,已經(jīng)沒有了對內(nèi)宣傳、對外宣傳之分。面臨重大(國際)事件時,不但要考慮報了會產(chǎn)生什么副作用,更要考慮不報會產(chǎn)生什么副作用。“不說話”一樣會犯錯,錯就錯在貽誤了有效傳播信息的時機(jī)。兩害相權(quán)取其輕,不如采取直面以對的方式,先發(fā)制人,力圖掌握對事件輿論的主導(dǎo)權(quán),將不利影響降到最低點。
面對“非典”,中國媒體經(jīng)歷了從初期的“沉默失語”到后期的“自覺宣傳”的過程。謠言四布始于主流媒體的含而不發(fā),止于媒體的公開透明。
擁有社會責(zé)任感的媒體,不能再固守過去的宣傳定勢,對重大事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應(yīng)當(dāng)及時出擊、逆流而上,到事件的風(fēng)暴中心去,用權(quán)威的調(diào)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向大眾發(fā)送真實全面的信息,擊碎謠言,穩(wěn)定人心。
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
我國的發(fā)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fā)展也離不開中國。媒體如能搭好這座橋梁,不僅會使中國樹立一個良好的國際形象,還能為國家發(fā)展創(chuàng)造一個更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不僅有利于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還能更好地維護(hù)本國的利益。
我國一直堅持對外開放、面向世界的方針,學(xué)習(xí)國外先進(jìn)的科學(xué)技術(shù),博采各國文化之長,借“他山之石”來發(fā)展自己,真正做到“有容乃大”。
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許多時候要依靠國內(nèi)主流媒體來塑造,媒體不僅要客觀報道中國的實際情況,也要讓國內(nèi)受眾深入了解世界的經(jīng)濟(jì)、文化進(jìn)展。通過網(wǎng)絡(luò),我們媒體的報道也會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信息來源,甚至可能被認(rèn)為是更重要、更可信的信息來源。
重大(國際)事件是媒體力量的試金石。中國媒體應(yīng)采取更家開放的態(tài)度,在與西方傳媒的競爭中迎頭趕上,以一種全球傳播的勇氣,樹立媒體權(quán)威。同時使中國日漸被西方傳媒埋葬的弱小的正義之聲,在國際傳播中重新得到張揚(yáng)。
轉(zhuǎn)播諾獎頒獎典禮,打造權(quán)威科學(xué)平臺
每年十月諾貝爾獎公布之后,中國境內(nèi)一輪一輪的反思都會潮水般涌起,佩服、抱怨、爭議、感嘆等各種情愫在中國民眾的心中回蕩、翻滾。每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爾摩抓牢了全球的目光,以百年歷史、皇家氣派、至尊榮耀著稱的世界頂級科學(xué)盛典到底什么樣呢?地球這端的人們格外好奇。
民眾因關(guān)心而好奇,因好奇卻不得真相而猜測,因猜測生疑進(jìn)而不滿、抱怨。諾貝爾頒獎典禮全球直播的進(jìn)程中,中國觀眾的缺失如同某種可怕的沉默,阻礙我們敞開胸懷、融入世界,繼往開來的步伐。而對于所有渴求進(jìn)步、盼望革新的中國人來說,找出原因、拉近差距,從而追趕超越才是重點。
央視科教頻道為何要頂著壓力主動制作這樣一個可能叫好卻不太可能叫座的特別節(jié)目?在輿論的風(fēng)口浪尖上將這樣一場風(fēng)起云涌的科學(xué)盛宴呈現(xiàn)給國人,科教頻道想要傳達(dá)什么?誰能夠回答這些大眾最關(guān)心的敏感話題:諾貝爾獎離中國到底有多遠(yuǎn)?中國科學(xué)家為什么得不到諾貝爾獎?中國教育怎么了?等尖銳問題。
為什么要轉(zhuǎn)播,諾貝爾頒獎典禮在中國本土化會為兩袖清風(fēng)的科教頻道帶來可觀的廣告收入嗎?群星閃耀的奧斯卡之夜是美國廣告商的最愛,電視臺廣告收益僅次于美式足球超級杯;但奧斯卡之夜在中國本土的市場商機(jī)卻很有限。獲得奧斯卡頒獎典禮的大陸播映權(quán)價格“不到200萬元人民幣”,和動輒千萬甚至上億元轉(zhuǎn)播費的體育賽事相比并不太高。與此相比,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轉(zhuǎn)播費幾近于無,差不多相當(dāng)于免費贈送了。這也從另一角度印證了諾貝爾頒獎典禮在中國不會有較好的收視表現(xiàn)。
商機(jī)多寡取決于收視率點數(shù)。首先是錄播,晚了一天就成了炒冷飯,時效性差了很多,缺少了最大的賣點;其次,還得考慮有沒有華裔、本土科學(xué)家獲獎,有沒有我們熟悉的世界級大科學(xué)獲獎家,獲獎項目我們是否熟悉。對普通觀眾來說,追看陌生的外國大科學(xué)家困難較大。
但是,百余年來,諾貝爾獎以其客觀嚴(yán)謹(jǐn)?shù)木裼涗浟耸澜缈茖W(xué)的發(fā)展,那些獲獎的人們,或是解決了某個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或是大大拓寬了人們認(rèn)識世界的視野,或是為人類帶來了更多福祗,他們?yōu)槿祟愖鞒隽司薮筘暙I(xiàn)。中國無緣諾貝爾科學(xué)獎,是國人的一大遺憾;科教頻道無法讓中國觀眾親眼目睹頒獎時刻的壯麗與輝煌,也不能不說是電視界的一大遺憾。
在全年下滑的態(tài)勢中,新能源車成為僅有的亮點。據(jù)中國汽車工業(yè)協(xié)會發(fā)布數(shù)據(jù)顯示,11月新能源汽車銷量同比增長37.6%,1~11月同比增長68%。
在我國“科教興國”戰(zhàn)略背景下誕生的科教頻道,開播九年來,以其高揚(yáng)“教育品格、科學(xué)品質(zhì)、文化品位”的特色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贊譽(yù),2002年獲得國際電視科技宣傳領(lǐng)域的最高獎--儒勒·凡爾納獎。它被專家譽(yù)為“走出了打造頻道品牌第一步”。科教頻道始終固守“三品”的頻道核心理念,獲得了其它電視媒體夢寐以求的品牌美譽(yù)度和受眾忠誠度。
科教頻道要想再上層樓,在國際上發(fā)出比較“強(qiáng)大”的聲音,其自身也必須強(qiáng)大——能夠在第一時間對發(fā)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科學(xué)事件進(jìn)行第一手的報道,而且是權(quán)威的、可信的報道,是最有說服力的試金石。在復(fù)雜的國內(nèi)輿論環(huán)境中,以巧妙的方式直播諾貝爾頒獎典禮,是一直致力于打造權(quán)威科學(xué)平臺的央視科教頻道必須面對的嚴(yán)峻挑戰(zhàn)。
雖然中國觀眾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只是看客身份,雖然轉(zhuǎn)播諾貝爾頒獎典禮既不會帶來可觀的商業(yè)利益,又費時費心費力,還很可能不討好甚至遭致棒喝,但能夠讓中國觀眾欣賞到國際科學(xué)盛會、了解世界前沿科學(xué)信息,進(jìn)而通過科學(xué)認(rèn)識世界、了解世界,是中央電視臺義不容辭的責(zé)任,科教頻道選擇了勇敢擔(dān)當(dāng)。
十年之內(nèi),諾貝爾獎由歐美科學(xué)家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不會得到根本改變。據(jù)統(tǒng)計,截止至2004年年底,美國共有278位諾獎得主。占世界人口總數(shù)不到5%的美國,獲得諾貝爾科學(xué)獎的人數(shù)卻占全球獲獎人數(shù)的70%以上。為什么美國有那么多人能夠獲獎,而中國人為什么始終未能出現(xiàn)在諾貝爾獲獎名單上?讓14億中國人在諾貝爾獎頒獎臺下做一個優(yōu)雅的看客,我們需要多大的肚量才能擁有鎮(zhèn)定自若的表情!這點急需媒體就如何正確看待諾貝爾獎對大眾進(jìn)行科學(xué)有力的引導(dǎo)。
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是對人類創(chuàng)新成就的一次國際性認(rèn)可,也是全球新聞媒體關(guān)注的焦點,中國媒體沒有理由背過身去。央視科教頻道、東方衛(wèi)視分別以《諾貝爾科學(xué)之夜》、《科學(xué)的光芒》為題,對諾貝爾獎頒獎典禮首次實況轉(zhuǎn)播,既是表達(dá)對科學(xué)的尊重,同時也是為了滿足大家對這個只聞其名不見其面的盛大典禮的好奇心。兩臺轉(zhuǎn)播的目的都在于拉近科學(xué)和公眾的距離,消除大眾對科學(xué)的敬畏,分享科學(xué)帶來的快樂,接受一次全面的科學(xué)精神的洗禮,共同體會科學(xué)發(fā)展觀的內(nèi)涵。中國如果放棄了“諾獎外交”的機(jī)會,不僅會失去進(jìn)一步擴(kuò)大我國的世界影響力的一次良機(jī),而且也會嚴(yán)重傷害國際友人的情感。2007年諾獎典禮的轉(zhuǎn)播,可以說是我國外交政策、科技政策、甚至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上的一大成功。
2 第一時間發(fā)出聲音
諾貝爾獎頒獎在北京時間12月10日23∶30分舉行,而《諾貝爾科學(xué)之夜》對頒獎典禮的轉(zhuǎn)播卻是推遲到次日20∶00后播出,這也是讓觀眾感覺困惑、稍有微詞之處。雖然作此選擇事出有因,但從另一側(cè)面也印證了觀眾常有的感覺:重大事件發(fā)生時,中國媒體往往明顯呈現(xiàn)出報道時間上的滯后性,尤其是面對國內(nèi)敏感事件時常常“失音”。
我們的媒體是國家方針、政策的宣傳工具,在報道前往往需要征求有關(guān)部門的意見,這必然空耗一段時間。在中國媒體保持沉默的時候,國外媒體卻正大張旗鼓地進(jìn)行緊密報道。受眾甚至?xí)J(rèn)為國內(nèi)媒體為維護(hù)政府利益在刻意隱瞞負(fù)面消息。滯后報道損害了媒體的形象,使媒體失去報道的主動權(quán),并進(jìn)一步喪失了對國際輿論的主導(dǎo)權(quán)。
在重大事件發(fā)生后,中國媒體必須爭奪新聞首發(fā)權(quán),不能讓西方媒體和一些網(wǎng)站道聽途說,亂發(fā)新聞。也不能等到虛假新聞在國內(nèi)外被傳得沸沸揚(yáng)揚(yáng)、造成一種先入為主的局面后才來澄清。落后必然挨打,盡早發(fā)布比事后解釋要好得多。“發(fā)布是主動的,解釋是被動的;按照人的一般認(rèn)知與接受規(guī)律,發(fā)布是被信任的,而解釋是被懷疑的。”
在重大事件發(fā)生時,媒體不僅不能缺席,而且還要盡早到達(dá)現(xiàn)場,在第一時間發(fā)出聲音,力爭與事件同步進(jìn)行報道,以爭取受眾最大程度的關(guān)注,達(dá)到適時引導(dǎo)輿論的作用。
那么,央視《諾貝爾科學(xué)之夜》以及東方臺《科學(xué)的光芒》為什么都推遲了20多個小時才對頒獎典禮進(jìn)行轉(zhuǎn)播呢?
何以延時播出:
大凡世界級的頒獎典禮都會因防范敏感或?qū)擂螆雒娑扇⊙訒r播出方式。比如,珍妮·杰克遜“露胸風(fēng)波”尷尬事件發(fā)生后,美國廣播公司決定,將原來的電視現(xiàn)場直播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改為延時5秒錄像轉(zhuǎn)播,以免讓觀眾看到穿著暴露的來賓可能會出現(xiàn)的不雅鏡頭。因為獲獎?wù)哌^度興奮,奧斯卡頒獎歷史中出現(xiàn)過若干次滑稽事件,比如,1974年奧斯卡頒獎典禮進(jìn)行到一半,一位長發(fā)、蓄須的全裸男子突然沖上舞臺,做出了“和平”的手勢;1997年以《征服情海》拿下最佳男配角獎的演員,不僅上臺時大喊大叫、又蹦又跳,下臺后甚至開始咬人;1998年榮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大獎的演員,因為興奮過度,上臺致謝時說他想跟每個人做愛!
文藝盛典中最容易出現(xiàn)鬧劇,其結(jié)局不過是給現(xiàn)場帶來一定程度的混亂和搞笑效果,觀眾一般都會一笑置之。但科學(xué)盛典就不同了,它以智慧的尊嚴(yán)和思想的深遠(yuǎn)制勝,莊嚴(yán)華貴的氛圍中不允許出現(xiàn)一絲不和諧音。國際敵對勢力、敏感政治事件、文化的隔絕和誤讀都會對它造成難以挽回的不良后果,各種不和諧音都在覬覦借此舞臺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所以,諾貝爾頒獎典禮在中國落地時機(jī)的選擇非常重要。雖然電視直播本身并沒有太大難度,但央視卻不能考慮直播方式,那么轉(zhuǎn)播時延遲多久才合適呢?
央視科教頻道之所以后延21小時播出,除政治、安全因素外,還有時差、語言等問題。況且頒獎晚會并不像體育比賽那樣注重第一時間。瑞典直播的時候我國已近午夜時分,如果現(xiàn)場直播,極大多數(shù)觀眾都不會看。另外,諾獎頒獎典禮中語言復(fù)雜,如果未經(jīng)翻譯而直接采用瑞典語間或英語、法語同步播出,也不會達(dá)到最佳的收視效果。所以,延遲至次日黃金時間播出應(yīng)該是最好的選擇。
2007年首屆《諾貝爾科學(xué)之夜》圓滿地播出了,并獲得2008年度廣電總局科技創(chuàng)新獎二等獎”(政府獎)。到之后兩年,第二屆“科學(xué)之夜”卻遲遲不見下文。
將《諾貝爾科學(xué)之夜》這一鮮活有力的科普形式堅持下去,每年利用人人關(guān)注的諾貝爾獎頒獎的良好時機(jī),加大科技宣傳力度,形成崇尚科學(xué)思想、弘揚(yáng)科學(xué)精神的輿論氛圍,這對實現(xiàn)科教興國戰(zhàn)略、建設(shè)創(chuàng)新型國家、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等目標(biāo),將提供良好的科技人文環(huán)境和最有力的智力支持。
諾貝爾獎設(shè)立百余年了,中國人卻年年經(jīng)受著困擾和尷尬,難以做到平靜和坦然。年復(fù)一年地缺席,中國人對諾貝爾獎是何等的愛恨交加。諾貝爾獎仿佛成了我們心中一塊很重的負(fù)擔(dān),重到已經(jīng)不堪承受。就如一位網(wǎng)友所說,“很不幸,我們跟諾貝爾獎生活在一個星球上,讓我們至今飽嘗‘諾獎弱國’的郁悶;很幸運,我們跟諾貝爾獎生活在一個星球上,讓我們見識了如此眾多的世界文明的璀燦之花”。 《諾貝爾科學(xué)之夜》仿佛一面鏡子,它提醒我們檢討自己的不足,并督促我們調(diào)整心態(tài),迎接本土諾貝爾獎的到來。
我們有理由期待,當(dāng)“諾貝爾自然科學(xué)獎頒獎典禮”等重大國際事件發(fā)生時,中國媒體不再回避,能夠做到登高一呼,及時有力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1]《傳播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如何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中國對外傳播的效果分析與對策思考》,俞熙娜.
[2]《中國媒體將走什么樣的改革之路?:半島電視臺與李希光對話實錄》來自:免費論文網(wǎng)www.paper800.com.
[3]《在重大突發(fā)事件報道中建立媒體權(quán)威》,杜志紅.
[4]《媒介的責(zé)任與空間》,葉鳳英.
[5]《黨政干部學(xué)刊》2001年第4期,《全球化時代的中華文化走向--方克立教授訪談錄》,姚黎君.
[6]《奧斯卡:萬千感慨80歲》之《中國胃口的奧斯卡》 2008年03月10日,新世紀(jì)周刊,余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