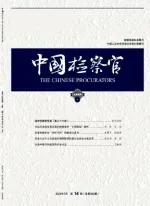公民的創(chuàng)作自由與國家公權(quán)力的界限
文◎郭慶珠
公民的創(chuàng)作自由與國家公權(quán)力的界限
文◎郭慶珠*
前文兩起與公民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關(guān)的熱點事件,雖然警方借口不同的罪名對作家進(jìn)行拘捕,但是該事件公開后,社會普遍猜測問題的關(guān)鍵應(yīng)該在于兩地的公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及官員認(rèn)為以上兩個作品的內(nèi)容“詆毀”了當(dāng)?shù)氐男蜗螅|動的官員的利益,有借警察權(quán)力不正當(dāng)打擊作家之嫌。以上事件其實并不是簡單的刑法問題,因為它提出了一個古老而又有現(xiàn)實意義的課題——如何正確理解公民的創(chuàng)作自由與國家公權(quán)力的界限?
一、憲法意義上的創(chuàng)作自由
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公民自由審美的精神活動外化于文字、圖畫等藝術(shù)形式的過程。公民首先在內(nèi)心尋求、審視美的東西,然后通過文字等把美創(chuàng)造、物化出來。創(chuàng)作的核心體現(xiàn)為創(chuàng)作者的精神活動,并把精神活動的成果呈現(xiàn)出來。從憲法的層面來講,創(chuàng)作自由可以歸入精神自由的范疇。精神自由是近代憲法所確認(rèn)的三大自由之一,它與人身的自由、經(jīng)濟(jì)的自由一道,共同構(gòu)成近代以來憲法權(quán)利體系的內(nèi)核部分。[1]我國《憲法》第47條也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進(jìn)行科學(xué)研究、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從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過程可以看出,創(chuàng)作自由是內(nèi)在和外在的統(tǒng)一,這是和精神自由的特點相統(tǒng)一的。內(nèi)在精神自由所保障者,主要為與他人、社會與國家(外在環(huán)境或?qū)ο螅o直接關(guān)系之內(nèi)心世界,通常亦不對外造成直接之影響或損害,因此,也較無予以限制之可能性與必要性。所以各國法律對此均不限制,而為絕對的保障。而外在精神自由是指個人將其內(nèi)在精神活動之結(jié)果或精神生活之方式,以語言、文字、圖畫、肢體動作或其他任何媒介表達(dá)于外,而使他人或社會得以知悉其內(nèi)心之意念的自由。外在精神自由并非是絕對的,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2]創(chuàng)作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主要是一種消極權(quán)利,即避免國家公權(quán)力干涉的權(quán)利,公權(quán)力不得對公民創(chuàng)作的自由進(jìn)行肆意、不當(dāng)?shù)母缮妗?/p>
保障公民的創(chuàng)作自由在現(xiàn)代法治社會有重要的意義。首先,是維護(hù)人性尊嚴(yán),保障公民藝術(shù)創(chuàng)作潛能得以充分釋放的需要。精神自由是基于人的屬性的內(nèi)在需要,是維護(hù)人性尊嚴(yán)的基本條件。[3]在現(xiàn)代法治社會,人在社會關(guān)系中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還是一個個具體的個體,不能借口社會共性完全抹殺個體的需要和自我的實現(xiàn),這種個體的需要和自我的實現(xiàn)恰恰是推動社會進(jìn)步的重要動力。“在特殊且本質(zhì)的意義之下形成個人的東西”是人性尊嚴(yán)的核心價值之一,它存立的基礎(chǔ)在于:人之所以為人乃在于其心智,這種心智使其具有能力自非人的本質(zhì)脫離,并基于自我的決定去意識自我,決定自我,形成自我。[4]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有自己的特點,對于美的發(fā)現(xiàn)和認(rèn)知往往需要創(chuàng)作者自身藝術(shù)特質(zhì)的充分彰顯來實現(xiàn),只有充分尊重創(chuàng)作者的“自我”,才會促進(jìn)文藝創(chuàng)作的繁榮。如果國家公權(quán)力可以肆意干涉公民創(chuàng)作自由的話,公民的“自我”必然被抹殺,文學(xué)藝術(shù)也必然走向凋敝,對于個體“自我”的尊重本身就是人性尊嚴(yán)的應(yīng)有之義。其次,是尊重和包容不同價值,建立價值多元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條件。在現(xiàn)代社會,利益是多元的,價值的訴求也是多元的,尤其是我國在經(jīng)濟(jì)上采取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以后,鼓勵和支持不同的利益主體在法治的框架下自由競爭,為各種價值的表達(dá)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舞臺。這種多元的價值訴求必然會在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出來,《大遷徙》和《在東莞》所反映的現(xiàn)象實際上是時代背景和現(xiàn)實價值需求在文藝作品中的反應(yīng),面對著這種表達(dá),國家公權(quán)力沒有必要過度的反應(yīng),在文藝作品沒有違反必要界限的情況下,國家公權(quán)力應(yīng)該尊重公民的創(chuàng)作自由。
二、國家公權(quán)力在公民創(chuàng)作自由中的界限
(一)公權(quán)力因什么事由可以進(jìn)行干預(yù)
一般認(rèn)為,“人民的著作自由之限制,如同人民之言論自由,為保障他人權(quán)利(名譽、人格),或為保障國家安全與社會利益,是可以限制之。”[5]上述限制的事由可以簡潔地概括為兩個層面,即不得侵害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公共秩序和安全也是為了人類的福祉,這一目的規(guī)定了個人權(quán)利的行使所不可逾越的外部界限。學(xué)術(shù)自由不可與這一目的相悖,也就必須對為了這一目的的手段有所尊重。[6]從廣義上來講,創(chuàng)作自由可是算是學(xué)術(shù)自由的一種特殊形式,因此上述學(xué)術(shù)自由的限制也是適用于創(chuàng)作自由的。以上兩個事由中,不得侵害國家安全的內(nèi)涵主要包括不得泄露國家秘密、不得鼓吹動亂等;不得侵害公共秩序的內(nèi)容主要包括不得對社會公認(rèn)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信仰構(gòu)成挑戰(zhàn)、不得對宗教信仰進(jìn)行誹謗或污蔑、不得對公民私生活的自主性或獨立性構(gòu)成侵犯等。[7]
需要特別明確一點的是,對于國家機(jī)關(guān)及其工作人員行使公權(quán)力的行為所進(jìn)行的批評不應(yīng)該成為干預(yù)公民創(chuàng)作自由的事由。我國《憲法》第41條第1款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jī)關(guān)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quán)利……。”國家公權(quán)力本來就源自于公民權(quán)利的讓渡,公權(quán)力行使的終極目的是維護(hù)公民福祉,公民對于行使國家公權(quán)力的機(jī)關(guān)及其工作人員當(dāng)然有監(jiān)督和批評的權(quán)利。國家公權(quán)力及其工作人員必須無條件的容忍公民的批評,而不得利用公權(quán)力進(jìn)行報復(fù)。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創(chuàng)造條件讓人民批評、監(jiān)督政府”,對公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批評是現(xiàn)代法治社會的一個常態(tài)。公民在文學(xué)作品中對公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進(jìn)行批評是正當(dāng)?shù)模粦?yīng)該成為公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干預(yù)創(chuàng)作自由的事由。
(二)公權(quán)力在什么情況下可以進(jìn)行干預(yù)
其一,要進(jìn)行充分的利益衡量,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等公益未必一定優(yōu)于創(chuàng)作自由等私益。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內(nèi)涵是多元的,很多事項都可以歸入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范疇,但并非每一個事項都會成為限制公民創(chuàng)作自由的法律依據(jù),那種認(rèn)為所有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事項都可以成為限制創(chuàng)作自由法律依據(jù)的認(rèn)識是十分有害的,必然成為公權(quán)力壓制創(chuàng)作自由的最完美借口。也就是說,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是限制創(chuàng)作自由的事由,但并非是每一個涉及到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事項都可以用來限制創(chuàng)作自由。憲法承認(rèn)公益與私益之間存在對立關(guān)系,若憑人民無限制地行使基本權(quán)利,會影響社會的其他法益,故須予以限制,但絕不能任意以謀求公益為借口而犧牲私人利益。[8]公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必須要對公益和私益進(jìn)行充分的利益衡量,只有公益的價值大于私益價值的時候,公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才可能對公民的創(chuàng)作自由進(jìn)行干預(yù)。比如,如文學(xué)作品鼓吹動亂,公權(quán)力予以干預(yù)是必要的,因為這時公益的價值明顯大于私益的價值。但是若象《在東莞》小說一樣,如果其中出于作品的需要涉及到了必要的“情色”描寫,雖然表面上有違公共秩序的要求,但是仍然不得以公共秩序為借口干預(yù)創(chuàng)作的自由,因為這時“情色”描寫只是整個藝術(shù)品得以呈現(xiàn)的手段,而并非該藝術(shù)品的目的,公益的價值顯然低于私益的價值,但若該藝術(shù)品的目的本身就是追求“情色”的宣揚,顯然公益的價值高于私益的價值,國家就應(yīng)該予以干預(yù)了。公權(quán)力在作出決定時,不能片面追求公益或某一方之利益,必須就相互沖突的利益進(jìn)行通盤考量,客觀衡量取舍。
其二,以“必要”為限度。由于創(chuàng)作自由主要是一種消極權(quán)利,公權(quán)力對待它必須要有充分的寬容和節(jié)制。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概念都屬于不確定法律概念,在進(jìn)行判斷的過程中有很大的自由決定空間。國家有關(guān)機(jī)關(guān)在判斷的過程中應(yīng)該以“必要”為限度,不可以過度的解讀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需要,過度解讀必然會對公民自由權(quán)的保障極為不利。何為“必要”?應(yīng)該以可以帶來對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重要侵害之高度危險性為標(biāo)準(zhǔn),如直接鼓吹動亂或?qū)ι鐣J(rèn)的秩序或倫理規(guī)則的違反等。也就是說,公權(quán)力對于創(chuàng)作自由應(yīng)該盡可能的寬容,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即使在近代具有一定專制主義傳統(tǒng)的憲政主義國家里,其憲法雖然并不徹底保障一般國民的言論自由等表達(dá)自由,然而唯獨對文化活動的自由,尤其是對學(xué)術(shù)自由則網(wǎng)開一面,予以全力保障。 ”[9]
三、結(jié)語
憲法規(guī)定公民基本權(quán)利的一個重要的作用是為國家公權(quán)力的行使劃定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保障我國憲法規(guī)定的公民創(chuàng)作自由,防止公權(quán)力的肆意干涉,避免公權(quán)力的打擊報復(fù),這是我國文藝繁榮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國,保障公民權(quán)利的應(yīng)有之義。
注釋:
[1]林來梵著:《從憲法規(guī)范到規(guī)范憲法——規(guī)范憲法學(xué)的一種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頁。
[2]許志雄等著:《現(xiàn)代憲法論》,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08頁。
[3]杜承銘著:《論表達(dá)自由》,載《中國法學(xué)》2001 年第3期。
[4]黃桂興著:《淺論行政法上的人性尊嚴(yán)理念》,載城仲模主編:《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一),三民書局1994年版,第10頁。
[5]陳新民著:《憲法導(dǎo)論》,新學(xué)林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07頁。
[6]何生根、周慧著:《論學(xué)術(shù)自由的法律界限》,載《法律科學(xué)》2007年第2期。
[7]杜承銘著:《論表達(dá)自由》,載《中國法學(xué)》2001 年第3期。
[8]陳新民著:《德國公法學(xué)基礎(chǔ)理論》(下冊),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頁。
[9]林來梵著:《從憲法規(guī)范到規(guī)范憲法——規(guī)范憲法學(xué)的一種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頁。
*天津師范大學(xué)法學(xué)院副教授,法學(xué)博士[3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