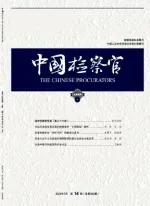非法證據排除對維護程序尊嚴的意義
——兼評我國刑事證據法的新規定
文◎王敏遠
非法證據排除對維護程序尊嚴的意義
——兼評我國刑事證據法的新規定
文◎王敏遠*
如今,“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1]已經成為中國法學界,尤其是訴訟法學界普遍肯定的論斷。然而,需要說明的是,能夠成為區別法治與恣意的人治的程序,應當是“正當程序”,即注重權利保障和職權規制的程序;不僅如此,而且應當是具有足夠尊嚴的程序。換句話說,體現了權利保障和職權規制的程序規范應當能夠有效的發揮作用,是區別于恣意的人治的法治的基礎。
程序規范應當能夠有效的發揮作用,需要具備諸多條件。其中,對違反程序的行為設置系統而科學的程序性法律后果,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基礎性條件。而在諸多程序性法律后果中,非法證據的排除又是常見且有效的規定。對此,筆者以前曾予以論述。[2]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設置系統而科學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卻一直缺乏應有的重視。不論是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還是經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均缺乏對違反程序的行為設置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后果。[3]最近,由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門頒發的 《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 “死刑案件證據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改變了這個局面。在這兩個規定中,對非法證據的排除作了較為明確而系統的規定。我認為,兩個規定的出臺,通過對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的確立和實施,將會有助于改變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法律規范缺乏應有的尊嚴的局面。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又必要深入探討兩個規定所依據的原理及相關內容,以使兩個規定在實踐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一、刑事程序法律規范具有尊嚴的含義及意義
如果說權利保障和職權規制是程序的正當性基礎,那么,程序規范具有不可違反的尊嚴,則是正當程序能有效遏制“恣意的人治”的基礎。這是現代刑事證據法的另一個基礎性問題。
現代刑事證據法大都是些程序性規范。這些程序性規范在現實中是否得到應有的尊重,使其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顯然是個必須重視的基礎性問題。很難設想,如果刑事證據法在權利保障和職權規制方面所作的規定,在現實中并不被尊重,那么,這樣的規定還有多少實際意義?通過對一些案例的分析,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人們對諸如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等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對形成這些冤假錯案的原因作多角度的剖析,諸如刑訊逼供屢禁不止、輕信口供、刑事證明標準難以把握等等。確實,形成這些冤假錯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原有的刑事證據規則不夠完善也是重要原因。然而,我認為,關鍵的問題是:已經規定的程序并未被尊重,恣意違反程序規范的行為仍能在現實中產生積極的效果。我們從已經披露的辦案過程不難看到這一點。佘祥林案曾多次被發回重審,原因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但在多次發回重審,事實和證據問題并未得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冤案仍然鑄成。即使是從1979年制定的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看,這也是嚴重違法。至于趙作海案更能說明問題。承辦案件的檢察機關和法院對案件事實、證據并無把握。據說,趙作海案的辯護人當時尚未取得律師資格,但他仍然能夠指出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但冤案仍未能避免。我以為,這樣的冤案很難認為是由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明標準等出了問題所致。
從極端的意義上甚至于可以說,如果能夠確保原有的程序規范得到有效遵守,應可以預防類似佘祥林案、趙作海案等冤案的發生。關鍵的問題在于,已經規定的程序可以恣意違反,而刑事訴訟進程和結果卻仍能以此為據。因此,缺乏不可違反的尊嚴的程序規范,其效果十分可疑。這才應是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二、如何使程序法律規范具有不可違反之尊嚴
如何使刑事程序規范具有不可違反的尊嚴,這是個復雜的問題。在我看來,建構完善的程序性法律后果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不可或缺的基礎。
關于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應系統規定刑事程序法律后果的問題,筆者曾在1994年發表過相關的論文。[4]我認為,程序法僅僅依靠實體法作為保障是不夠的,因為現實表明:現有的程序法對屢見不鮮的違反刑事訴訟程序的行為幾乎無可奈何,由此導致了諸多不合理現象。例如,刑事訴訟中的職權機關違反程序規定行使職權,但其效力卻被肯定;職權機關的程序違法行為使刑事訴訟中的參與人權利受到侵犯,而結果卻被肯定;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未導致任何法律后果――既無合適的實體法律后果可適用,也無明確的程序法律后果的規定,等等。為此,刑事訴訟法需要建構自成體系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在該文中,筆者曾對刑事程序法律后果的概念進行過簡要論述,即對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及其結果在程序上不予認可,或予以否定或要求補正。根據該概念,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法律后果共有四種:(1)否定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的效力,并使訴訟從違反訴訟程序的該行為發生的那個階段重新開始。(2)否定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的效力,并否定因該行為所得到的訴訟結果。(3)否定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及其結果,并使訴訟進入另一階段。(4)補正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以使該行為得到糾正,最終符合程序法的要求。
此后,基于建構刑事訴訟法自成體系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的需要,筆者另撰文對設置刑事程序法律后果的原則問題進行了論述。[5]在我看來,設置刑事程序法律后果的原則應當包括權利保障、規范職權、完整、充分、適當、協調等原則。其中,特別需要在此指出的是,在循序漸進地建構刑事訴訟法自成體系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的過程中,應當首先針對最常見的、嚴重侵犯權利的違反程序規范的行為設置有效的程序性法律后果。
我認為,設置刑事程序法律后果的原則,對違反程序的行為設置系統而科學的程序性法律后果,是使刑事程序規范具有不可違反的尊嚴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基礎性條件。
三、對兩個《規定》相關內容的簡要評述
根據上述原理,我們分析關于刑事證據的這兩個《規定》,可以發現:
第一,鑒于排除非法證據是程序性法律后果的重要內容,因此,兩個《規定》明確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及相關內容,使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設置程序性法律后果方面邁出了引人矚目的步伐。
“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對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這些非法言詞證據,采取了非常嚴厲的態度,即絕對予以排除。這不僅意味著在法庭審判時應當排除非法言詞證據,不能將其作為認定被告有罪的根據(該規定第2條),而且在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準逮捕、審查起訴中,對于非法言詞證據也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為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的根據。并將此延伸到了刑事二審程序。“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第12條規定,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第一審人民法院沒有審查,并以被告人審判前供述作為定案根據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檢察人員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被告人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死刑案件證據的規定”不僅對非法證據的排除作了相應規定(如該規定第19條規定的“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等),而且對違反刑事證據規則的其他一些情況,也規定若干程序性法律后果。例如,該規定第26條規定:“勘驗、檢查筆錄存在明顯不符合法律及有關規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或者說明的,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引人矚目的是,兩個《規定》不僅對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作出了明確規定,而且對采用非法方法獲得的物證、書證,也規定了相應的程序性后果。“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第14條規定:“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死刑案件證據的規定”第9條第4項規定:對物證、書證的來源及收集過程有疑問,不能作出合理解釋的,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該規定第14條規定:“勘驗、檢查筆錄存在明顯不符合法律及有關規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或者說明的,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兩個《規定》對非法證據的明確否定態度,使我國刑事證據法發展過程中的應予充分肯定的進步,其中所規定的排除或要求補正等諸多程序性法律后果,對于促進我國刑事程序規范具有不可違反的尊嚴,應會產生積極影響。
第二,如何使兩個《規定》中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得到落實,仍需進一步的努力。
兩個《規定》明確肯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等程序性后果是一回事,在發生了違法取證行為之后,能否真正產生非法證據排除等程序性后果則是另一回事。歷史和現實表明,非法取證是很難被揭露的,更難以被證實。由此可見,如何解決發現非法證據,是能否有效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關鍵。為了有效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兩個《規定》對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等非法行為規定了相應的審查程序,另一方面,則將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明確規定由控方承擔。例如,“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第11條規定,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訴人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當然,應當清醒地看到,兩個《規定》現有的努力是否足以有效解決這個問題,尚難肯定。例如,在法庭查證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的問題時,實踐中現有的做法是:由審訊機關提交加蓋公章的說明材料以證明沒有刑訊逼供。這樣的做法不斷受到質疑。“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第7條規定:在法庭查證審前供述的合法性問題時,如果“公訴人提交加蓋公章的說明材料,未經有關訊問人員簽名或者蓋章的,不能作為證明取證合法性的證據。”這無疑較原有的做法邁進了一步。然而,其對發現和證明非法取證行為的效果究竟如何,尚待觀察。顯然,“經有關訊問人員簽名或者蓋章”的說明材料如果輕易地被視為可以“證明取證合法性的證據”,那么,證明存在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就將是十分困難甚至可以說是難以實現的事情。
第三,關于非法證據,對控辯雙方應有所區別,不應“一視同仁”。
如果說程序性法律后果的設置目的在于規制職權、保障權利,那么,在確定非法證據的排除及相關程序規范時,對控辯雙方就應有所區別,不應 “一視同仁”。兩個《規定》確實將非法證據排除工作的重心放在了控方。然而,在有的地方,卻給人以將控辯雙方“一視同仁”的感覺。“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第13條規定:“庭審中,檢察人員、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未到庭證人的書面證言、未到庭被害人的書面陳述是非法取得的,舉證方應當對其取證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如果該條內容確實意味著對控辯雙方 “一視同仁”,那么,有必要對其進行檢討。對控方證據要求其不僅具有真實性,而且具有合法性,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是出于規制職權、保障權利的需要。然而,對于辯護方提供的有利于被告人得證據來說,重要的是其提供的證據的真實性,即如果辯護方提供的證據足以證明無罪,那么,該證據的真實性才是關鍵問題。換句話說,無罪的證據如果是真實的,即使不能證明其合法性,也不應影響其證明效力,更不應予以“排除”。[6]因此,就非法證據的排除而言,我們絕不能對控辯雙方“一視同仁”。
對兩個《規定》的如上簡要評論,并不是否定兩個《規定》通過刑事證據法在權利保障與規制職權方面的積極貢獻,以及因此而對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文明進程的推進作用,而是要以此說明,兩個《規定》在權利保障與規制職權方面具有積極意義的諸多規定,關于非法證據的排除等程序性法律后果的規定,應當在實踐中嚴格貫徹落實;而且,我國刑事訴訟法律制度及刑事證據法的進步并不能因此而告一段落,應在新的起點上作進一步的努力。
注釋:
[1]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的名言:“權利法案的絕大部分條款都與程序有關,這絕非毫無意義。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和隨心所欲或者反復無常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差異。”《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任東來等著,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頁。
[2]參見王敏遠:《輕程序現象、原因及對策》,載《法學研究》1994年第4期、《違反刑事訴訟法的程序性法律后果》,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5期。
[3]當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曾在司法解釋中,對采用刑訊逼供的方式獲得的言詞證據,規定了應予以排除。然而,這些規定在現實中卻并未發生應有的作用。
[4]參見王敏遠:《違反刑事訴訟法的程序性法律后果》,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5期。
[5]參見王敏遠:《設置刑事程序法律后果的原則》,載《法學家》2007年第4期。
[6]當然,筆者無意鼓勵辯護方采用非法方法搜集證據。對于采用非法方法搜集證據的,應按照相關法律予以處理。但這與非法證據的排除是兩回事。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的觀點在筆者為參加2010年刑事訴訟法學會撰寫的論文中已有表達,在此作了少量文字補充[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