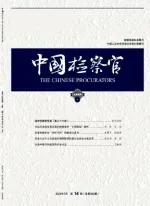訴訟詐騙之定性分析
文◎閆 雨* 黃華生*
訴訟詐騙之定性分析
文◎閆 雨* 黃華生*
一、基本案情
2007年8月24日,江西美江醫(yī)藥有限公司(以下簡(jiǎn)稱美江公司)總經(jīng)理梅某因資金周轉(zhuǎn)問(wèn)題向徐某借款25萬(wàn)元人民幣,并約定一個(gè)月后歸還。到期后,徐某多次討要未果,便萌發(fā)報(bào)復(fù)梅某的想法,復(fù)印了該張借條,2008年5月初徐某利用其妻替美江公司辦理貸款保存美江公司印章之機(jī),在借條的原件上加蓋美江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章,然后又找到律師
雷某商量,共同偽造了以美江公司為擔(dān)保人的協(xié)議書并加蓋美江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章。2008年5月16日,梅某連本帶息共計(jì)32萬(wàn)元人民幣還給了徐某,徐某則將復(fù)印偽造的借條還給了梅某。2008年5月19日,雷某在明知梅某已經(jīng)將欠款全部還給徐某后,仍幫助徐某以加蓋美江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梅某印章的借條原件及偽造的協(xié)議書,向南昌市西湖區(qū)人民法院以借貸糾紛為由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美江公司還款共計(jì)557500元。法院依法受理后,根據(jù)徐某的申請(qǐng)將美江公司的資金賬戶凍結(jié),導(dǎo)致美江公司經(jīng)營(yíng)困難。后來(lái)查明,這是一起徐某和雷某策劃實(shí)施的訴訟詐騙案。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rèn)為,徐某、雷某構(gòu)成詐騙罪(未遂)。理由是訴訟詐騙屬于三角詐騙,宜將該行為定性為詐騙罪。
第二種意見認(rèn)為,徐某無(wú)罪,雷某構(gòu)成幫助偽造證據(jù)罪。理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 《關(guān)于通過(guò)偽造證據(jù)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cái)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wèn)題的答復(fù)》作了相關(guān)規(guī)定。
第三種意見認(rèn)為,徐某、雷某無(wú)罪。理由是幫助偽造證據(jù)罪情節(jié)嚴(yán)重?zé)o明文規(guī)定,該案詐騙未成功,情節(jié)未達(dá)嚴(yán)重,因此,徐某、雷某均不構(gòu)成犯罪。
三、評(píng)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
(一)以詐騙罪定性之理由
徐某、雷某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訴訟詐騙行為。所謂訴訟詐騙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提起民事訴訟為手段,提供虛假的陳述,出示虛假的證據(jù),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決,從而獲得財(cái)產(chǎn)或財(cái)產(chǎn)上利益的行為。雖然訴訟詐騙與普通詐騙存在一些差異,但僅是外在表現(xiàn)形式不同,并不影響其行為的詐騙性質(zhì)。結(jié)合我國(guó)刑法關(guān)于詐騙罪規(guī)定和刑法理論,把訴訟詐騙作為詐騙罪處理是完全合理的。理由如下:
首先,行為人實(shí)施的被騙人與被害人并非同一人的訴訟詐騙的主要客體與詐騙罪的客體沒(méi)有區(qū)別。我國(guó)刑法學(xué)界大多數(shù)觀點(diǎn)認(rèn)為訴訟詐騙行為既妨害了司法機(jī)關(guān)的正常活動(dòng)又侵犯了公私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筆者認(rèn)為,訴訟詐騙行為是侵犯了雙重社會(huì)關(guān)系,但仔細(xì)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該行為所重點(diǎn)侵害的法益應(yīng)該是公私財(cái)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對(duì)于復(fù)雜客體的問(wèn)題主要看刑法側(cè)重哪一方面的保護(hù)。對(duì)于侵犯復(fù)雜客體的犯罪,完全可能按其侵犯的主要客體進(jìn)行處罰。典型的如刑法關(guān)于搶劫罪的規(guī)定。同理,就訴訟詐騙而言,行為人根本目的在于非法占有公私財(cái)產(chǎn)及財(cái)產(chǎn)性利益,其所實(shí)施的一系列妨害司法機(jī)關(guān)正常活動(dòng)的行為均是為其根本目服務(wù),所以訴訟詐騙的主要客體與詐騙罪的客體沒(méi)有區(qū)別。就本案而言,徐某、雷某偽造一系列虛假證據(jù)的行為雖然妨害了司法機(jī)關(guān)的正常活動(dòng),但是其根本目的在于通過(guò)這些偽造的證據(jù)非法取得被害人梅某的財(cái)產(chǎn),所以其所侵犯的主要是梅某的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從這點(diǎn)上看,徐某、雷某的訴訟詐騙行為符合詐騙罪對(duì)于犯罪客體的要求。
其次,從詐騙罪的主客觀方面看,訴訟詐騙也完全符合詐騙罪的主客觀構(gòu)成要件。本罪客觀方面表現(xiàn)為行為人以虛構(gòu)事實(shí),隱瞞真相的方法欺騙他人,使他人陷入錯(cuò)誤,并使之處分財(cái)產(chǎn)的行為。對(duì)于詐騙的方法手段刑法并沒(méi)有作出限制,只要足以使對(duì)方陷入錯(cuò)誤認(rèn)識(shí)即為刑法意義上的欺騙。由于詐騙罪侵犯的是公私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所以受騙者與被害人是否必須為同一人不是成立詐騙罪所必須的內(nèi)容。由此可知這里的 “對(duì)方”并不限于財(cái)物的被害人,一切具有處分財(cái)產(chǎn)權(quán)限或處于可以處分財(cái)產(chǎn)地位的人均可以成為受騙者。詐騙罪的基本構(gòu)造是:“行為人實(shí)施欺騙行為——對(duì)方 (受騙者)產(chǎn)生錯(cuò)誤認(rèn)識(shí)——對(duì)方基于錯(cuò)誤認(rèn)識(shí)處分財(cái)產(chǎn)——行為人或第三者取得財(cái)產(chǎn)——被害人遭受財(cái)產(chǎn)損害。”[1]對(duì)于訴訟詐騙而言,行為人主觀上基于非法占有他人公私財(cái)產(chǎn)目的,客觀上實(shí)施了虛構(gòu)事實(shí)或隱瞞真相的行為,虛構(gòu)了與被害人之間根本不存在的民事關(guān)系,向法院提起虛假的民事訴訟,在這里法官雖然不是被害人,但是法官具有財(cái)產(chǎn)處分的權(quán)力,因此這一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詐騙行為,至于訴訟詐騙中被騙人是法官而非被害人這一點(diǎn)并不能否認(rèn)行為人成立詐騙罪。詐騙罪的本質(zhì)體現(xiàn)在基于他人意思瑕疵而取得財(cái)物,其手段并沒(méi)有限制。通過(guò)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獲得他人財(cái)產(chǎn)只是一種欺騙的手段,法官基于錯(cuò)誤的認(rèn)識(shí)處分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使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受到損失,但是從根本上講,被害人遭受財(cái)產(chǎn)損失的真正原因是因?yàn)樾袨槿说奶摷僭V訟行為所導(dǎo)致,行為人的訴訟詐騙行為與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損失之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guān)系。對(duì)于訴訟詐騙而言,行為人以虛假的證據(jù)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法官產(chǎn)生錯(cuò)誤認(rèn)識(shí)——法官基于虛假證據(jù)作出處分裁判——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cái)產(chǎn)——被害人依照判決交付財(cái)產(chǎn)。因此訴訟詐騙與詐騙罪的本質(zhì)相同,都具有“騙”的根本屬性,其本質(zhì)都是基于他人的意思瑕疵而取得財(cái)物,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gòu)成要件。本案中,徐某、雷某虛構(gòu)了一個(gè)根本不存在的借款事實(shí),并偽造一系列虛假證據(jù)加以證明,妄圖通過(guò)法院的判決非法占有被害人梅某的財(cái)產(chǎn),完全符合詐騙罪的主客觀構(gòu)成要件。
最后,《刑法》第266條對(duì)詐騙罪采取了簡(jiǎn)單罪狀的規(guī)定方式,即“詐騙公私財(cái)物,數(shù)額較大的”就構(gòu)成犯罪。至于詐騙的具體方式,刑法未作限制,也就是說(shuō)詐騙的具體方式是開放性的,可以多種多樣。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許多新型的詐騙隨之出現(xiàn),其詐騙手段多種多樣,但其本質(zhì)并沒(méi)有改變,因此把訴訟詐騙行為歸入第266條詐騙罪當(dāng)中并不違背詐騙罪的立法精神,同時(shí)也并不會(huì)超出人們對(duì)法律的預(yù)見。
(二)以幫助偽造證據(jù)罪定性之不妥
在正面論證了本案應(yīng)當(dāng)以詐騙罪定性之后,以下還有必要對(duì)本案定性的第二種意見即主張以幫助偽造證據(jù)罪定性的意見進(jìn)行否定性分析。
對(duì)于訴訟詐騙問(wèn)題,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通過(guò)偽造證據(jù)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cái)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問(wèn)題的答復(fù)》(以下簡(jiǎn)稱《答復(fù)》)指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guò)偽造證據(jù)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cái)物的行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dòng),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guān)規(guī)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zé)任。如果行為人偽造證據(jù)時(shí),實(shí)施了偽造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印章、人民團(tuán)體印章的行為,構(gòu)成犯罪的,應(yīng)當(dāng)依照《刑法》第280條第2款的規(guī)定,以偽造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人民團(tuán)體印章罪追究刑事責(zé)任;如果行為人有指使他人作偽證行為,構(gòu)成犯罪的,應(yīng)當(dāng)依照《刑法》第307條第1款的規(guī)定,以妨礙作證罪追究刑事責(zé)任。”這一答復(fù)是本案第二種定性意見的主要依據(jù)。但是,筆者認(rèn)為,本案以幫助偽造證據(jù)罪定性存在以下明顯不妥:
第一,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答復(fù)》完全忽視了對(duì)于被害人財(cái)產(chǎn)的保護(hù),同時(shí)也是對(duì)詐騙罪構(gòu)造的誤解,其不合理之處顯而易見。依據(jù)《答復(fù)》,對(duì)于訴訟詐騙要么做無(wú)罪處理,要么以偽造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人民團(tuán)體印章罪定罪處罰,要么以妨害作證罪或幫助毀滅、偽造證據(jù)罪定罪處罰。根據(jù)《刑法》第280條第2款規(guī)定偽造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人民團(tuán)體印章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剝奪政治權(quán)利”。對(duì)于妨害罪證罪《刑法》第307規(guī)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jié)嚴(yán)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工作人員犯本款的從重處罰”。對(duì)于幫助毀滅、偽造證據(jù)罪《刑法》第307條第2款規(guī)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刑法》第266條對(duì)詐騙罪的處罰規(guī)定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yán)重情節(jié)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yán)重情節(jié)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wú)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méi)收財(cái)產(chǎn)。訴訟詐騙的社會(huì)危害性已經(jīng)超出社會(huì)的容忍限度,其危害性與普通詐騙相比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如果按照此《答復(fù)》處理案件必將導(dǎo)致重罪輕判,違背刑法罪責(zé)刑相適應(yīng)原則。
第二,本案以《答復(fù)》作為定罪的依據(jù)將導(dǎo)致荒謬的結(jié)論。從案件事實(shí)來(lái)看,徐某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雷某僅起次要作用。如果認(rèn)定徐某無(wú)罪,而對(duì)雷某定幫助偽造證據(jù)罪,顯然極不合理,這種司法結(jié)論有損刑法的公平正義。順帶指出,就《刑法》第307條第2款規(guī)定的幫助毀滅、偽造證據(jù)罪而言,在立法上也是有缺陷的。刑法僅對(duì)當(dāng)事人以外的人幫助毀滅、偽造證據(jù)的行為做否定性評(píng)價(jià),但對(duì)當(dāng)事人本人毀滅、偽造證據(jù)的行為卻未加以規(guī)定,從邏輯上講主次顛倒,這種設(shè)置顯然是不合理的。幫助毀滅、偽造證據(jù)罪中使用“幫助”一詞很容易讓人們誤解為共同犯罪中的幫助犯,其實(shí)幫助毀滅、偽造證據(jù)罪當(dāng)中的“幫助”與共犯中幫助犯中的“幫助”并非同等含義,幫助毀滅、偽造證據(jù)罪中的“幫助”是指一種實(shí)行行為,本罪使用幫助一詞是為了和當(dāng)事人本人實(shí)施毀滅、偽造證據(jù)的行為相區(qū)別,但是“幫助”一詞的使用導(dǎo)致懲治當(dāng)事人本人毀滅、偽造證據(jù)發(fā)生困難,是一個(gè)明顯的立法缺漏。由于本案適用《刑法》第307條第2款規(guī)定將導(dǎo)致極不合理的結(jié)論,所以不宜照搬《答復(fù)》適用該規(guī)定。
第三,《答復(fù)》只是一種指導(dǎo)性的意見,并非司法解釋,對(duì)司法機(jī)關(guān)的案件辦理不具有約束力。各級(jí)司法機(jī)關(guān)在辦理案件中,對(duì)于上級(jí)機(jī)關(guān)的指導(dǎo)性意見應(yīng)當(dāng)進(jìn)行具體分析,不宜簡(jiǎn)單地照搬照套。在司法實(shí)務(wù)中,很多法院對(duì)訴訟詐騙行為正確地定性為詐騙罪,而并沒(méi)有根據(jù)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的《答復(fù)》這種非司法解釋,效力也值得懷疑的文件處理案件,這是應(yīng)當(dāng)加以肯定的做法。[2]例如,2006年,上海市金山區(qū)的王連豐先后11次通過(guò)偽造欠條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騙取他人財(cái)產(chǎn),結(jié)果被上海市金山區(qū)人民法院以詐騙罪定罪判刑。[3]
(三)按無(wú)罪處理之不當(dāng)
至于本案的第三種意見認(rèn)為徐某、雷某無(wú)罪,其主要理由是詐騙未成功,情節(jié)未達(dá)到嚴(yán)重。筆者對(duì)這種審理意見是不能接受的。根據(jù)我國(guó)刑法規(guī)定,詐騙公私財(cái)產(chǎn)數(shù)額較大的,才構(gòu)成犯罪。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詐騙未遂的一律不夠成犯罪。詐騙未遂情節(jié)嚴(yán)重的,也應(yīng)當(dāng)定罪并依法處罰。本案中徐某、雷某的訴訟詐騙行為導(dǎo)致了法院將美江公司的資金賬戶凍結(jié),就已經(jīng)侵害了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至少對(duì)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造成了一定的威脅。徐、雷二人的行為導(dǎo)致梅某的美江公司經(jīng)營(yíng)困難,就已經(jīng)造成了嚴(yán)重后果。再者徐某、雷某的行為所具有的社會(huì)危害性也達(dá)到科處刑罰的程度,所以判定其無(wú)罪是完全沒(méi)有道理的。
綜上所述,本案訴訟詐騙行為雖然與普通詐騙有所差異,但僅僅是外在表現(xiàn)形式的不同。形式上的不同并不影響訴訟詐騙行為的詐騙本質(zhì)。訴訟詐騙不過(guò)是詐騙罪中一種比較新型的、特殊的形式。對(duì)于訴訟詐騙案件而言,將其定為詐騙罪符合刑法的規(guī)定和刑法的精神,同時(shí)也有利于堅(jiān)持罪責(zé)刑相適應(yīng)原則。
注釋:
[1]張明楷:《刑法學(xué)(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第735頁(yè)。
[2]陳興良、周光權(quán):《刑法學(xué)的現(xiàn)代展開》,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652頁(yè)。
[3]中央電視臺(tái)一套 2007年 5月 15日《今日說(shuō)法》欄目的節(jié)目《神秘的欠條》披露了王連豐訴訟詐騙一案。在節(jié)目中,主持人撒貝寧和全國(guó)律協(xié)法律援助與公益法律事務(wù)委員會(huì)副主任佟麗華都認(rèn)為對(duì)王連豐以詐騙罪定性沒(méi)有問(wèn)題。資料來(lái)源:中顧網(wǎng)http://www.9ask.cn/Blog/user/lawyerlcl/archives/2007/23240.html,瀏覽日期:2010年6月12日。
*江西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法學(xué)院[33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