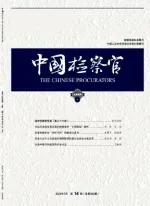因他人告發而要求賠償損失未成,強迫他人打欠條還款行為如何定性
文◎周清水 朱梁雙
因他人告發而要求賠償損失未成,強迫他人打欠條還款行為如何定性
文◎周清水*朱梁雙**
一、基本案情
王某因賭博被鄰居李某告發,公安機關當場將王某抓獲,后王某因賭博被拘留15天,罰款6000元。王某從拘留所出來后,得知是因為李某告發后,懷恨在心,總想找機會報復。一天,王某糾集他人闖入李某的住房,對李某一陣拳打腳踢后,讓李某賠償自己所遭受的罰款與拘留期間的誤工損失,共計8000元。李某稱自己沒錢,王某等又對李某拳打腳踢,并在李某家中翻箱倒柜尋找錢財未果后,讓李某打一欠條,欠條內容為:今欠王某人民幣8000元,遲延利息2000元,共計10000元,三個月內歸還。王某等人離開后,李某立即報警。后王某被公安機關抓獲。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王某之所以向李某索要錢財,是因為李某告發王某賭博,致使王某遭受一定經濟損失,王某向李某索要錢財是為了賠償王某損失,雙方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盡管是非法的債權、債務關系)。王某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觀上盡管對李某采用了暴力行為,但是并沒有導致李某輕傷的后果,因此本案王某是一種索取債務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第二種意見:盡管王某所遭受的損失與李某的告發行為有關,但雙方并不存在債權、債務關系,王某以此為借口,要求李某賠償損失并出具欠條,總體上是一種敲詐行為,應成立敲詐勒索罪。
第三種意見:王某糾集他人當場使用暴力,向李某索要錢財,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應成立搶劫罪。只是因為李某沒有錢財,才讓李某出具欠條,但這并不影響王某搶劫的故意與行為,只不過涉及到搶劫未遂的問題。
第四種意見:本案王某的行為應該分兩個階段考慮:第一階段王某對李某毆打后向李某索要錢財的行為應成立搶劫罪(未遂)。搶劫未成,逼迫李某打欠條行為應成立敲詐勒索罪(未遂)。由于王某是在一個侵財故意下連續實施的兩個行為,可以按照吸收犯的原理,對王某按照搶劫罪(未遂)一罪處理。
三、評析意見
筆者一方面同意第四種意見所主張的王某的行為應成立搶劫罪(未遂)與敲詐勒索罪(未遂),另一方面認為本案不能按照吸收犯原理對王某擇一重罪處罰,而應該實行數罪并罰,理由如下:
本案主要涉及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的區分以及對吸收犯的理解問題。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財物的所有人或者保管人以日后的侵害行為相威脅,當場或者日后占有其數額較大財物,或者以當場實施暴力相威脅,迫使被害人日后交付數額較大財物的行為。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財物的所有人或者保管人采用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當場劫取他人財物的行為。從兩罪的定義看,兩者主觀上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觀上都有可能使用暴力、脅迫行為,特別是對一些勒索性的搶劫行為和一些暴力型的敲詐行為經常會出現一些認識上的分歧。但是只要抓住兩罪的本質,不難將兩罪作出正確的區分。就本案事實而言,應該就王某犯罪發展的兩個階段進行不同的分析與定性。
(一)王某糾集他人采用暴力手段,當場向李某索要錢財用于賠償損失的行為應成立搶劫罪
本案王某是否構成犯罪主要涉及財產犯罪與索取債務行為的區分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19日下發的《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行為人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從該司法解釋可以明確看出,如果雙方確實存在一定債權、債務關系 (某種情況下包括非法的債權、債務關系,如賭債),當行為人行使權利獲得某種財產利益時,可以排除其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從而不能構成財產犯罪。如果行為人不當地行使權利,其手段行為或者方法行為觸犯了刑法的其他罪名時,應該按照手段行為或者方法行為定罪處罰,而不能按照財產犯罪處罰。本案中盡管王某向李某索要錢財是為了賠償王某因李某告發王某賭博事實而造成的各種損失,但是向國家機關控告各種違法行為是每個公民的合法權利與義務,違法者對自己的違法行為承擔一定的法律后果是法律的必然要求。李某的告發行為并不會在雙方之間產生實質意義上的債權、債務關系。要求李某賠償損失僅僅是王某隨意尋找的一個借口,這一點王某應該明確的知道無論從法律上還是社會習慣上,李某都不應該對其所遭受的損失承擔任何責任。因此,盡管本案存在一定的前因,但并不能否定王某等人主觀上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王某等人采用暴力手段,強行要求他人賠償不應由他人賠償的損失,客觀上侵害了他人的財產權利,依法應成立搶劫罪(未遂)。
(二)王某當場索要財物未成,強迫李某打欠條還款的行為應成立敲詐勒索罪
在暴力性的搶劫和暴力性的敲詐勒索中,對于定性問題常常會引起一定分歧,特別是司法實踐中經常把通俗話語中的 “敲詐”理解成刑法中的敲詐勒索行為,導致許多情況下將一些尋找借口,當場采用暴力、脅迫行為并當場取得財物的勒索性的搶劫行為都認定為敲詐勒索罪,而不是認定為搶劫罪,從而放縱了犯罪人。事實上,正確區分暴力性的搶劫和暴力性的敲詐勒索行為,關鍵在于對行為人取得被害人財物方式的理解,具體講是關系到對“兩個當場”的理解。搶劫罪要求必須是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當場取得財物,“兩個當場”缺一不可,才能構成搶劫罪。而敲詐勒索罪則要求不能同時具備“兩個當場”,主要包括兩種情形:第一,以日后的侵害相威脅,當場取得被害人財物;第二,以當場實施暴力相威脅,逼迫被害人日后交付財物。一般的講,搶劫罪的暴力行為在于壓制對方的反抗,使對方不敢或者不能反抗,從而當場交付財物。敲詐勒索罪的暴力行為在于給對方施加心理上的壓力,迫使對方承諾日后交付財物,使對方在交付財物的時間上具有一定的選擇自由。如果行為人預謀敲詐,但是其所實施的暴力行為足以壓制被害人的反抗,是被害人除了當場交付財物而別無選擇時,則應認為行為人以搶劫方式實現了其取得財物的目的,行為人的行為應認定為搶劫行為。因此,兩罪區分的關鍵在于行為人的暴力行為是否壓制了被害人的反抗,從而使被害人對于當場或者日后交付財物是否具有一定的選擇自由。本案中,王某采用暴力手段索要錢財未成后,又采用暴力手段,使不欠自己債務的李某當場寫下欠條,承諾日后歸還,因為王某只是當場取得欠條并未當場取得有經濟價值的財物,同時欠條也無法律上的效力,王某追求的只是通過欠條讓李某日后交付財物,因此,王某的行為應成立敲詐勒索罪(未遂)。
(三)對王某應按照搶劫罪(未遂)與敲詐勒索罪(未遂)數罪并罰
吸收犯是指實施了數個不同的犯罪行為,其中一個行為吸收其他行為,只成立吸收行為一個罪名的犯罪。成立吸收犯,要求數行為之間具有密切關系,具體表現為行為人所實施的數個犯罪行為屬于實施某種犯罪的同一過程,前行為可能是后行為發展的所經階段,后行為可能是前行為發展的自然結果。例如,行為人盜竊槍支后,私藏在家里,這里行為人有兩個行為,一是盜竊槍支的行為,構成盜竊槍支罪;二是私藏槍支的行為,構成私藏槍支罪。私藏槍支行為是盜竊槍支行為的必然發展結果,應被盜竊槍支行為所吸收,行為人僅成立盜竊槍支罪。當然,我國法律對于吸收犯缺少明確規定,實踐中對于吸收犯的處理主要依靠法學理論的指導。處理吸收犯時,應注意我國刑法規定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如果我們一定要按照吸收犯原理對行為人按照搶劫8000元未遂的事實定罪處罰,將無法評價其敲詐多于搶劫預謀數額2000元的犯罪事實,明顯違背了我國刑法規定的罪責行相適應原則。本案中王某在搶劫未遂,不能當場取得財物情況下,為了日后取得財物,逼迫李某打欠條承諾日后還款行為,并非先前搶劫行為的必然發展結果,兩行為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逼迫打欠條還款行為是行為人在原來犯罪未能成功情況下,產生新的犯意,實施的新的犯罪行為,應該成立新的犯罪,兩個犯罪之間不能存在吸收行為。最高人民法院 《關于搶劫過程中故意殺人案件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中明確指出,行為人實施搶劫后,為滅口而故意殺人的,以搶劫罪和故意殺人罪定罪,實行數罪并罰。同理,本案王某搶劫未遂后臨時改變犯意,采用暴力行為逼迫他人打欠條,敲詐他人的,也應該數罪并罰。本案對王某應按照搶劫罪(未遂)與敲詐勒索罪(未遂)數罪并罰。當然,王某的搶劫行為屬于入戶搶劫,應適用較重的刑罰。
*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檢察院[450003]
**西北政法大學[71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