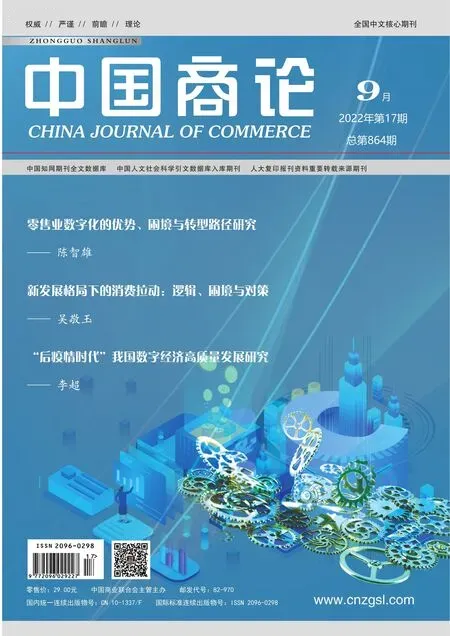中國企業投資哈薩克斯坦的法律風險防范及解決途徑
新疆財經大學法學院 王婧
中國企業投資哈薩克斯坦的法律風險防范及解決途徑
新疆財經大學法學院 王婧
近年來,中國與中亞五國的龍頭老大—— 哈薩克斯坦經濟貿易往來十分頻繁,哈國已經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因此,本文闡釋投資哈國的法律依據,分析、探索中國企業投資哈國的法律風險以及解決爭議的措施,旨在為中國企業在哈國投資提供法律幫助。
中國企業 哈薩克斯坦 投資的法律風險 防范及解決
哈薩克斯坦作為中亞五國之一,其綜合國力和經濟發達程度居中亞五國之首。近年來,我國與哈方的經濟貿易往來頻繁。隨著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在能源、礦產、電信等項目上開發和進出口規模的擴大,今后相當一段時期中國與哈方的投資貿易將會繼續保持穩定的快速增長態勢。因此,研究哈國的法律與政策,防范由此帶來的法律風險十分必要。
1 中國企業投資哈國的主要法律依據
中國與哈國的投資和經貿合作,主要是根據多邊國際條約、合作方簽訂的協議、合作方的國內法以及國際慣例來實施。
1.1 多邊國際條約為中國投資哈國搭建了基礎性框架
中國與中亞國家中合作的哈、吉、塔、烏均為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因此它們在上合組織框架下達成的一系列政府間協議,構成了它們之間開展經貿合作的基礎性法律文件。此外,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同參加的某些多邊國際條約也構成雙方經貿合作的法律基礎。
1.2 政府間協議和企業間協議是中國投資哈國最重要的法律依據
政府間協議是由合作方的政府簽訂,屬于國家之間的條約,在簽約國之間發生法律效力。近年來中國政府與哈國簽訂了多個雙邊協議,比如中國政府與哈薩克斯坦國政府簽訂的《關于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合作的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政府關于中哈天然氣管道建設和運營的合作協議》、中哈《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等,這些政府間的雙邊協議都是中國與哈國開展經貿合作的法律根據。 企業之間的協議直接規定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在法律上相當于合同,約束的是企業的經營行為。依據企業間協議所實施的能源勘探、開采等行為一般由資源國法律調整。這類協議包括: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哈薩克斯坦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簽訂的《關于中哈天然氣管道建設和運營的基本原則協議》等。
1.3 哈國的國內法也是調整中方投資的重要依據
在以直接投資方式進行的經貿合作中,東道國的法律是規范外來投資者經營行為的主要依據。但哈國的法律穩定性不夠,修改的頻率高,容易影響投資者的利益。如哈薩克斯坦在2004年、2005年和2007年先后三次修改《地下資源和地下資源利用法》,不斷強化國家對資源的控制,以爭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該法的不斷修改和補充使以前簽訂的石油合同增加了變數。盡管哈薩克斯坦高層領導多次保證,對已經進入其國內石油開采領域的外國企業,不存在改變“游戲規則”的問題,但是2007年修訂的《地下資源與地下資源利用法》已經明確規定“本修改法自正式頒布之日生效,并對以前簽訂的開采合同或者聯合勘探和開采合同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具有效力”。可以看出,哈薩克斯坦政府通過修改和補充法律,在不斷擴大對已簽署合同的控制力。
2 中國企業投資哈國的法律風險
為了拓展國際市場,進軍哈國進行投資和國際經貿合作,中國企業的投資決策者們應當事前對投資中可能遇到或將要遇到的各種法律風險進行研究分析、控制和防范。
2.1 執法不規范,對外經濟政策頻繁調整的風險
哈國在經貿和投資方面法律法規多變且不健全,在解決具體問題時,則常以總統令、 內閣規定等文件來調節外商和外國投資在其國內的活動。頻繁的總統令和內閣文件往往是后面否定前面的政策,多變的政策影響了投資環境的穩定,影響了投資者決策。 政府有關部門的執法隨意性較大,影響了中資企業在哈國的貿易和投資活動。因此,中國企業投資哈國必須要慎重決策,仔細研究調查被投資國的稅收政策和對外的經濟政策及法律。
2.2 貿易壁壘的風險
(1)從關稅及關稅管理的措施來看。哈對部分進口產品所征收的關稅稅率遠遠高于8.6%的關稅平均水平,如糖類稅率為30%、肉類熟食為30%等。
(2)從通關環節壁壘來看。自 2002年10月起,哈授權第三方機構對進口貨物進行“海關審計”,并以國際價格為基礎確定進口貨物的海關價值,導致部分通關貨物的海關價值高估。通關時,必須提供哈海關和中央銀行用以監督貿易過程中資金使用情況的“交易護照",否則不予放行,通關手續繁瑣徒增了通關成本和風險,對我國企業通關貨物構成實質性壁壘,須引起中方企業重視。
(3)從技術性貿易壁壘來看。哈對部分進口商品做出了特別檢測規定,即中國企業向其出口的機電產品,都必須通過哈標準化、度量衡和檢測中心進行的國家安全檢測,以確認其對人體健康、財產及生態環境是否有害。由于中哈兩國產品的技術標準不同,哈的特別檢測必然加重中方企業的負擔。
(4)從服務貿易壁壘來看。哈《建筑法》規定,外國投資者可以合資企業的形式進入哈建筑業,但外資在建筑合資企業中的持股比重不得超過49%。
(5)哈銀行信譽程度不高,信貸能力較低,會計、保險、審計、信息等服務領域發展滯后,不能為外商提供高質量服務,且對外資銀行的準入有限制性規定。哈規定外資銀行的資本份額不得超過國內所有銀行總資本的25%。哈還規定外資銀行的監事會中至少有1名具3年以上銀行工作經驗的哈公民,至少70%以上的外資銀行員工為哈公民。
這些不平等的法律規定直接對外資企業的生產經營和服務活動構成了壁壘。
2.3 投資壁壘的風險
(1)從礦產投資壁壘來看。哈薩克斯坦2005年修改的《礦產法》規定,企業在準備轉讓礦產開發權、直接收購或出賣哈薩克斯坦石油公司股份時,需要到哈能源和礦產資源部審批,而哈能源和礦產資源部在發放許可證時有權拒絕發放許可證,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2006年11月,中國中信集團在收購加拿大內森斯能源在哈薩克斯坦的石油資產時,哈方以“注冊地不在哈薩克斯坦但資產在哈國境內的石油天然氣公司在轉讓股份時,也必須獲得哈政府的批準”為理由要求中信集團暫停收購。哈薩克斯坦的上述做法損害了中國企業的投資利益,也對收購哈薩克斯坦國內礦產企業構成了實質性障礙。
(2)哈薩克斯坦政府規定,在哈薩克斯坦開采石油、天然氣及其他地下礦產資源的外資企業必須與哈政府簽訂地下資源使用合同。哈政府向企業提供的合同有兩種,一種是海上石油項目產品分成協議,一種是超額利潤稅協議。海上石油項目產品分成協議主要適用于海上石油開采項目,規定外國投資者在哈境內開發海上石油時,在項目投資回收期前哈國所占的利潤份額最低比例為10%;投資回收期后,哈國所占的利潤份額最低比例為40%。其中投資回收期為25年或30年。在超額利潤稅協議下,外國投資者必須繳納15%~60%不等的超額利潤稅。這一規定使投資回收期滿后哈國所占利潤過高,制約了投資企業的預期收益。
(3)從土地投資壁壘來看。哈2003年頒布的《土地法》規定,哈本國公民可以擁有農業、工業、商業用地和住宅用地;外國自然人和企業只能租用農業用地,租期不得超過10年。過短的土地租期往往使投資者難以放心投入,長期合作發展。
2.4 人力資源壁壘的風險
哈對國外勞務實行嚴格限制,外國人在哈取得勞動就業許可和居留許可較困難。哈薩克斯坦以配額形式限制外國勞動力的進入,不僅申辦獲取引入外國勞動力許可證的程序十分繁瑣,而且許可證的數量還有限制。目前,哈對外國員工申請勞動許可的規定仍舊是阻礙外國投資的主要壁壘之一。這也使外資企業在哈國選擇勞動力面臨著很大的制度風險。
3 如何解決中國投資哈國發生的爭議
3.1 用國際公約或國際慣例來解決爭議
當爭議發生時,如果被投資國的本國法與投資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公約相沖突,則通行的做法是適用國際公約。例如,哈薩克斯坦《石油法》規定:適用《石油法》和《礦產資源使用法》時,不能與哈薩克斯坦參加或締結的國際公約的規定相抵觸;哈薩克斯坦《投資法》也規定,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批準的國際協議優先于國家法律。在資源國本國法與國際公約都沒有規定的情況下,適用國際慣例。
3.2 用被投資國的法律來解決爭議
盡管存在政府間的協議,但中國對哈國的投資合作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要靠簽訂、履行各種合同來具體落實,這些合同在主體、內容和客體方面存在著涉外因素。如果當事人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發生爭議,經過協商仍不能解決,且不同國家的法律對同一合同問題有不同的規定,那么適用不同國家的法律就可能導致不同的處理結果,這就產生了解決爭議究竟應當適用哪個國家的法律的問題。基于自然資源主權原則,考慮到本國的經濟和社會利益,被投資國政府往往會對爭議的法律適用進行國家干預,直接規定適用本國法,排除外國法的適用。例如哈國政府在同外國石油公司簽訂的石油勘探開發合同中,其適用法律條款就規定:本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本合同條款中的優先權是由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現行法律基礎嚴格確定的。
3.3 用當事人選擇的法律來解決爭議
投資涉及到的法律關系類型眾多,紛繁復雜,并非所有爭議都必須適用被投資國的法律解決,在沒有相反法律規定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一般情況下,當事人應當采用明示的方式選擇法律;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還可以變更以前的選擇;當事人選擇法律不能規避強行法的適用,即當事人只能選擇作為實體法的任意法。
4 中國投資哈國發生爭議的解決方式
4.1 外交或政治的方法
外交或政治的解決方法包括談判、斡旋、調停、調解、國際調查以及在聯合國組織的指導下解決爭端。
4.2 仲裁的方法
我國和哈國的法律中都有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的規定。例如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投資法》就明確規定投資爭議可以通過國際仲裁法庭解決。
4.3 訴訟的方法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投資法》規定在投資糾紛通過談判無法解決時,通過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法院根據國際條約和現行法規,可通過雙方在協議中所確定的國際仲裁法庭來解決。
綜上所述,我國企業無論是在哈國投資或是與之進行經貿合作,都必須認真研究、熟悉哈國的法律和政策,以防范或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
[1] 中國商務部外貿發展事務局.中小企業外貿操作指南[M].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7.
[2] 烏魯木齊市貿易發展局.對外貿易政策法規匯編[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3] 哈薩克斯坦的《石油法》、《礦產資源使用法》、《礦產法》等.
F752
A
1005-5800(2010)08(c)-2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