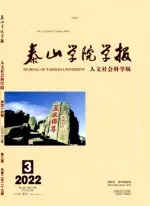再論秦漢以來我國鄉村基層行政的專制性
萬昌華
(泰山學院歷史系山東泰安 271021)
自 20世紀前期開始,中外學者中有人認為中國傳統郡縣型的行政體制之下,廣大的鄉村基層社會是自治的民主政治體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我國知名社會學家費孝通。
比費孝通“中國古代鄉村社會皇權——鄉紳二元模式”的觀點走得更遠,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上世紀初年造說認為,傳統政治之下中國的皇權統治根本就出不了都市地區和次都市地區。韋伯說:“事實上,正式的皇權統治只施行于都市地區和次都市地區。……出了城墻之外,統治權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減弱,乃至消失。”[1](P110)另外,日本學者和田清上世紀七十年代也著有《中國地方自治發達史》一書,專門講中國所謂的“發達的地方自治”。[2]
本人認為,以上諸人的中國中古時期鄉村社會是自治的二元的民主社會的觀點與秦代以來我國鄉村基層社會的歷史實際相背離。另外,如丘吉爾所言,書寫歷史也就是在創造歷史。以上諸人如此的忽悠中國中古時期鄉村社會的歷史,會給我們當下基層農村的政治社會建構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對有關的史實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澄清與分析梳理。
這個工作本人之前已在進行。比如,2008年9月齊魯書社出版了拙著《秦漢以來基層行政研究》(與興彬合著),今年 1月同出版社又出版了拙著《秦漢以來地方行政研究》。從網上可以看到,以上二書現已銷往北美、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東南亞和港臺地區。本文是以上二書中論題的繼續。
一
從秦朝起,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我國廣大鄉村實行的是鄉里組織與亭組織,兩套并行的社會基層控制系統。其中,鄉里組織是基層行政控制系統,亭組織是縣府派駐到基層社會的主管治安的機構。這種對鄉村基層社會實行嚴厲控制的基層社會行政編組方式,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班固在《漢書·百官公卿表》的縣令條中寫道:“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繳。游繳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繳繳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我們后邊將要講到,班固這段話中關于當時鄉里基層行政組織的記述基本正確,但“亭”的記述不正確。“亭”是秦漢時期縣行政之下基層社會行政中的另一分支,主要管彈壓,是一種有別于當時正式鄉村基層社會行政的準基層行政機構。
《后漢書·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繳。”本注曰:“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后,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游繳掌繳循,禁司奸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關于亭,該志另作一條曰:“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與前引《漢書·百官公卿表》中有關的記載相比較,此種表述應更與事實相符。
鄉嗇夫是秦漢時期統治鄉村基層社會的主要鄉官之一,為秦國原來的舊制。此事可見于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田律》、《廐苑律》及《倉律 》。[3](P30,P36)
秦漢時期的另一主要鄉官鄉三老也為秦制。《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自立為將軍、與吳廣率起義軍入據陳后,曾“號令召三老、豪杰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杰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由此可見,秦代的三老都是在鄉里有影響的人物。
漢代建立之后承襲秦制,鄉官制度繼續,同時又有所發展。一是如前引《后漢書·百官志》縣官條本注中所云,鄉嗇夫分成了兩種:有秩嗇夫與一般的縣置嗇夫。有秩嗇夫由郡府任命。有秩就是有官品、祿秩的意思。二是漢代三老有鄉三老和縣三老之分。
出土資料也清楚表明了西漢時期主要鄉官嗇夫有“有秩嗇夫”與一般嗇夫之分。據《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西漢末年東海郡共有 170個鄉;有鄉“有秩嗇夫”大約 28人,有一般鄉嗇夫137人。①東海郡的郡置鄉“有秩嗇夫”與縣置鄉嗇夫二者相加約是 165人,165人這個數字與東海郡有 170個鄉的數字非常接近。此事可以證明,兩漢時期雖然鄉“有秩嗇夫”與鄉嗇夫同是主要的鄉官,但二者不是一回事,他們分開設立,有“鄉有秩嗇夫”的鄉就沒有縣置鄉嗇夫,有縣置鄉嗇夫的鄉就不再設“鄉有秩嗇夫”的觀點正確。另外,從《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以上的有關內容看,當時鄉嗇夫中郡府任命的“有秩嗇夫”與一般縣置嗇夫的比例大約是 1∶6。
總之,以上史實充分表明了這樣幾點:鄉“有秩”是鄉“有秩嗇夫”的省稱,一般鄉嗇夫在級別上要低于鄉“有秩嗇夫”;二者雖秩級有別,但職能相同,都是一鄉的行政長官;每鄉或設“有秩嗇夫”,或設有一般嗇夫,沒有一鄉兩個嗇夫的。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鄉有“有秩嗇夫”,《續漢書·百官志》云鄉置“有秩”,這樣的簡單表述易使人產生歧義。如果再展開解釋一下的話,大概當時的鄉“有秩(嗇夫)”由郡任命,一般的鄉嗇夫由縣署,如同今天的鎮長、鄉長之設,同是鄉鎮的行政一把手,有鄉級鄉鎮干部與副縣級鄉鎮干部之別。所以如此,原因是不同秩級的官吏要由不同級別的行政主管部門管轄。副縣級級別的鄉鎮長要由地區級的組織部門任命,一般的鄉鎮長只要縣里任命就可以了。
要之,秦漢時期的鄉行政長官,不管是“有秩嗇夫”,還是一般的鄉嗇夫,都是在籍的皇家官員。用現在的話說,是吃“國庫糧”的脫產的“國家干部”。憑著這個基礎,他們完全可以在皇家的行政體系內繼續高升,有的還能當上大官。比如朱邑,宣帝時為舒桐鄉嗇夫,后官至大司農。[4]再比如張敞,以本鄉有秩補太守卒史,然后察廉為甘泉長。[5]
關于漢代設立三老的情況。《漢書·高帝紀》二年二月,“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戎。”這里的縣三老,似還是任職于具體的一個鄉,只是,有了縣三老名義的人身份比一般的鄉三老要高而已。以后此制有變化。
據史料,當時各地設立縣三老的情況普遍,并且以后還有了更高級別的三老——郡三老。《東觀漢記》:秦彭為山陽太守時曾“擇民能率眾者為鄉三老,選鄉三老為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郃陽令曹全碑陰》有“縣三老商量”、“鄉三老司馬集”題名。[6](P189)《后漢書·王景傳》:王景“父宏為郡三老。”
《漢書·百官公卿表》和《后漢書·百官志》都說鄉有游徼,言“徼循禁盜賊”或“徼循司奸盜”。但其他史籍所見游徼均直屬于縣廷。
《漢書·胡建傳》中有“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之句,《漢書·趙廣漢傳》中有“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置百石”之句。《漢書·黃霸傳》中言黃霸少時為“陽夏游徼”。《漢書·朱博傳》中有“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余,如律令”的記載。東漢時期,《后漢書·臧宮傳》中有“少為縣亭長、游徼”句。《后漢書·鄭均傳》引《東觀漢記》:“兄仲,為縣游徼。”《后漢書·王屯傳》:一女子訴某亭長枉殺其家人十余口后,“(眉令)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系,及同謀十余人惡伏辜。”以上所有這些關于游徼的記載均不言鄉。不但如此,有的還直稱某縣游徼,或縣游徼,或門下游徼。
門下游徼的稱謂又多見于碑刻。如《堂邑令費風碑》、《中部碑》不但有“門下游徼”的記載,而且還列于門下功曹之后,門下賊曹之前。[7]又如《蒼頡廟碑側》,左側有萬年左鄉、北鄉有秩,蓮勺左鄉、池陽左鄉有秩等等,門下游徼則在右側列于功曹和門下賊曹之間。[6](P202)
嚴耕望先生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一書的第五章《縣廷組織》中寫道:“鄉游徼即縣職之外部耳,碑傳所見游徼,其中或有出部者,惟同是縣吏,故統稱縣職歟?”[8](P228)安作璋、熊鐵基二先生則說:“可以認為,游徼是直屬于縣而派往各鄉徼巡者,……巡行于鄉以禁盜賊,故名。”二位據《五行大義》引用的翼奉話“游徼、亭長,外部吏,皆屬功曹”后指出,“游徼為縣職,是分部于各鄉的”縣令長的直屬吏員。[6](P202)以上三位先生的論斷正確,但仍有補充的必要——漢代游徼是縣令長的心腹屬吏無疑,但并不是各鄉都派駐。新出土資料表明,漢代各個縣的游徼數目與它們所擁有的鄉的數目不一致。此點更可進一步證明以上三位先生的論斷正確。
前已述及,據《尹灣漢簡·集簿》西漢末東海郡共有 170個鄉。但東海郡當時并非有如此多的游徼。總計,東海郡當時才共有游徼 82人,游徼的人數不能與東海郡的鄉數對應。從具體的記述上看亦如此。比如,海西縣是東海郡的大縣,有14個鄉,但只有游徼 4人;下邳縣次于海西,有 13個鄉,卻有游徼 6人。而厚丘縣的游徼相對而言人數更少,9個鄉才只有游徼 2人。厚丘縣平均 4個半鄉才有游徼 1人。
但是,當時東海郡卻是每縣都有游徼,最多的6人,最少的也有 1人,無一或缺。
從以下《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中各縣吏員的排列次序看,游徼是屬于縣主官令長直接管轄的縣府吏員無疑。比如其中記道:“海西吏員百七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游繳四人,牢監一人,尉史三人”;“下邳吏員百七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游繳六人,牢監一人,尉史四人”;“郯吏員九十五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游繳三人,牢監一人,尉史三人”。必須指出的是,以上的排列決不是無意的。肯定是有意為之。正是因為縣令、縣丞和縣尉在一縣之內的依次是一、二、三,所以才有了游徼、牢監和尉史地位排列的后一個一、二、三。總之,可以這樣認為,當時游徼是根據各縣的戰略地理位置以及各縣具體社會治安狀況而設立的,人數并不確定。由于當時游徼長期巡行于鄉間司奸捉盜,因而后人在記述有關的歷史時不仔細考究,而誤認為他們是鄉官的一部分了。
為了加深對此點的理解,我們在這里不妨也可以用個中國當代的歷史后例來做注釋:當時的游徼很像前些年各地縣里派往農村的駐村干部。他們雖然是縣府隸屬的干部,但每年都有很長的時間住在鄉間檢查與督導工作。
從《尹灣漢簡·集簿》和《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中的有關內容看,當時的“亭”不在鄉行政系統之內。“亭”與鄉、里基層社會行政單位,三者之間無十進制的關系。
《尹灣漢簡·集簿》一開始記述東海郡的四項內容,每項都是單列的:第一項:“縣邑侯國卅八,縣十八,侯國十八,邑二。其廿四有侯。都官二”;第二項:“鄉百七十□百六,里二千五百卅四,正二千五百卅二人”;第三項:“亭六百八十八。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郵卅四人。四百八如前”;第四項:“界東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如前。”我們從上述記述中完全可以看清楚,當時亭的組織與鄉、里完全不是一個系列。
從《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記述的東海郡各屬縣有關亭的具體情況看,亭亦不與鄉相屬相統無疑。比如,東海郡海西縣有鄉 14個,按十進的關系的話應有亭 140,但實際上不是。海西縣只有亭 54個。東海郡下邳縣有鄉 13個,按十進的關系應設亭 130個,但卻只有亭 46個。蘭陵縣有鄉 13,按十進的關系應設亭 130,但只有亭 35個。總之,以上史實均清楚表明了,秦漢時期亭的設置與鄉行政組織沒有直接隸屬的關系。
《后漢書·百官志》:“亭有亭長,以禁盜賊。”由此可知亭長與游徼二者在職責上相近。據史籍中的有關內容可以斷定,亭長與游徼一樣,也是一種縣令長的直屬吏員;亭是各地縣行政機關在自己轄區內分布于基層的固定統治據點。
要之,這里需要正確理解前已揭《五行大義》中所引用的翼奉的話:“游徼、亭長,外部吏,皆屬功曹”;以及正確理解《后漢書·臧宮傳》與《后漢書·王屯傳》中的“少為縣亭長、游徼”與舊日亭長“即今門下游繳者也”的話。這些話語中所包含的更多歷史信息應是,“部”字不能理解為區別內外的“部門”之“部”,而應理解為動詞,“部署”之“部”;雖然游徼與亭長二者有地位高下之分,但職責相同,即他們都是縣令長們專門部署在縣駐地以外、主要負責彈壓與鎮制的親近屬吏。游徼與亭長,二者的區別只是在于:1、一般,游徼的管刺監督地區大,是數個鄉。亭所管刺的地區要小,往往一鄉之地就有幾個亭;2、亭長在各鄉地界上有固定的“辦公場所”亭,而游徼的“辦公場所”一般設在縣府。大概在當時,亭長只有干好了才能升為游徼。
據史料記載,未統一東方六國之前秦國的統治者就在其統治區內廣泛設亭了。《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中有“市南街亭求盜才 (在)某里”,“某亭校長甲,求盜才 (在)某里”,“某亭求盜甲告曰”等的記載。[3](P252,P255,P264)由以上的有關內容推斷,秦國當時主要是在城鎮人口較稠密處設亭。至秦王朝建立后,他們便更廣泛設亭于廣大鄉村地區了。《史記·高祖本紀》:劉邦在秦朝為泗水亭長時曾使求盜至薛治竹皮冠。《集解》引應劭曰:“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巡捕盜賊。”應該說,中國現行體制下的民警派出所組織的祖宗就是秦代的亭。
至漢代,亭的制度較秦代又有發展。前揭《尹灣漢簡·集簿》載,東海郡西漢末年有亭 688個,有亭卒 2972人,郵 34人,另有 408人如前。另據《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東海郡當時另有亭長 688人,則當時每亭有亭成員近 6人。此人員數目多于秦國時的每亭校長一人,求盜一人,也多于秦朝時的每亭有亭長一人,亭卒二人。
《漢書·刑法志》中有“獄豻不平”語。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豻。”由此可知,因為亭長有權捕拿犯人,漢代時亭內也設立了關押犯人的場所——鄉亭臨時監獄豻。
東漢時鄉亭制度繼續實行。衛宏撰《漢官舊儀》曰:“尉、游繳、亭長皆習備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劍、甲鎧。……設十里一亭,亭長,亭侯;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奸盜。亭長持三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盜。”[9](P49)
名義上設鄉亭、置亭長是促進社會治安的,但其中弄權、欺壓人民者大有人在。《后漢書·魯恭傳》:魯恭拜為中牟令后有治下某亭長借人牛不還,“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后漢書·卓茂傳》:卓茂“遷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
《后漢書·百官志》鄉官條本注曰:“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另,《宋書·百官志 》:“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在這里,鄉佐放在了鄉官首位。也是據《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上述記載均不誣。
出土的《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中的鄉佐均列于亭長之前。西漢末年東海郡各縣大都有鄉佐。鄉佐與各縣鄉的數目不盡一致。亦即并非所有鄉皆有鄉佐。比如,海西縣有 14個鄉,但僅有鄉佐 9人;下邳縣 13鄉,僅有鄉佐 9人;郯縣有鄉 11個,有鄉佐 7人;蘭陵縣有鄉 13個,有鄉佐才 4人。但是,在東海郡的下屬縣邑中,幾乎每縣都有鄉佐。最多者 9人,最少的屬縣□□和昌慮只有鄉佐一人。18個屬縣中,僅司吾一縣無鄉佐。由以上《宋書·百官志》的把鄉佐列鄉官之首及《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中的鄉佐列亭長之前可知,鄉佐也當是類似于游繳,是縣令長們的外部吏。所不同的是,二者雖然同為縣令的直屬吏員但工作的領域不同。鄉佐的工作是在經濟領域。
總之,鄉佐與游繳一樣,也是各地縣行政機關直屬的工作在鄉村基層社會中的下沉官。
上述鄉級行政與亭的系統還不是秦漢時期最基層的社會行政治理的承載者。其下還有里組織與什、伍組織。
秦代鄉之下就有里組織普遍存在。《史記·高祖本紀》云:劉邦是原秦朝“沛豐邑中陽里人”。原注引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中陽”當然就是劉邦所在的里之稱了。我們這里順便提及的是,劉邦原來不是豐鄉人。是秦統治者用強力把其全家從魏地遷來的。《漢書·高帝紀》引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于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班固說:“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故其“骨肉同姓少。”按大梁之破在秦王政二十二年 (前 225年),而劉邦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前 256年)②,則劉邦舉家被遷到沛縣豐鄉時他的年齡已在 30歲左右。
《漢書·百官公卿表》中記述到了漢代的基層行政組織“里”。《尹灣漢簡·集簿》“鄉里條”也是記述到“里”。里有里正。實際上,不但如此,自秦代起,“里”之下還有組織。《后漢書·百官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已告監官”。此記大體不誣。大概,此種制度自商鞅變法時起秦國就開始實行了。
《商君書·境內篇第十九》:“五人束簿為伍,一人羽而剄其四人”,“隊五人,則陷隊之士,人賜爵一級”。《史記·商君列傳》:“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由以上史源看,司馬遷的記述正確。因為是兵民為一,當時一般的成年男子都被編成“伍”。五人一伍,因而其稱謂也就被人們習慣地稱為“士伍”了。在未正式確定百姓為“黔首”之前,秦國的成年男子被統稱為“士伍”。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法律答問》以及《秦律十八種》中有關的內容多多。比如:“士五 (伍)甲盜一羊”;“士五 (伍)甲盜,以得時直 (值)臧(贓),臧(贓)直(值)過六百六十”;“士五 (伍)甲盜,以得時直 (值)臧 (贓),臧 (贓)直 (值)百一十”。[3](P163,P165,P166)當時,士伍們都在里正的嚴密管轄之下生活,并且相互間有犯事連坐的法律責任。
很明顯是避秦王政之諱,里正當時統稱為里典。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有關的記載亦多。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律曰‘與盜同法’,有(又)曰‘與同罪’,比二物其同居、典、伍當坐之”。[3](P159)《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書:某里典甲詣里人士五 (伍)丙,告曰:‘疑癘 (癘),來詣,”“愛書:某里典甲曰:’里人士五 (伍)丙經死其室,不智 (知)故來告。”[3](P263,P267)
據睡虎地秦墓竹簡《傅律》和《法律答問》,秦代伍的頭目稱作伍老。《傅律》:“典、老弗告,貲各一甲”。[3](P143)《法律答問》:“賊入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曰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3](P193)另,《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中記述,秦襄王病,百姓“殺牛塞禱”,結果“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以上內容是說,因為討好統治者討的不當,里正與伍老都被罰了款。
“編戶齊民”一詞最習見于漢人的著作。[10]有時,編戶齊民又簡作編戶、編戶民或齊民。分別見于《史記·貨殖列傳》、《漢書·食貨志下》和《漢書·高帝紀下》等。什么是“編戶齊民”?就是不分貴賤、無一例外地利用行政權力把全社會所有的人都嚴密組織起來。《漢書·高帝紀下》師古注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漢書·食貨志下》引如淳曰:“齊者,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然而,人民之間無有了貴賤,但他們相對于最高專制統治者而言卻全部的下賤了。
與秦代相同,漢代的人民也統統進入了最高專制統治者編就的基層社會組織牢籠之中。
《漢書·韓延壽傳》:韓延壽為潁川太守時“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師古曰:“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漢書·尹賞傳》: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后,曾率部屬及“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兇服被鎧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
以上有關漢代里伍組織的記述中有兩點需要補充或展開。一是里正、伍長是漢代常制,不是韓延壽個人的發明;二是其中講明了漢代里正與伍長之間還有一基層層級。關于第二點,新公布的出土漢律中明確記有田典的鄉官官職可以給予說明。③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中不只一處記有田典。比如,《二年律令·錢律》:“盜鑄錢及佐者,棄市。同居不告,贖耐。正典 (即里典)、田典、伍人不告,罰金四兩”。另外,《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戶律》:“田典更挾里門鑰以時開;伏閉門,止行及作田者。”很明顯,這里的田典,既不是里的負責人,也不是伍長,就是司馬遷寫《史記·商君列傳》時所見到的漢代的“什長”。另外,以上的“田典更挾里門鑰以時開;伏閉門”之句所勾勒出的當時廣大鄉村被嚴格控制起來的社會狀況,應尤其引起人們的注意。
二
秦漢以后,我國廣大鄉村也是被嚴密的編組成鄉、里、什伍或保、甲、什伍的。只不過是,有時候鄉里組織的名稱有些變化,或者擔任里甲組織的人身份有了變化而已。
比如三國時期的吳國,國家不但嚴格控制核心地區,而且對非核心地區的控制也十分嚴密。從 1999年公布的長沙走馬樓吳國簡牘中的有關內容中,我們能進一步了解到當時吳國鄉里制度的細部有關情況,以及國家政權對縣以下鄉里社會進行嚴密控制的有關情況。簡牘表明,不是當時吳統治腹地的長沙走馬樓地區也有發達完備的鄉、里、丘等社會基層行政設置。即鄉與里的行政單位之下,當時還有丘。國家進行戶口登記時以丘為單位。所有人戶都被編組進了各個丘。各丘中人戶姓氏混雜,不是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制。人戶中所有人的姓名、年齡與生理特征等,都必須詳細記錄在戶口冊上。縣廷中的專管吏員對自己所管轄的鄉里嚴格管理,必須具保,負有連帶的法律責任。以下這幾支簡就記錄了有關的詳細情況:“東鄉勸農掾殷連被書條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紀為簿。輒科核鄉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戶民自代,謹列年紀以 (已)審實,無有遺脫。若有他官所覺,連自坐。嘉(禾)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破莂保據”;“廣成鄉勸農掾區光言:被書條列州吏父兄子弟伙處人名年紀為簿。輒隱核鄉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聾頤病,一人夜病物故,四人真身已逸及隨本主在官,十二人細小,一人限田,一人先出給縣吏。輒隱人名年紀相應,無有遺脫,若后為他官所覺,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破莂保據”;“東鄉勸農掾番琬叩頭死罪白:被曹敕,發遣吏陳晶所舉私學番倚詣廷言。案文書:倚一名文。文父廣奏辭:本鄉正戶民,不為遺脫,輒操黃簿審實,不應為私學。乞曹列言府。琬誠惶誠恐,叩頭死罪死罪。詣功曹。十二月十五日庚午白。”[11](P32-33)《后漢書·百官志》曰:縣廷的“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秋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由此可知,如我們前些年人人都熟悉的農村工作隊,勸農掾是當時吳政權從縣里下派到各鄉村中的下派“干部”。另外由此可知,當時是禁止人們自由外出求學的。不經官府批準老百姓的后代私自外出求學屬違法行為,所犯罪的罪名是“遺脫”。晉代,此鄉官之制仍基本實行:“凡縣五百 (戶)以上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不滿千以下置治書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12]
南北朝時期也是沿襲的秦漢的一套基層社會進行嚴密編制的制度。比如北朝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政權,他們都是如此。北魏的實行鄰、里、族黨三級鄉里制始于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當時是采納給事中李沖的建議實行的,稱做三長制。具體做法是:“三長,謂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13]東魏的鄉里組織是以五家為鄰比,二十家為閭里,百家為族黨。北齊時則是“人居十家為鄰比,五十家為閭,百家為族黨。一黨之內,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十有四人,共領百家而已。至于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14]
與前代一樣,隋唐時期的統治者在統治縣以下廣大鄉村社會上也費盡了心機。
隋王朝建立伊始,統治者就“頒新令,制人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查焉。”[15]隋文帝開皇九年 (589年),在蘇威等人的奏請下,鄉村的黨又改稱為鄉,并擴大轄區:“五百家為鄉,正一人;百家為里,長一人。”[16]同時,賦予鄉正以署理辭訟之權。但事后一年,即開皇十年,隋統治者即因關東諸道巡省使虞慶奏“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于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賂”,于是又廢除鄉正理辭訟之權。[14]
唐代的鄉里組織是“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為鄰,五鄰為保。保有長,以相禁約。”[17]鄉置鄉長與鄉佐,里置里正。相比較而言,唐代統治者對里正的選拔與任用更為重視。史載,諸里正“縣司選勛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干者充”,“掌案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稅。”[14]為了更好地發揮里正臨民的積極性,唐統治者對其極為優渥,免除他們所有的勞役與賦稅。[18](P200)
作為秦漢時期傅籍與編戶齊民制度的延續,唐統治者與前代統治者一樣,也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并且唐代也定期搞貌閱。
唐律中的《戶婚律》、《捕亡律》中都有關于戶籍制度的規定。《戶婚律》首重的是民戶戶口的脫漏和年狀的增減,規定民戶、里正和州縣官府都必須對這類違法行為負責。脫漏戶口指隱瞞戶口不在戶籍上登記;增減年狀指“增年入老,減年入中、小及增狀入疾”。唐律對于家長、戶主和尊長也有明確的規定,表明了法與禮的結合,反映國家與民戶的關系。唐律的《捕亡律》主要內容是逃亡法。其中關于丁夫、雜匠、民戶、官奴婢等逃亡罪的規定屬于戶籍法的范疇,規定了民戶和地方行政人員對于上述人員逃亡應負的責任。
唐律還根據《戶令》中關于鄰、保組織民戶互保的有關規定,規定了民戶的某些犯罪要追究連帶責任,按相糾連坐法懲治。[19]
如有關專門研究者指出的,唐代的戶籍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下列方面的內容:
一、為了調查、登記和統計戶口,實行了嚴密的“手實”制度和編制籍帳的制度,規定民戶必須如實申報戶口和土地,地方行政組織必須定期編造戶籍和計帳;
二、為了檢核戶口、控制民戶,實行了定期貌閱戶口和對地方行政官員的考核制度,規定地方行政組織要定期檢查丁口的實際年齡、形貌、身狀是否與戶籍登記一致,對于脫戶、漏戶、逃亡等違法行為,必須按律的規定進行懲治,對于新附入籍的民戶進行優待,免除一定時期內的賦稅徭役;
三、為了使民戶之間互相牽制,規定民戶犯罪的相應責任,做到互保相糾。
唐代編造戶籍時戶主自己先填寫家庭所有成員的情況的“手實”,官府逐一核實,裝訂成冊,叫做戶籍帳。戶籍帳由里到鄉,然后到縣到州,直至中央。
根據文獻記載和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唐代經濟社會文書,可知唐代戶籍的基本內容是由手實與官府人員加名籍 (戶口)的詳細的腳注兩部分組成。具體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戶主和家庭成員姓名、家庭成員與戶主的關系;2.性別;3.年歲;4.年狀。唐代如同隋代,也按年齡把人們分為老、丁、中、小、黃幾種;5.身狀。是否三疾,即病疾、篤疾、廢疾;6.身份。分為官、民、賤等幾種。
戶籍的腳注體現了政府對戶籍登記的具體管理,主要包括人口變動、年歲和身狀的改定以及是否向政府交納租調 (課戶、不課戶)等。如果在兩次造籍年份之間民戶內有人口死亡,到新造戶籍時要據實申報,在腳注中正式削除,注明某年帳后死或籍后死。民戶有逃亡或沒落,遷入或遷出,有新生、歸附(指少數民族內附者)、括附 (隱瞞戶口而經檢括附籍者)、漏附 (前次遺漏而新附籍者)或者殘、疾等情況,也皆須在腳注中注明。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宋元明清時期我國鄉村基層行政組織中從事管理工作人員的身份盡管職役化了,但該組織在控制社會與民眾人身方面沒有變化。比如北宋,開寶七年 (974年)曾一度廢“鄉”設“管”,每管設戶長,主賦稅;設耆長,主盜賊、詞訟事;[20]再如南宋時期高宗建炎元年 (1127年)“罷戶長催稅,復甲頭”;紹興七年 (1137年)下令“大保長仍舊催科”;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又“令保甲催稅”。[21]此處,不管是管的戶長、耆長也罷,甲頭也罷,還是大保長,都只不過是名詞與概念的不同,其為最高統治者管束人民的職責與性質與前代沒有不同。
宋代保甲制度控制人民的反動性尤其不能低估。它的要害在“保”與“甲”,這些東西是專制國家權力對鄉里社會最基層的直接滲透。保甲組織之下,“故有所行,諸自外來者,同保互告,使各相知;行止不明者,聽送所屬。保內盜賊,畫時集捕,知而不糾,又論如律。”倘若保丁“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22]當時,統治者通過這種人人具結家家犯事連坐的方式,比較容易地把整個鄉里社會牢牢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上。
當時此方面具體的事例也不少。比如張詠在蜀時規定“凡十戶為保,一家犯事,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23]有人在講到該問題時往往認為推行者王安石是一位“改革家”,因而他的保甲制度也不能否定。但必須清楚,王安石是位君主專制主義者。他有《兼并》詩一首,其中講:“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操權柄,如天持斗魁;取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24]從此詩我們可以看到,他與商鞅一樣的是一個強調強主弱民、進行被統治者之類的類的自我否定的人。
宋代最高統治者的主要根椐財力將鄉里社會人戶劃分為九等,不管比較富有的人家同意與否,上等戶都必須擔任鄉里職役。不僅如此,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四月辛亥,政府又規定里正負責催稅及承擔縣里的差役,充當衙前。[25]里正一旦充當了衙前,往往被連累得傾家蕩產。所以,當時民富者不敢露富,貧者也不敢求富,人們爭相逃脫擔任里正衙前,甚至出現過民以死求免充里正衙前的慘狀。如宋仁宗時韓琦說,“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自經而死”。[14]
從以上敘述可以看到,自宋代開始,鄉里組織的頭目一改了在秦漢時位要聲顯的狀況,從而成為了任州縣官吏任意驅使的差役。并且一般講來,這種狀況越到后世其程度越加嚴重。此事表明了,在專制主義的集權統治大政治環境之下,鄉里組織的“干部們”其身份可以是多種形態的:可以給里正們以特權,讓他們利益均沾;也可以不給里正、戶長們以特權,讓他們以奴隸的身份來為自己效勞。但是要之,他們都不代表農民自己與鄉村社會本位的利益、愿望及要求。
與宋代大體相同,元代鄉職也實行職役化。其中,里正受專制國家的壓迫與盤剝尤甚。往往,雜差任務下來后里內的地痞爭相逃脫,在此情況下,只好由擔任里正的較富裕的人家他們自己承擔;一般人戶完不成催征了,專制政府也強迫他們支墊貼賠。因而,元代過得較好的人家一旦充任了里正,也往往是不久便傾家蕩產。史載,“順帝至正中,以浙右痛于徭役,民充導正者,皆破產”。[26]
明初朱元璋統治時期曾規定廣大鄉村互相知丁。即規定一村之內的人必須互相知道各家的男人在干什么;如果不在家的話也必須知道此人到什么地方去了。朱元璋規定的互相知丁互知“務業”的具體內容是:“凡民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具在里甲。縣州府務必周知,市村絕不許有逸夫。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余皆四業,必然有效”;“知丁之法,某民丁幾,受農業者幾,受士業者幾,受工業者幾,受商業者幾。且于士者志于士,進學之時,師友某氏,習有所在,非社學則入縣學,非縣必州府之學,此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為未成士之師,鄰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幾出入可驗,無疑為也。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專工之業,遠行則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巨細所為,鄰里采知,巨者歸遲,細者歸疾,出入不難見也。商本有巨微,貨有重輕,所趨遠近水陸,明于引間。歸期艱限,其業鄰里務必周知。若或經年無信,二載不歸,鄰里當覺之詢故”。[27]
為了對人民進行思想控制,朱元璋另外規定在里甲設專職負責教化人的“老人”。“老人”也是鄉役的一種。對于明統治者搞的這種老人制度及其他一些專制措施,當時的一些人曾給予了肯定。比如,海瑞稱:“圣制老人之設,一鄉之事,皆老人之事也。于民最親,于耳目最近。誰善誰惡,洞悉之矣。尤擇一醇謹端亮者為之。以年則老,識則老,而諳練事務則又老。有渠人,因構一亭書之曰申明亭。朔望登之以從事焉。是不計仇,非不避親,毋任口雌黃,不憑臆曲直。善則旌之,惡則簡之。此亦轉移風俗之大機括,而鄉落無夜舞之鰍鱔矣”。[28](P149-150)明代另一位士人鄧士龍則記述道:“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后,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于途,拾起一視,恐污踐,更置階圮高潔地,直不取也”。[29]對此,我們應做何思考呢?我想,雖然專制統治者們不大喜歡海瑞,但海瑞卻是忠心于專制統治者與專制制度的。這是其一。其二是,朱元璋時的“人間道不拾遺”大概類似于秦國的“民風純厚”。到過秦國的荀子當時談到過此事。人都被馴化得不敢有一點的“私心雜念”了,必然的會“人間道不拾遺”。另外,顧炎武也曾說:“太祖損益千古之制,里有長,甲有保,鄉有約,寬有老,俾互相糾正,當時民醇俗美,不讓成周”。[30]我們認為以上對于朱元璋專制鄉里制度的歌頌都是愚見。尤其是顧炎武之論,更是如此。成周時期國人能參政議政,可以自主廢立國君,而朱元璋治下的廣大鄉村小民如同畜欄中任他隨便整治的牛馬,顧炎武竟將二者硬扯到了一塊,實令人不可思議。
在許多方面,清代統治者對鄉里社會的控制同樣的嚴厲。比如,清統治者在全國各地的鄉村都實行嚴格的人口月報制度。有人言,“保甲之法,清查戶口,譏查出入,……每鄉置循環簿,月朔報縣,而縣之官吏……年終報郡。”[31](P303)大概從清朝到民國時期,我國在推行保甲之法的日子里,具體情況都是這樣的。
還有,清代規定對僧尼道士也實行編甲:“至于寺觀,亦分給印牌,備書僧道口數、姓名,稽察出入。”[32]“和尚道士尼姑之庵觀寺院,其師徒籍貫年歲田房,本身有無殘疾。俗家有無親人,皆應逐一詳注,一律編人保甲”。[33]再比如,清政府把乞丐也組織起來了。乞丐也實行了編甲。史載,其方法與措施“一是選立丐頭為管束之人,二是查造丐戶牌冊,三是驅逐少壯乞丐,四是老幼乞丐建棲留所安置,禁止散處。丐頭,……人選可由棲止地段的民戶保長擇舉。也可以由管轄該片的衙役保充。江南農村常按‘坊’承管乞丐。乞丐亦造保甲牌冊,曰‘丐頭循環冊’,開列丐頭姓名,承管乞丐人數,年歲、籍貫、體貌特征和棲身處所。由于丐群成員常有變動,在上述各項之后,還須以四柱形式寫明每月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人數,按月送縣例換。此外,乞丐各有腰牌,兩面書寫。正面為縣正堂示諭,背面記本人姓名、特征及所隸屬丐頭之名,順莊編號,常掛腰間……。”[34]清統治者一般不許人異地討飯。如有此類情況出現,則要求“外來流丐,保正督率丐頭稽察”。[35]
三
除了以上列舉的諸多史實能清楚表明我國秦漢以來的鄉村基層社會是被專制的國家權力控制與管制的、而不是如費孝通所言是什么自治與民主的之外,有關思想家與學者的一些論述也能加深我們對該問題的正確認識。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認為,所謂社會基層的民主與自治應是,一、他們在一般情況下絕無外在的強加的專制政治權力;二、他們在行動上能最大限度地體現當地居民的意志、而不是受著更高行政權力的不時的制約與定向。[36](P65-108)具體到我國中古時期廣大鄉村的實際情況,現代政治學家蕭公權認為,“缺乏自治更接近 (傳統政治下中國)鄉村生活的實情。”[37](P338注釋[12])有我國旅居西方國家時間最長的法學家之譽的瞿同祖則認為傳統中國的鄉村社會中根本就沒有自治。他說,“清代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都是按同樣的原則組成的,所有行政單位,從省到州縣,都是中央政府設計和創建的。……所有地方官員,包括州縣長官,都是中央政府的代表。在州、縣或組成州縣的市鎮、鄉村,都沒有自治。”[37](P5)
除了蕭公權和瞿同祖之外,當代堅持中國傳統社會內沒有鄉村自治的,比較知名的學者或思想家還有魯迅、錢端升、劉澤華等人。分別見魯迅的文章《燈下漫筆》,錢端升著作《中國政府和中國政治》和劉澤華先生的著作《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劉澤華先生甚至認為中國古代的廣大鄉村社會中不但沒有自治與民主,人民甚至是些被奴役與被完全制服了的國家奴隸。可分別參見其著作《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的第二章《君主集權國家對人身的支配》與第三章《君主集權國家對土地的支配》。[38]
另外,瞿同祖先生的關于中國中古時期鄉紳這一在鄉村社會中比較有影響的階層性質的分析,也有利于我們加深對該問題的認識。他指出,“中國士紳的特權地位并不純粹取決于經濟基礎。士紳的成員身份,并不像有些學者推測的那樣來自財富或土地擁有。無疑,在財富和士紳成員身份之間有著密切關聯,而財富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擁有財富,使人有足夠的閑暇接受參加科舉考試所必須的教育。……然而,在具備進入特權階層的條件與特權身份的實際獲得之間是有差距的。財富和地產本身不是士紳的身份的充分條件。庶民地主不論擁有多少土地也不屬于士紳集團。只有在向政府購買官銜或學銜 (國子監學生身份,監生)成為可能時,財富和身份之間的聯系才可能最緊密。售賣官爵功名是清朝時的普遍做法,特別是在 19世紀的危機局勢迫使朝廷尋求額外的收入之時。這是唯一繞過科舉考試、將財富直接轉變為地位的情形。……另一方面,任何有功名或得到官方委任的人,無論是否有地產,也可以馬上躋身士紳之列”;[37](P286-287)“中國士紳所擁有的地位和權力是基于政治而產生的。”[37](P285注釋9)瞿同祖先生在該書中還指出,“關于士紳,……他們代表地方社區的權利,是得到政府和公眾普遍認可的。他們作為地方官員和老百姓之間的斡旋者,向地方官員提供咨詢,經常在地方行政的某些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因為地方社團參與地方事務管理經常被視為地方自治的條件,所以問(中國清代)士紳參與 (地方管理)是否意味著地方自治,就是一個依邏輯當然有的疑問了”;要問中國有無地方自治的話,“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參與者僅限于作為少數人群體的士紳。其次,士紳既非地方百姓選舉的代表,也不是政府任命的代表。他們只不過憑籍自己的特權地位而被(習慣上)接納為地方社群的代言人而已。但是他們參與政府事務和代表地方社群說話的權利,并沒有像西方民選議會那樣在法律上正式明確下來。法律并沒有規定哪個士紳成員應該被咨詢或應該被邀請參與行政事務,這些都主要隨州縣官們自便。……實際上,士紳的介入主要是基于個人標準,其效力也主要依賴于特定士紳個人所具有的影響力”;“即使士紳有權利在地方政府中代表自己的利益,但仍然沒有代理人去代表地方社會的其它群體。”[37](P337)
以上瞿同祖先生的分析非常深刻,我們完全贊同。另外要補充的是,如一首清代的對聯所說的,中國當時地方紳董的地位相對于正式的皇家官吏來地位比較可憐,他們得時不時地向州縣官“袖金贈賄”,④即得時不時地向州縣官們暗自下禮行賄。
總之,在君主獨裁專制主義與極度中央集權主義的中國中古舊時代里,中國的廣大鄉村中是沒有近代意義上的自治與民主存在的。如果說有的話,那也是一種集中營式的被管制下的農民“自己人治自己人”的偽自治與偽民主。因此,如果從中去尋找我們今天建設基層自治與民主的思想與制度營養的話,也只能是像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國民政府大員陳立夫一樣,找到的是“管、教、養、衛”。[39](陳立夫序)
[注 釋]
①《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清楚寫明了的鄉有秩是 24人。另外有的縣之下雖然清楚寫明了有“鄉有秩”,但數字已失。鄉有秩有一縣多至 4人或 5人的,以上的估計是取了它們的中間數。
②據《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
③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呂后二年即公元前186年實行的律令。
④這副清代對聯主題是諷刺當時的州縣官的,全文是:“見州縣則吐氣,見道臺則低眉,見督撫大人,茶話須臾,只解得說幾個是是是;有差役為爪牙,有書吏為羽翼,有地方紳董,袖金贈賄,不覺得笑一聲呵呵呵。”載《經典雜文》,2008年第 4期。
[1]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2]和田清.中國地方自治發達史 [M].東京:東京汲古書院,1975.
[3]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4]班固.漢書·朱邑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
[5]班固.漢書·張敞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
[6]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 (下)[M].濟南:齊魯書社,1985.
[7]洪適.隸釋·隸續[M].北京:中華書局,1986.
[8]嚴耕望.秦漢地方行政制度[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
[9]孫星衍等.漢官六種[M].北京:中華書局,1990.
[10]劉安,蘇非,李尚,伍被.淮南子[M].北京:中華書局,1955.
[11]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上) [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12]房玄齡.晉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3]魏收.魏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4]馬端臨.文獻通考 (卷十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5]魏征.隋書·食貨志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魏征.隋書·高祖紀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7]劉句,張昭遠,賈偉.舊唐書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8]張哲郎.鄉遂遺規——村社的結構[A].吾土吾民[M].北京:三聯書店,1992.
[19]長孫無忌.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61.
[20]徐松.宋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1]趙彥衛.云麓漫鈔 (卷十二)[M].北京:中華書局,1996.
[22]脫脫.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3][35]徐棟.保甲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24]王安石.王臨川集[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25]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 [M].北京:中華書局, 1961.
[26]郭成偉點校.大元通制條格[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7]朱元璋.大誥續編·互知丁業[A].錢伯城等.全明文(第 1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8]海瑞.海瑞集 (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 1981.
[29]鄧士龍.國朝典故[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杜, 1993.
[30]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M].北京:中華書局, 1965.
[31]聞天均.中國保甲制度[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35.
[32]昆岡,李鴻章.光緒大清會典事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3]葉世倬.為編審保甲示 [A].徐棟.保甲輯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4]王風生.保甲事宜[A].徐棟.保甲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6][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7]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38]劉澤華.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39]黃倫.地方行政論[M].重慶:正中書局,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