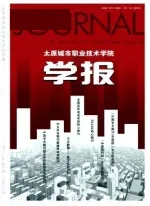《喜福會》:邊緣化的“第三空間”
李 怡,陳曉蘭
(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海南 海口 571158)
《喜福會》:邊緣化的“第三空間”
李 怡,陳曉蘭
(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海南 海口 571158)
《喜福會》是華裔美國作家譚恩美的首部代表作。本文結合作家的文化身份背景,從作品中母女二人的身份和作品中出現的中國意象的角度指出《喜福會》的文本內容呈現出邊緣化的特征,同時體現了“第三空間”成為小說內容載體的重要作用。
喜福會;第三空間;邊緣化
20世紀以來,在全球化背景下,學界的目光經歷了“空間轉向”,將關注點投向了非地理、歷史世界以外的人文領域的“第三空間”,導致了在文學研究、城市建筑設計、地理學等領域的一次變革,使研究者的研究視角得以擴展和延伸。《喜福會》中由于美國華裔文學家譚恩美身份和文化背景的雙重性造成了視角邊緣化,出現了“雜合”的現象。
“第三空間”的概念來自于美國后現代地理學家愛德華·索雅(Edward Soja)1996年出版的《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象地方的旅程》。“第三空間”理論在文本研究中就好像一張觀念和觀念之間復雜的網絡,文學在這張大網之中確立了自己關照世界的方式。列斐伏爾認為“社會所生產同時也生產了社會的理論所示,文學故此同樣是一種社會媒介,一個特定時代不同大眾的意識形態和信仰,由此組構了文本同時也為文本所組構。文本組構了作者想說、能說,甚而感到不得不說的言語,同時又組構了言說的方式。所以文本是環環相扣,交織在它們或者是認肯或者是有意顛覆的文化慣例之中。”英國達勒姆大學地理系的麥克·克朗(Mike Crang)在199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學》中,以“文學地理景觀”為題專門討論了文學中的空間。他指出“文學作品不是一面反映世界的鏡子,而是這些復雜意義的一部分。”而后殖民主義理論家霍米·巴巴認為文學作家在有限的空間內的想象導致了文學創作者在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性“建構”,也就是構建了既不同于“帝國主義”文化也不同于“第三世界”文化的空間模式。在分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關系時,巴巴強調它們互相依存、互相建立起對方的主體性,并指出所有的文化陳述和系統都建立于一個模糊、雜合的“第三空間”。
一“、中國夢”和“美國夢”的邊緣化
《喜福會》將華裔家庭的生活以文學的形式加之呈現,較少修辭和情節的夸張,基本原封不動地反映了瑣碎而平時的美國華人家庭生活。但是,作品中深層體現的并不是“中國夢”和“美國夢”的追尋,而是兩者在母女兩代人身上的共同的缺失,使美國的華裔人群陷入了“三明治式”的兩難境地,兩種不同文化身份的碰撞使美國華裔難以真正進入美國的政治主流社會。身處美國社會華裔作家,更是比普通人敏銳地捕捉和認識到了這種境遇。
小說開頭以一則寓言為引子,一只鴨子因為把脖子伸得太長變成了天鵝。一位婦人買下這只“天鵝”,想把它帶到美國實現自己的夢。她夢想在美國生下一個女兒,長得像她,卻能過上和她完全不同的生活:女兒將享有美國能給予的一切好處,不再有任何憂傷。婦人最終希望把這只天鵝送給女兒當作禮物,因為它實現的目標遠遠超越了自己的期望。從某種意義上說,婦人的夢實現了:女兒得到了尊重,然而令人覺得諷刺的是,她卻變得過于美國化——“只說英語,吞下的可口可樂多于憂傷”。有學者根據這則寓言指出了美國夢的兩個主題:吸收西方文化,性格上繼承東方人的美德。這則寓言引出了本文所要分析的“美國夢”主題:一方面母親望女成鳳,既希望孩子擁有最好的西方教育,又希望她們在性格上繼承東方人的美好傳統;另一方面女兒卻完全脫離了東方文化,覺得吸收、同化是實現“美國夢”的前提。“美國夢”的最初意義,是指的美國從歐洲大陸來到美洲大陸后開辟荒地時的積極、樂觀、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母親”們遠離故土,也正是帶著這種美好的希望來到美國,所以他們希望自己的后代們講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事事稱心,應有盡有。她們相信,只要努力,都會實現。“媽相信,在美國,任何夢想都能成為事實。你可以做你一切你想做的;開餐館,或者在政府部門工作,以期得到很高很高的退休待遇。你可以不用付一個子的現金,就可以買到一棟房子。你有可能發財,也有可能出人頭地,反正,到處是機會。”“母親”將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這片對她來說十分陌生的土地上,她希望女兒們聽她們的話,練習鋼琴,贏得下棋比賽的冠軍,比誰家的孩子都爭氣。這無不體現著中國家庭“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教育理念。對母親,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這使得他們在教堂的禮拜上可以學習英語,需要適應美國的生活方式和習慣,以致于教育孩子們時會說需要適應這個新來的社會,“這種美國規矩!每個人來到異國他鄉,首先都得遵守當地的規矩。如果你對此一無所知,裁判便會說:你這個人怎么搞的,滾回去。……所以最好的辦法是,你拿著棋子,自己去琢磨其中的奧妙。”母親的“美國夢”在兒女身上基本獲得了實現,漂亮的房子,富足的經濟,但是同樣不理解的是兒女們的生活方式、服飾、穿著、學業,乃至婚姻的選擇。“美國夢”實現了,母親卻失落了。
女兒是在美國出生和成長的一代,和其他的美國孩子一樣,接受著美國的文化教育觀念,倡導個性自由,要求成為他自己。“美國夢”對他們而言,不僅具備了父輩們的內涵和意義,更多的是被賦予了美利堅民族的意義。在對婚姻的選擇上,她們有別于中國家庭的各種要求,更多的是“個性”。“中國人有中國式的建議,美國人也會有美國式的建議,而一般情況下,我認為,美國式的見解,更合我意。”中國,對于女兒,是中國式的童話。她們通過母親的講述,隱約地了解到了它的內涵。女兒們通過中國夢的找尋,試圖在找尋自己祖輩的文化傳統,小說的結尾,吳精美終于與她失散了40年的親人在上海機場相遇,這一情結的安排,試圖在給“中國夢”的追尋找到最好的方式,但是文化的隔膜和兩種夢的尋找將是一直存在的話題,身份的構成使女兒成為邊緣化的人群,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
二、中國意象在“他國”的邊緣化
《喜福會》的意象構成極具有中國的民族特色,喜福會中四人一桌的麻將、薇弗萊·龔小時候被母親緊逼而學的圍棋,將中國的傳統文化帶入了“他者”文化的領域。但是無論是麻將還是圍棋,在離開本土文化的氛圍被植根于異國文化體系中,均喪失了它們原有的含義,成為小說文化邊緣化“雜糅”的代表。
喜福會成立的最初是“母親”逃難到桂林時為了振作精神而發起的打麻將的聚會。“我們每星期輪流做一次東,做東,即出錢出力……做東的一方,要準備一些名字吉祥討口彩的點心來款待大家——金錢餅,因為樣子像圓圓的銀洋或金圓,長長的米線象征著長命百歲,落花生象征得貴子,福橘象征多吉多祥。”第二次喜福會的創辦是在母親遠渡重洋來到美國后,為了“那遺落的中國的夢和希望”,帶著游子對故土的思念。盡管母親此時已遠離國內的戰亂,但是她此時身處大洋彼岸的異國他鄉,使母親更加思念她們自己心中構建的“中國”,喜福會成為她們記憶和情感共鳴的延伸地。母親去世后,“我”接替了母親的位置,但是“我”眼中的聚會已經半美國化了,人們穿著美國式的褲裝,圍坐在西班牙式的吊燈下,討論是華爾街市場上投資的美國的股票,交流著防止通貨膨脹的最好辦法。現在與其說它是帶有中國文化的象征,不如更準確地定位為一群已經或正準備積極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華裔群體地聯誼會,喜福會成為華人社區游離于中美文化群體的標志之一。
小說中除了喜福會的由來,還提到了更具中國典型文化的代表——圍棋。圍棋融匯了中國古代的陰陽哲學,將玄妙萬端的人生世界濃縮入小小的棋盤中。黑白二子是陰陽二氣的載體,體現著古人對變化萬千的萬物的抽象的模擬。“母親”強迫著“我”學習圍棋,并參加地方棋賽。“母親”的這代人在希望兒女在中國“圍棋”所參悟的棋道中獲得融入美國社會的奧妙,并教導“最強烈的力量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風”。圍棋所代表的儒家和道家的文化在小說中喪失了它的文化意義,反而成為了移民美國的外來者融入美國社會的“武器”或者是“工具”,在小說中帶有與眾不同的象征意義。
華人移民的后代在美國出生長在美國,接受美國文化觀念影響,希望融入美國社會,而在美國社會中,他們又是弱勢的群體。邊緣化的身份標識造成了他們與父母的沖突,與中國文化價值觀的沖突,甚至還有與美國社會的沖突。小說中,被邊緣化的女兒們的沖突實質是在尋找跨越文化的群體歸屬感,使得他們的文化文學視角跨越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呈現出空間和時間的交錯性,同時也在自己構建的開放的“第三空間”中尋找文學和自身的立足點。
[1]陸揚.空間理論和文學空間[J].外國文學研究,2004,(4).
[2]邁克·克郎.文化地理學[M].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3]張宏嫻,李加強.唐詩翻譯中的第三空間——霍米·巴巴之雜合理論在唐詩英譯中的體現[J].宿州學院學報,2008,(6).
[4]吳冰,王立禮.華裔美國作家研究[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
[5]程愛民,張瑞華.中美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對《喜福會》的文化解讀[J].國外文學(季刊),2001,(3).
[6][美]譚恩美.喜福會[M].程乃珊,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7]袁霞.從《喜福會》中的“美國夢”主題看東西文化沖突[J].外國文學研究,2003,(3).
I106.4
A
1673-0046(2010)5-01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