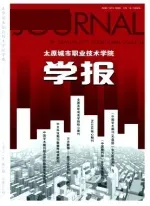濃縮的意象 想象的擴張——淺析龐德《在地鐵車站》的張力美
宋 芳
(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濃縮的意象 想象的擴張
——淺析龐德《在地鐵車站》的張力美
宋 芳
(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龐德的《在地鐵車站》雖然是一首只有20個單詞的短詩,但卻是詩歌中的經典。詩歌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張力,使得《在地鐵車站》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顯現出詩人廣闊而深厚的思想和詩歌強大的生命力。
張力;語言;情感;意蘊
《在地鐵站》是美國著名詩人埃茲拉·龐德于1913年發表的一首短詩,原文只有短短的兩行,14個單詞。全詩如下:
INASTATION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這是現在我們所見的通行刊印的版本,其實最初刊印時并非如此,每行詩分為3個部分,一組詞與另一組詞之間都有留白處,第一句句末為冒號,如下:
The apparition of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譯文:
人群中這些面孔幽靈一般顯現;
濕漉漉的黑色枝條上的許多花瓣。
這首短詩一經發表就在詩壇引起了極大轟動,后來這首詩不僅成為龐德個人的代表作,而且成為整個意象派詩歌的經典。談到英美詩歌,尤其是談到龐德倡導的對20世紀詩歌創作產生深遠影響的意象派運動,總不能繞過這樣一首僅僅20個單詞的短詩。在文學的浪潮中,任何詩歌流派都有勢盛有勢微之境遇,但是好的詩歌作品卻可以經久不衰。龐德的這首小詩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在文學作品不斷涌現的今天仍傲然屹立,不被人所遺忘,原因何在?筆者認為,除了它遵循意象派運動的原則,無論在形式上還是節奏上一反傳統,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以外,關鍵的一點還是在于它的張力美。
現代詩歌理論中的張力概念源于英美新批評學派,最先提出這一概念的是美國學者艾倫·退特。他在《論詩的張力》文中說:“我提出張力(tension)這個名詞,我不是把它當作一般比喻來使用這個名詞的,而是作為一個特定的名詞,是把邏輯術語‘外延’(extension)和‘內涵’(intension)去掉前綴而形成的。我所說的詩的意義就是指它的張力,即我們在詩中所能發現的全部外展和內包的有機整體。”李元洛在《張力彈性》中,對艾倫·退特的定義作如是解:“這里所說的‘張力’,是借用物理學的術語,但它并不具有科學的或邏輯的意義,而只是一種文學批評特別是詩歌批評的用語。所謂內涵力和外延力的完整有機體,它的基本意義就是詩歌在內蘊上不能作直線式的指陳,在結構上不能作散文式的蔓衍,因為一覽無余的直陳與散文化的松散,都不可能構成張力,而是要在矛盾的對立統一的基礎上,由不和諧的元素組成和諧的新秩序,在相反的力量動向中尋求和而不同。詩中張力的作用,在內涵上是使詩意的密度加強,并使詩意深廣化;在結構上使詩作凝縮而不松散,詩質堅實而不稀薄;在美學效果上是大大增強詩的打動人心的力度。”可見,詩歌在語言、結構上的對立統一,給人以強烈的感情沖擊力和想象擴張力,使得詩意豐富而深廣,這就是詩歌的張力美。論文力圖從語義、情感、意蘊三個方面來分析龐德《在地鐵車站》中所表現出的張力美。
一、語義的張力
可以說,詩人是最具叛逆性和創造性的作家群。詩人在創作時常常突破常規,發揮自己的想象和創造力,給人以視覺和精神上的沖擊。具體到詩歌文本里,它直接反映在詩句和語詞的運用上。人們通常強調詞語的組合一定要符合語言表達習慣,但詩人龐德在《在地鐵車站》中就突破了這個常規,有意地與詞語表達習慣相悖,通過一些反常的搭配把本來“無緣”的詞語硬湊到一起,使它們各自的作用力彼此抗衡,在這種矛盾抗衡中構成一種表意的模糊,在看似模糊中收到超乎尋常、奇峰突起的表達效果。
在詩歌的第一行出現了兩個并蒂的意象,分別為“apparition”與“face”。這兩個意象搭配就充滿了矛盾和新奇,因為這兩個事物分別屬于不同的世界,Apparition有“幽靈、鬼怪”的意思,屬于非現實世界,而“face”屬于人類現實世界。Black bough與Petals也是在色彩明暗上充滿矛盾的,black bough是指黑色的枝條,在色彩上是暗的。petals是花瓣的意思,花瓣的色彩總體是明亮的,明亮與暗沉相對。暗色調,給人以一種熄滅、結束、幻滅的感覺,帶有壓抑、抑郁的情緒。明亮色調,則象征著光明、希望、開始。龐德在整首詩的意象選擇上是如此的有悖常理,然而正是這樣抽象,而且超乎尋常的描述形成了詩歌解讀中的意義空白,引發了讀者的無限遐想。理解這首詩時,讀者可以通過這樣的意象并置尋找其中的關聯,展開聯想,領悟出自己獨特的感受。
語義的張力不僅表現在意象上的矛盾,還在于語言的濃煉。《在地鐵車站》是一首極為短小凝練的詩歌,全詩僅僅20個單詞,龐德在“我是怎樣開始的”文章中曾說過:“一件藝術品的優劣不是以量來評價的:如果你適當安排音節、運用標點,16個音節就夠寫一首詩的了。”于是龐德將30余行的詩情濃縮為2行小詩。這樣的語言壓縮并沒有帶來藝術性,因為語言的壓縮,舍棄掉不必要的動詞,而僅用幾個意象構造全詩,正是這種意象并置才使得詩意被擴張,張力效果在意象的統一、對立間產生,形成意象與意象之間,詩句與詩句之間的空隙張力,使讀者從空隙中讀出弦外之音,想象詩歌意象之外的意象。
二、情感的張力
詩歌的張力美還在于情感上感性與理智的剛柔并濟。詩歌是生命體驗的詩意傳達,是個人情感的最真實的映射。龐德說過,“詩歌是極大感情價值的表述”,詩歌“致力于傳達精練的感情”,“給予我們人類感情的方程式”。龐德十分注重情感的表達,但是他并不只關注感情,也關注思想(理性)的表達,他不只一次地提到藝術給人們提供了有關“人性”和“思想”的“資料”。他說:“藝術給予我們有關理學的資料”;他甚至直截了當地提出文學“必須要求任何一種或每一種思想主張都達到明晰與生動……”可見,龐德關于詩的情感方面,強調的是理性與感情的交融。因而龐德在創作《在地鐵車站》時,并不是把他自己的內心情感一下子全直白地展現出來,而是經過思考與提煉,使得情緒化的感情提升為理性化的詩句,龐德就曾說過“意象是在一剎那時間里呈現理智與情感的復合物的東西。”正是這種理性與感性并存的意象,使得詩句具有持久的韻味,讓讀者回味無窮。相比之下,在詩歌的表達方式上,有些詩人的作品則顯得比較直白,如郭沫若的《我是偶像的崇拜者》,就是自我情感的直接抒發:
“我崇拜創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臟;/我崇拜炸彈,崇拜悲哀,崇拜破壞;/我崇拜偶像破壞者,崇拜我!/我又是個偶像破壞者喲!”
沒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完全是詩人感情自然流瀉,這樣的直抒胸臆固然有它的雄渾豪邁氣質,但是跟龐德的《在地鐵車站》比起來,就顯得缺少一種內在的張力美。直接的感性的勃發,而缺少理性的節制,在藝術蘊藉的深沉上明顯要比龐德的詩歌遜色。而龐德的詩將感性和理性二者兼容,融會貫通,給人以獨特的審美情感體驗。龐德在“我是怎樣開始的”的文章中描述了《在地鐵車站》的形成過程:“足有一年多的時間了,我一直在試圖為一個非常美麗的事物寫一首詩,我在巴黎地鐵目睹了這個場景……那一整天,我都試圖找到言詞來描述這種情景給我的感受。”作者最后將自己的情感隱藏在“意象”后面,而這意象也正是作者“理智與情感的復合物”。正是這樣的感性與理性的交織,使得詩句看起來平靜,實則內在的張力十足。
三、意蘊張力
有張力的詩歌在意蘊上常常表現為不確定性和多義性,表現出似有若無、撲朔迷離的意境,以喚醒人們的體驗,引起人們的想象,使人獲得奇美的享受。文學張力追求文本的多義性,即力求在有限的文字空間容納多種意義。經久不衰的詩歌必然擁有某種“多義性”,他們在自己的結構中包含一種或者更多種可解讀性,這既是詩歌在意蘊上的張力。《在地鐵車站》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四個單詞,但是卻充滿了張力,有著多義含混的特質。
《在地鐵車站》十分短小精煉,信息量有限,僅有五個意象迭加而成:幽靈、臉龐、人群、花瓣、枝條。重心落在面龐和花瓣上。可是,面龐和花瓣到底是什么關系呢?這首詩在刊印時出現過兩個版本,如果按最初刊印本來看即第一句結尾符號是冒號的話,我們就可以認定,第二句是對第一句的解釋,即面龐似花瓣。如果第一句結尾符號是分號的話,則又可以認定兩句呈并列關系,面龐與花瓣沒有比喻關系,兩者重疊出現或者交互出現。以如今通行刊印的分號來看,龐德避免了簡單的比喻,譬如“花瓣似的面龐”、“面龐似花瓣”,而是呈現給讀者“面龐”和“花瓣”兩個并蒂意象。這就給了我們多義解讀的可能。
從“面龐”“花瓣”兩個意象并列的角度解讀。第一行詩,“人群中幽靈般顯現的面龐”可以說是現代都市文明的濃縮剪影。在擁擠的人群中,人來人往,行色匆匆,彼此相會而又彼此擦身而過,這不正是現代都市生活的真實寫照嗎?“幽靈”一般給人的感覺是冷漠的、無表情的,人群中幽靈般顯現的面龐,可以說是真實生活在機械化社會里的人們被異化,人情味逐漸丟失的生存狀態的復現。暗含著詩人對快節奏的現代工業文明的調侃和不滿意。而第二句“濕漉漉枝條上的花瓣”是多么愜意的景致,詩人聯想到雨后的田園風情,給人以清新的回想。第二句的田園景致與第一句的現代文明剛好相對,忙碌與閑適,工業與田園。由此可見,第一句描寫現代生活實景,第二句追尋遠古美夢,兩句詩一分號聯接,即可看作是現代人追憶田園的顯示,也可看作遠古人對未來的向往。
從“面龐似花瓣”的角度解讀,又可體察出另外一番詩味。地鐵仍是現代城市的最好注腳,而地鐵中最奪目的風景便是一張張鮮活而生動的面龐。詩人在地鐵看到這美麗場景后,找到了與面龐想對應的事物——花瓣,用鮮艷的花瓣來比喻地鐵中美麗的面龐,把濕漉漉的樹枝比作陰暗潮濕的地鐵站,而“幽靈”又可以從時間維度上解讀,象征著美好的事物停留的時間過于短暫,給人以形象直觀的感受。所以無論是地鐵中富有生機活力的面龐還是美麗的花瓣,都給讀者易于消逝的感覺。而這種現代生活中稍縱即逝的美,引發了現代讀者無限的共鳴與深思。
[1]王劍.詩歌語言的張力結構[J].當代文壇,2004,(1).
[2]束定芳.論隱喻的詩歌功能[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0.
[3]張英.英語詩歌中的變異與突出[J].外國語言文學研究,2007.
I106
A
1673-0046(2010)7-018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