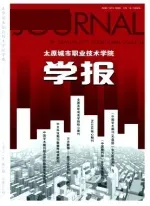從銜接與連貫的角度論詩歌翻譯
——以《雪夜林畔小駐》中譯為例
郭蘭蘭
(三峽大學,湖北 宜昌 443002)
從銜接與連貫的角度論詩歌翻譯
——以《雪夜林畔小駐》中譯為例
郭蘭蘭
(三峽大學,湖北 宜昌 443002)
許多學者熱衷于用銜接與連貫理論研究小說、散文、戲劇、新聞等文體形式,而將其系統地應用于詩歌文體或其翻譯研究中的較少。詩歌作為特殊的文學文體有特殊的銜接與連貫特征。論文試以余光中的《雪夜林畔小駐》中譯本為例,從形式銜接與意義銜接兩個方面來分析譯詩中連貫的重構。
銜接;連貫;重構;形式銜接;意義銜接
詩歌翻譯因其形式與意義的特殊表現手法往往使其在形式與意義的選擇中無法做到兩面俱全。正如西方學者所言詩歌是翻譯中所丟失的東西,詩歌翻譯的確存在一定的難度,但從詩歌的文體形式來講,翻譯中應從宏觀與微觀兩方面來重構原詩歌的銜接與連貫。
一、銜接與連貫
銜接是使語篇達到連貫的各種手段和方式,分為形式銜接與意義銜接。形式銜接包括句內與句際銜接,意義銜接則主要依靠修辭手段、語篇結構、邏輯思維等實現。在Halliday&Hason合著《英語中的銜接》以來,連貫就成為學者研究的熱門話題。一般認為銜接與連貫是統一不可分割的,銜接手段與銜接方式是重構語篇連貫的重要特征。
二、詩歌翻譯中的銜接與連貫
詩歌有其獨特的詩學形式特征和意義表達方式,這些特別的詩學形式特征和意義表達方式構成詩歌的連貫,從而使譯文讀者從宏觀和微觀上了解欣賞原詩的意蘊。從這個目的出發,譯者的任務就是要實現原詩的形式美與意蘊,即有目的地重構原詩的連貫,因此在詩歌翻譯中有效地運用銜接手段與銜接方式是成功翻譯詩歌的重要任務。以下是原詩與譯詩:
StoppingbyWoods on a SnowyEvening
Whose woo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though;
He will not see me stoppinghere
Towatch his woods fill up with snow.
Mylittle horse must think it queer
Tostop without a farmhouse near
Between the woods and frozen lake
The darkest eveningofthe year.
He gives his harness bells a shake
Toask ifthere is some mistake.
The onlyother sound’s the sweep
Ofeasywind and downyflake.
The woods are lovely,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keep,
And miles togo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gobefore I sleep
雪夜林畔小駐
想來我認識這座森林,
林主的莊宅就在鄰村,
卻不曾見我在此駐馬,
看她林中積雪的美景。
我的小馬一定頗驚訝:
四望不見有什么農家,
偏是一年最暗的黃昏,
寒林和冰湖之間停下。
它搖一搖身上的串鈴,
問我這地方該不該停。
此外只有輕風拂雪片,
再也聽不見其他聲音。
森林又暗又深真可羨,
但我還要守一些諾言,
還要趕多少路才能安眠,
還要趕多少路才能安眠。
(一)形式銜接
形式銜接指在句內和句際中運用一切有形的銜接手段使話語連貫,主要是由語言本身的因素構成,如語音、語法和詞匯等。
1.語音銜接
詩人對詩句的語調和音韻非常重視,因為和諧的語調和音韻最能加強詩歌的音樂感。音韻常見的有頭韻、半諧韻、尾韻和和聲。此詩是一首漂亮的押韻詩,基本韻律是四步抑揚格(AABA BBCB CCDC DDDD的韻腳形式)。一共四小節,每一小節1、2、4行押韻,第3行的尾韻是下一節的韻腳。這樣的韻律格式讓人感覺詩節之間的聲音和意義環環相扣非常緊湊。最后一節同押一個韻,讓人有完整和諧的感覺。譯詩的韻律基本與原詩一樣:lin/cun/ma/jing;ya/jia/hun/xia;ling/ting/pian/yin; xian/yan/mian/mian,在語音銜接手段方面基本重構了原詩的銜接手段,讀起來朗朗上口極富樂感。
2.語法銜接
韓禮德和哈桑指出,從形式上看語篇是由相互聯系的小句組成,而這些小句主要是通過五種銜接紐帶串聯起來,即指稱、省略、替代、連接和詞匯銜接,前四種是語法銜接。替代與省略在原詩較少體現,論文主要介紹語法銜接中的指稱與連接。
(1)指稱,或指代銜接,分外指與內指。外指是指用一個詞或短語來指代情景語境中的某一事物。內指一般發生在語篇內,進一步可分為前指與后指。前指指用一個詞或短語指代前文中的詞或短語;后指正好相反指用一個詞或短語指代后文中將提到的詞或短語。
原文中的指稱有:(a)Whose woods(1句)-these(1) -the(woods)(7&10);(b)Whose(1)-His(2)-he(3)-his(4);(c) Mylittle horse(5)-He(9)-his(9)。譯詩中對應的翻譯是:(a) /-這-林&森林;(b)/-林主的-/-他;(c)我的小馬-它-/。有些指稱被譯成實詞或省略不譯,這種避虛就實和零式銜接方式與英語中偏愛用指稱銜接方式相反。譯詩中的銜接形式與原詩不盡相同,但譯詩同樣構建了原詩的連貫,因為語法連貫的本質或功能就是語法連通,譯者的責任是要用具有同等功能和效果的方式重構指稱與被指稱的預設和被預設之間的語法關系。此外,英語是綜合型和分析型互參的語言而漢語是分析型語言,英語對語法依賴較大,語篇連貫通常靠顯性的語法形式體現,而漢語常用隱性的銜接方式或語意形成連貫。
(2)連接手段是在前言與后語之間建立系統聯系的專門用語,韓禮德和哈桑區分了四種連接關系:附加、轉折、因果、時間。連接是人類運用于邏輯推理的基本手段,因此這四種連接關系同樣存在于漢語中,意味著英漢語中有同樣的銜接手段,因此,在翻譯中譯者采用形式對應的方式即可體現原語連貫機制的特點。原詩的連接手段主要體現在最后一節:But/And/And,對應翻譯:但/還要/還要。
3.詞匯銜接
詞匯銜接指詞項間詞匯意義上的聯系,即通過選擇運用詞匯在語篇中建立貫穿篇章的鏈條來達到連貫的目的。這些詞匯或重復或由其他詞語替代或共同出現,構成語篇連貫性和完整性,以保證篇章主題或語義的統一。詞匯銜接分為復現和同現(或搭配)。
(1)復現銜接
復現指在階的一端對某一詞項的重復;在階的另一端用概括詞對某一詞項的回指;還有一些是處于中間地帶的同義詞、近義詞或上義詞的使用。復現關系分為重復和同義關系。同義關系包括同義、近義、反義、上下意義和部分整體關系。重復關系的詞在語篇中構成重復性銜接突顯語篇主題。詩中沒有體現同義,在此不再贅述。
詩人很好地借用重復性銜接,原詩中“I”重復出現五次,“woods”四次,“think”、“house”和“he”分別重復了二次,重復銜接方式反復再現增強了詩的音樂效果,突出其地點與人物,使讀者有身臨其境的感覺。“Miles togobefore I sleep”在詩尾處的重復更別具匠心,不僅賦予詩極強的音樂效果,而且有效地凸現了詩的內涵和意蘊,在讀者心中產生了強烈的震顫和感應。這些重復在譯詩中都得以再現,盡管“I”在譯詩中重復出現次數不及原文,但其意義隱含在其中,因為漢語重意合,“我”常出現會使語篇不自然,省掉更符合漢語表達且讀者也能讀出其存在。譯詩以相同的重復銜接方式重構了原詩的連貫。
(2)同現銜接
同現即搭配,指詞之間在同一語境中同時出現的組合關系,即什么詞經常與什么詞搭配使用。在特定語境中,詞匯搭配顯然是作者精心選擇而成,這些選擇性的詞匯搭配無疑可服務于重構語篇連貫,加強語境預設。原詩語境是在一個寒冷的雪夜詩人獨自一人徘徊在覆滿白雪的森林邊,只有詩人的小馬在身邊,而要到達目的地還有很長的距離。Snow/frozen、darkest/evening、horse/harness、bells/shake、easy/wind、downy/flake、
woods/deep、promise/keep、miles/go等搭配揭示了詩歌的主題與詩人復雜矛盾的心情。對應翻譯是雪——冰、最暗的——黃昏、馬——身上、串鈴——搖一搖、輕——風、拂——雪片、森林——深、諾言——守、路——趕,譯者在保證漢語搭配習慣前提下基本上直譯原詩的搭配,再現了原詩同現銜接,以確保全詩的連貫。
(二)意義銜接
意義銜接指根據具體語境,不運用明顯的銜接手段,而是依靠意義或內容使語篇連貫的手法。這種內部聯系大多是通過修辭、結構和邏輯實現的。
(1)修辭手段
詩人用“think”、“he”和“his”等詞將小馬看作有思維的人,詩人獨立于自然和人類世界之間觀賞大雪覆蓋的樹林,就連馬也不知道主人是否應該在這樣的地方停息,更彰顯了詩人的矛盾心理。最后小馬搖一搖身上的串鈴提醒詩人前行。擬人化表達方式:think it queer,he和his分別翻譯成了:頗驚訝、它和省譯。His被省譯與漢語的分析型語言特征有關,其意義功能與原詩仍一致,唯一翻譯不成功的是原詩擬人化的“he”被譯成了“它”,沒能完整地構建這一修辭手段所構建的語篇連貫。此外詩中還用到暗喻的修辭手法。那片可愛、又暗又深的“森林”暗指某種對人有著無窮魅力的神秘而不可知的東西,而文章末尾的“安睡”暗示著一種停止、放棄。最后詩人用疊句強調自己有事在身肩負責任的重大,必須離開樹林。譯詩中這些暗喻讀者也可感受到:“森林又暗又深真可羨……才能安眠”。
(2)語篇結構
語篇結構也是實現語篇連貫的手段之一,有內部聯系的詩歌具有一種整體性和統一性。詩歌整體意境由整體的結構來實現。任何文體都有一定的語篇規則,詩人為達到整體連貫和統一必然會遵循一定的原則。原詩采用了詩歌的基本結構,全詩共四個小節,每小節四小句,每小句八個音節,小節之間的韻律規則中有變化,形成環環相扣,將詩的意境與主題層層推向高潮至結束。譯詩同樣分四小節,每小節四小句,每小句九個音節,韻律也基本同原詩保持一致,因此譯詩可以說是成功重構了原詩在結構上的連貫。
詩歌翻譯的主要目的是要使讀者能感受和欣賞原詩的語言與形式特色和意蘊,這就要求譯者用目標語再現和重構原詩的語言與形式特點以及原詩的意蘊,保持原詩整體的銜接手段與連貫,并應在翻譯時盡量保持以同樣功能的銜接手段再現原詩的連貫。
[1]陳江榮,郭嘉俊.音與意的和諧統一[J].安徽文學,2009,(5).
[2]王東風.連貫與翻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H315.9
A
1673-0046(2010)7-02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