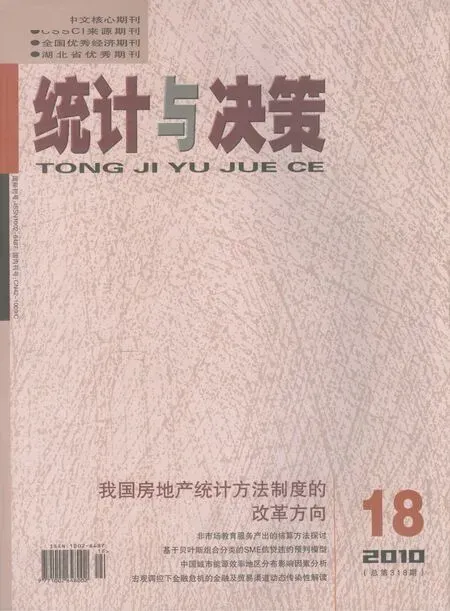宏觀調控下金融危機的金融及貿易渠道動態傳染性解讀
李 成,王建軍,張國柱
(1.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西安 710061;2.中國人民銀行 白銀市中心支行,甘肅 白銀 730900)
宏觀調控下金融危機的金融及貿易渠道動態傳染性解讀
李 成1,王建軍1,張國柱2
(1.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西安 710061;2.中國人民銀行 白銀市中心支行,甘肅 白銀 730900)
文章用金融危機四階段周期理論剖析金融危機的傳染機制。通過構造金融渠道危機傳染模型及貿易渠道危機傳染模型,對20國集團國家金融危機隱蔽期、危機爆發期、危機深化期和危機恢復期的數據進行檢驗,得出結論:金融渠道具有顯著地周期性危機傳染特質;貿易渠道具有次顯著地周期性危機傳染特質,傳染性變化與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滲透同步;貿易渠道傳染性周期演進滯后于金融渠道;金融危機恢復期宏觀經濟變量顯著性增強,表明調節宏觀經濟政策可以降低金融危機的傳染性。
金融危機傳染;金融危機四階段;金融渠道;貿易渠道
0 引言
2008年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金融危機。此次金融危機走過了一條烈度漸進式增強的發展軌跡。金融危機爆發模式的改變與危機傳染模式的演進具有直接關系,揭示金融危機傳染渠道的傳染性在整個金融危機爆發過程中的動態變化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的認識金融危機,并提出有效地宏觀經濟措施抑制其傳染性,以達到控制危機爆發烈度的目的。Reuven Glick和Andrew K.Rose(1999)通過區域貿易模型,對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發生的幾次區域金融危機的傳染進行了分析,指出區域貿易是區域金融危機傳染的重要通道,而宏觀經濟變量在其中作用甚微。鑒于進入21世紀以來飛速發展的運輸及信息科技,國家間的貿易已經突破了地理上的限制,全球范圍的資源配置與商品流通將各國的經濟捆綁在一起,從初步證據來看,貿易渠道對于金融危機的傳染作用明顯,本文將深入剖析貿易渠道危機傳染性的動態變化。同時經濟的全球化伴隨著金融全球化,資本突破國家界限在世界范圍內尋找最佳的獲利點,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引起了危機由直線到網狀交叉的復雜傳染,揭示金融渠道的危機傳染的動態性也是本文的主旨。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均提出了宏觀經濟刺激計劃,本文從宏觀經濟變量的角度出發,探討這些宏觀經濟振興方案對于減弱金融危機傳染、幫助宏觀經濟復蘇的作用。
1 理論分析
1.1 金融危機周期模型
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較低,呈現出危機從爆發到恢復的時間段相對平穩期短很多的特點,因此需要關注的時期僅是危機從爆發到恢復的整個過程。金融危機的進程也具有周期性,Arthur Burns和Wesley Claire Mitchell在其著作《測定經濟周期》中最早對經濟周期做出了經典定義。他們認為經濟周期是一國總體經濟活動的波動,一個完整周期要經歷經濟活動從低水平開始的擴張,達到階段性經濟頂峰后進入衰退和收縮期,最后經濟會重新從低谷中復蘇,這個變化是重復發生而非階段性的。因此經典的經濟周期理論將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定義為從一個經濟低谷到另一個經濟低谷的過程。
本文將一個完整的金融危機周期定義為從隱蔽期開始,經歷危機爆發期、深化期和恢復期后重新回到隱蔽期的過程。基于凱恩斯學派的乘數加速數理論,拓展出適應金融危機分析的周期模型,進而對金融危機傳染的周期性進行探索。薩繆爾森對經濟周期的乘數加速數模型做出了貢獻,他以國民收入方程Q=C+I+G為基礎,給出了經濟運行的方程組:

其中Qt為時期t的總收入,Ct為時期t的總消費,It為時期t的投資凈額,Gt為時期t的政府支出,c0為自發性消費,i0為自發性投資,a為加速數,b為邊際消費傾向。
經過整理后可得:

凱恩斯認為企業家做出的投資決策來自于對于未來盈利的預期,正是這種預期的變化導致投資的波動性,進而對經濟產生沖擊,使經濟呈現出周期性運行的特點。他將這種預期的變化歸結為企業家的 “動物精神”,“一種自發的行動而不是行動的沖動所致,不是根據收益乘以概率的加權平均數做出的。”從方程⑴中可以看出,c0和i0都具有自發性質,符合凱恩斯所定義的“動物精神”,于是設I0=c0+i0,I0是一個由“動物精神”決定的外生變量。由此方程⑴可整理為:

從方程⑵出發,用它來解讀金融危機的生命周期。
1.2 金融危機周期中金融渠道與貿易渠道傳染性分析
一定區域內的國家傾向于向某個主要的國家銀行借貸以發展經濟,一旦區域內某國發生金融危機,其他國家發生危機的概率高于區域外的非危機國家,首先發生危機的國家稱為危機源國,本文構造的模型通過分析危機源國與其他國家在爭取某一國家投資時的競爭性衡量其金融渠道的傳染性;分析直接貿易及在第三國市場的貿易競爭性來衡量貿易渠道的傳染性。此次世界金融危機的特點在于全球性,波及眾多國家的同時涉及非常復雜的資金往來,而危機源國是美國。美國作為世界上吸引外來資金最多,金融市場最具吸引力的國家,只衡量其對某一區域資金的吸引力是不夠的,本文將區域性研究的邊界拓展至全球。
(1)金融危機爆發期——金融渠道率先發生傳染
金融危機的爆發具有突然性,現有的技術很難對金融危機的準確發生時間進行預測,因此當金融危機進入爆發期,前期的收入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發生變化的僅是由“動物精神”決定的I0。在金融危機的爆發期I0會大幅萎縮,并且會持續性萎縮,表現為各國當期Qt及以后各期總收入 (Qt+1,Qt+2,Qt+3,…)劇烈下降。金融危機爆發之初各國政府無法及時擴大財政支出,這個時期的Gt可以視作常數。因此,在爆發期,各國投資者對危機發源國未來盈利預期的逆轉促使他們大量撤出資金導致資本市場下挫,在危機發源國投資越多的國家受到的損失越大,由于投資國金融機構需要調整自身風險承擔能力,銀行需要恢復自身資本充足率,投資基金面臨增收保證金的壓力,導致了風險從發源國外溢至投資國,并牽累投資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可見金融危機可通過金融渠道發生傳染,且這種傳染非常迅速。
(2)金融危機深化期——貿易渠道表現出傳染性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金融機構倒閉,證券市場崩潰,廠商資金鏈斷裂進而大量企業破產,工人失業。伴隨著經濟的巨幅下落,金融業收入持續萎縮。由于金融危機爆發期I0的逆轉,導致其后各期收入(Qt+1,Qt+2,Qt+3,…)大幅下降,從方程⑵中可以看出,這種收入下降如果沒有外生因素的影響將一直持續下去,形成“收入黑洞”。因此,金融業從金融危機中走出需要自發性投資和消費I0及政府支出Gt的擴張,而I0是由“動物精神”決定的,在金融業沒有產生任何復蘇跡象的時刻消費者和企業不會主動擴張I0。危機發源國經濟收縮導致進口需求下降,其主要出口國受此沖擊在一段時期內收入會不斷下降,類似危機發源國,這種收入下降如果沒有外生因素影響將持續下去,出口國隨即感染金融危機,至此金融危機完成了通過直接貿易的傳染過程。而危機發源國在第三國市場上與他國的競爭越強,表明危機發源國對第三國的重要性越大。危機爆發后,危機源國進口的減少導致第三國經濟收縮,從而導致第三國對其他國家進口的減少,直接促使其他國家經濟萎縮,金融危機由此通過間接貿易渠道傳染。
(3)金融危機恢復期——貿易渠道傳染性強于金融渠道
從當前金融危機看,世界各國在危機深化期都拿出了大量的經濟刺激方案,擴大政府支出,然而金融危機在經濟刺激方案實施之后,由于下滑慣性、消費者及企業家預期逆轉的滯后性,金融危機會繼續深化直到觸底。隨著政府經濟刺激計劃見效,廠商復工增加,工人就業上升,金融危機步入恢復期。這一時期I0開始大幅增長,且在政府前期投入的拉動作用下,金融業收入Qt產生恢復性增長。隨著各國宏觀經濟數據傳出金融危機觸底的信號愈加強烈,企業家和投資者由強烈看空轉向謹慎看多,世界范圍內經濟增長和金融交易趨于平穩,危機發源國金融市場獲利性的緩慢回升有助于提振他國投資者的信心,資金開始回流,同時國內需求的復蘇促使危機發源國進口更多的商品,國際貿易走上正軌。金融危機傳染的金融渠道在這一時期會減少并逐步恢復到危機隱蔽期的水平,但是由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滯后性,貿易渠道傳染性還處于上升趨勢中,在金融危機的恢復期中貿易渠道傳染性將強于金融渠道。
2 模型與計量檢驗
2.1 模型設定
為了切實揭示金融傳染渠道和貿易傳染渠道在金融危機傳染過程中是如何發揮其作用的,下文利用20國集團國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期間的數據進行計量研究。在Glick.A和Rose(1999)及Caroline Van Rijckeghem和Beatrice Weder(2001)文獻框架的基礎上加以拓展,提出本文的計量模型。這次世界金融危機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在危機的隱蔽期、爆發期、深化期中,金融渠道和貿易渠道在危機傳染中作用的動態變化是計量檢驗的重點。在此次金融危機的每個時期都將運用以下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設定金融危機的傳染變量是一個雙值變量,如果一個國家發生了金融危機,傳染變量便取值為1,反之則為0。設置雙值變量可以明確的表明危機的發生及傳染,缺陷在于無法表達發生在眾多小國間的集群式復雜金融危機傳染。
(1)金融渠道危機傳染模型。
金融渠道傳染變量(Financei)用于衡量危機發源國與其他國家爭奪資金的程度。Caroline Van Rijckeghem和Beatrice Weder(2001)在他們的論文中設定該變量為危機發源國與其他國家競爭來自同一國家銀行的資金,這樣的定義適用于對小國危機的研究,不適應美國這樣與多國均存在緊密金融聯系的大國,因此本文擴大資金來源國的數量,將美國重要的經濟伙伴囊括其中,同時對國家間資金的往來不僅局限于銀行借貸,擴大至廣義的國家間資金流動。數據處理量的加大,有助于計量結果更趨近真實。
金融渠道傳染變量的計算受啟發于GlickA和Rose(1999)對于第三市場貿易競爭變量的定義,通過對他們提出模型的改進得出本文的金融渠道傳染變量:

Financei(share)是個加權平均值,衡量資金提供國k對于a國及i國的重要性,當k國對于這兩國的重要性相等時這個指標取得最大值。該指標的第一部分衡量k國對于a國及i國的總體重要性,第二部分確定a國與i國爭奪來自k國的資金的競爭強度。Financei(share)的值越大表明資金爭奪的競爭越激烈。fik表示k國流向i國的總資金量,fak表示k國流向a國的總資金量(k≠a,i),fa.表示流入 a 國的資金總量,fi.表示流入i國的資金總量,本文中a國為美國。
通過衡量各國從他國獲得資金的總量而非份額,可對上述指標作出另一種變化:

GlickA和Rose(1999)在通過廣泛的檢驗發現用上述兩種指標來衡量貿易競爭均是可以的,在本文中我們將驗證它們是否可以有效衡量國家間對資金的競爭,并以此確定金融傳染渠道的存在。
(2)貿易渠道危機傳染模型。
本文從兩方面衡量貿易傳染渠道,分別是直接貿易和危機發源國在第三國市場上與他國的貿易競爭。直接貿易用某國到危機發源國的出口總量占危機發源國總進口量的百分比來衡量:

其中tai表示i國對危機發源國a的出口量,ta.表示a國的總進口量。
對于危機發源國在第三國市場上與他國的貿易競爭,本文沿用GlickA和Rose(1999)的經典定義:

Tradei(share)的值越大表示危機發源國a在第三國市場上與i國的貿易競爭越激烈。a國和i國對k國的重要性與他們在k國總進口中所占權重呈正比。當k國對于a國和k國重要性相同時,Tradei(share)取得最大值。其中tak表示k國對a國的出口總量,tik表示k國對i國的出口總量(k≠a,i),ta.表示a國的進口總量,ti.表示i國的進口總量。
(3)宏觀經濟政策
本文選取一系列可能與金融危機有關的宏觀經濟變量加入模型,以探討宏觀經濟對于金融危機傳染的影響情況。選取的變量有M2對國家外匯儲備的占比M2/reserve;社會信貸總量的變化百分比;實際有效匯率;經常賬戶占GDP的百分比;國內通貨膨脹率。
2.2 計量檢驗結果
本文將2007年5至10月設為金融危機隱蔽期,2007年11月至2008年4月設為金融危機爆發期,2008年5至10月設為金融危機深化期,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設為金融危機恢復期。
將金融渠道、貿易渠道的危機傳染性檢驗結果總結如下:
從表1中看出金融渠道傳染性變量的顯著性水平隨著危機從隱蔽走向爆發、深化而不斷增強,同時金融渠道傳染性變量Financei的顯著性水平較高,可以證明金融渠道傳染性的存在。金融渠道傳染變量系數一直保持上升,在危機深化期達到最大,從危機恢復期轉為逐步降低,表明金融渠道的傳染性伴隨危機進程而出現相應周期變化。

表1 Ⅰ危機隱蔽期、Ⅱ危機爆發期、Ⅲ危機深化期金融渠道及貿易渠道傳染性檢驗
貿易渠道傳染變量顯著性從危機爆發期開始保持上升的趨勢,滯后于金融渠道傳染變量。貿易渠道的傳染性變量系數從危機爆發、深化至危機進入恢復期不斷升高,在恢復期開始高于金融渠道傳染系數,但其顯著性多低于同時期的金融渠道傳染變量,這個結果印證了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過度的時滯性,可以預見,隨著實體經濟觸底反彈,金融系統穩定性增強,貿易渠道的傳染特性將不斷降低。直接貿易變量DirectTradei及危機發源國在第三國市場上與他國的貿易競爭變量Tradei(share)的顯著性變化趨勢相同,均隨著危機周期走向深入,顯著性水平不斷升高。
可見金融渠道的傳染性要更加靈敏,甚至在危機的隱蔽期其傳染性已經開始顯現。貿易渠道的傳染性出現相對較晚,隨著危機程度的加深通過危機國與他國的貿易實現金融危機的傳染,其傳染性在危機恢復期較金融渠道更大。
從結果中發現,由于世界金融危機涉及國家眾多,且發生迅猛,加之宏觀經濟政策的滯后性,導致其與危機傳染性相關性在爆發期、深化期較弱。宏觀經濟變量中社會信貸變化和M2/reserve在金融危機的恢復期內顯著性明顯增強,說明各國的經濟刺激計劃開始發揮作用。信貸擴大和貨幣供給量的增加促使投資的上升,增加有效需求幫助經濟走出下降通道。
2.3 結果穩健性檢驗
通過對理論模型的微擾來確認上述檢驗結果的敏感性。穩健性檢驗的結果總結在表2、表3、表4中。針對表2中宏觀經濟變量在危機前期顯著性較低的情況,用其他宏觀經濟變量對原有回歸變量進行替換。本文選擇M2增長率;政府預算與GDP比值的變化量;經常賬戶與GDP比值的變化量;社會投資與GDP的比率。本文在選擇宏觀經濟變量時參考了GlickA和Rose(1999)研究中的做法。
從表2中可以看出M2增長率、社會投資/GDP等宏觀經濟變量在替換之后的顯著性依然在金融危機恢復期開始增強,證明表1中所呈現的結果是穩健的。接著,利用其他金融渠道傳染性變量和貿易渠道傳染性變量對原模型中變量進行分別替換,總結如表3、表4,表中省去了其他變量的回歸結果。
表3的檢驗中宏觀經濟變量與表2一致。使用三個其他金融渠道傳染性變量對模型中的變量進行替換。Financei(share)表示國家間資金爭奪的強度;國家吸引資金排名定義為,為危機爆發國提供資金最多的國家標示1,第二多的國家標示2,以此類推。金融渠道傳染性衡量變量替換之后,其顯著性依舊較高,說明表2中的結果是可信的。

表2 金融危機三周期傳染性檢驗穩定性驗證:宏觀經濟變量替換

表3 金融危機三周期傳染性檢驗穩定性驗證:金融渠道傳染性衡量變量替換

表4 金融危機三周期傳染性檢驗穩定性驗證:貿易渠道傳染性衡量變量替換
表4的檢驗方式與表3類似,對貿易渠道的傳染性變量進行替換,其結果沒有動搖表2結果的穩健性。
3 結論與思考
本文對金融危機進程的四周期進行了詳細分析,并構建了金融危機金融傳染渠道、貿易傳染渠道分析框架。通過對美國等20國在世界金融危機期間數據的模型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3.1 結論
(1)金融渠道具有顯著的周期性危機傳染特質。金融渠道傳染變量系數先升高后降低。其系數自危機隱蔽期始增大,經危機爆發期至深化期達峰值,至危機恢復期逐漸降低,表明金融渠道的傳染性伴隨危機進程的發展而呈現相應的周期性變化。
(2)貿易渠道具有次顯著的周期性危機傳染特質。貿易渠道傳染性變化與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傳染同步,其傳染性在危機隱蔽期沒有顯現。從危機爆發期、危機深化期直至恢復期其傳染性不斷升高,在恢復期其傳染性比金融渠道更強烈。
(3)貿易渠道傳染性周期滯后于金融渠道。在金融危機的四個周期中,貿易渠道傳染性具備與金融渠道傳染性相同的增強趨勢,但始終滯后于金融渠道。金融渠道的傳染性較同時期貿易渠道更為顯著,甚至在危機隱蔽期其傳染性已開始顯著。直到危機恢復期,金融渠道傳染性開始下降,而貿易渠道傳染性由于滯后效應繼續增強。
(4)宏觀經濟政策調節可以抑制金融危機的傳染機制。宏觀經濟變量在危機恢復期出現顯著性表明宏觀經濟政策對減弱金融危機傳染有抑制作用。社會信貸變化和 等宏觀經濟變量顯著性由弱變強的過程,揭示了各國宏觀經濟刺激計劃的有效性,但是由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滯后性,其作用在金融危機恢復期始顯著。
3.2 思考
(1)關于模型有效性的進一步驗證。資金競爭性傳染渠道模型及貿易競爭性傳染渠道模型對金融危機發源國的有效性已被前文驗證。但被傳染的國家是否也通過類似渠道將危機繼續傳染給更多國家,這個過程中本文的模型是否依然有效需要繼續的深入探討和檢驗。
(2)關于金融渠道和貿易渠道傳染性的存續時期。至本文中數據涉及的時期為止,金融渠道和貿易渠道的傳染性仍然沒有消失。隨著金融危機進入恢復期,這兩條渠道的傳染性將持續到危機再次進入隱蔽期,還是在危機恢復期便消失是值得繼續關注的問題。
(3)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時退出。目前世界經濟正在走出經濟低谷,這不僅體現在各國股市上,更得到經濟數據的支持。已經有國家開始調整金融危機時期的宏觀經濟政策:澳大利亞和挪威央行率先加息,印度也宣布上調銀行準備金率,美國經濟一年多來首次實現了正增長。中國公布的第三季度數據同樣表明今年GDP增速“保八”無憂。但是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經驗證明,在危機最嚴峻的時刻過去不久就退出宏觀經濟刺激無疑是錯誤的,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適時退出是值得商榷的。
[1]Reuven Glick,Andrew K.Rose.Contagion and Trade Why Are Currency Crises Tregional?[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1999,(18).
[2]Buiter,H W,Coresetti,G.,Pesenti P A.A Center-Periphery Model of Monetary Coordination and Exchange Rate Crises[C].NBER Working Paper,No.5140,1995.
[3](美)杰弗里·薩克斯 菲利普·拉雷恩.全球視角的宏觀經濟學[M].費方域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李成,王建軍.國際金融危機:直向性傳染到交叉性傳染的動態效應分析[J].財經科學,2009,(6).
[5]李成,王建軍.解讀信貸推動下的美國房地產泡沫與金融危機--基于2000-2008年月度數據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 [J].金融論壇,2009,(2).
(責任編輯/易永生)
F830.99
A
1002-6487(2010)18-0099-04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09AZD020)
李 成(1956-),男,山東濟南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金融監管與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