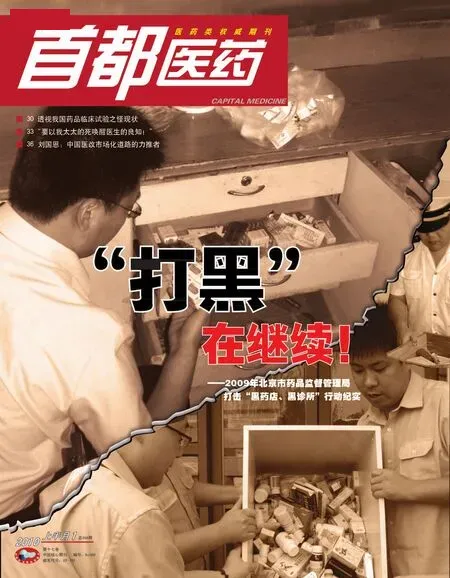統一的臨床診療指南缺失過度醫療在所難免
我國醫療衛生領域長期以來存在著兩個頑疾:一個是廣大農村人口、城市弱勢群體看病難、看不起病;另一個就是過度醫療,大處方、大檢查和“被手術”的盛行。近年來,醫患關系日益緊張,醫患矛盾不斷升級,究其原因相當一部分是由患者不滿醫生對其過度醫療所引起。過度醫療不僅給患者的身心健康帶來傷害甚至致死,而且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加劇病人看病難、看病貴,同時也損壞了醫院及醫護人員的形象,給病人、家屬及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對于過度醫療的原因,大部分患者把矛頭指向了醫生受經濟利益的驅使而致的主觀故意。而記者接觸到的一些醫生對此卻另有一番言論。
舶來的診療指南不合國情造成過度醫療
現在患者普遍反映的“看病貴”,很大程度上是由使用價格不菲的“高檔”藥物所致。例如對乙肝患者的治療用藥,國內推崇的拉米夫定、胸腺肽、干擾素等幾乎都是國外著名藥業集團的代表產品。但這些藥物在我國使用的療效大打折扣,諸如誘使病毒發生變異、停藥后肝炎復發和惡化等遺留問題日漸增多,又引發了新一輪本無必要的治療,造成過度醫療的惡性循環。而這樣的用藥方法恰恰源于我國參照歐美相關診療標準而制定的治療指南。

▲各種不同版本、科別的診療指南
對此,友誼醫院神經內科的王會剛醫生認為,這是由于國內目前沒有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疾病診療規范所致。現在我國的醫師法是和歐美國家接軌的,所以我國的某些臨床專業如心血管內科、消化內科等都有參照美國或歐盟的診療規范制定的一些臨床診療指南,且成為我國醫療訴訟的法律依據。因此,大多醫生為避免醫療糾紛,在診斷、治療疾病時,都會參照這樣的診療指南。可是這個指南并不是由我國的臨床醫生制定的,而是由很多學者翻譯、改編過來的。按這樣的標準,即使在較為發達的歐美國家也造成了30%的過度醫療,那么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出現過度醫療就更不足為奇了。
解放軍302 醫院中西醫結合肝病科主任劉士敬曾提到,我國最新制定的丙型肝炎防治指南幾乎就是歐美肝病協會制定的丙肝指南的翻版,例如其中要求丙肝診治需要搞清丙肝病毒基因分性和丙肝病毒RNA 定量數值,可是在我國這些檢查需要到省級以上醫院方可進行,意味著一個患者要跑到省城才能確診,才能治療;并且治療藥物選定為長效干擾素(派羅欣),一支1300 多元。這從根本上脫離了我國國情,畢竟我國和美國、歐洲國家的國情不同,經濟實力也無法同日而語。以此診療標準,想不過度醫療都難。
隨著世界醫藥產業的迅猛發展,輔助檢查的設備越來越先進,診療標準也隨之節節攀升,如過去是黑白超,現在是四維彩超;過去頂多做個CT 掃描,現在動輒核磁共振,這必然帶動醫療費用的持續增長。在治療上,除參照歐美的規范之外,由于我國的老百姓信任中醫,往往采取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法,如此一個病治下來,醫療費用與歐美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盡管我國的醫師法和歐美接軌了,醫學診療水平和歐美接軌了,可最重要的——我國的經濟水平卻沒能和歐美接軌,這就是導致過度醫療的主要原因。”王會剛醫生一語中的。
教條的診療指南難符臨床實際誘發過度醫療
曾經有一個病人,因為消瘦、不想吃東西,到一家頗具盛名的醫院看病。顯然這是消化系統疾病的典型主訴,醫生按照有關診斷標準給這個病人化驗了肝功能,做了胃鏡等消化系統的相關檢查,結果顯示一切正常。于是,醫生懷疑是功能性疾病,讓病人去找中醫試試看。病人來到北京中醫醫院,急診科周愛國主任留意到這個病人短期消瘦顯著這一細節,于是又讓病人做了肺部CT、頭部CT,結果是肺癌腦轉移。周主任說,當時自己其實也不能確定這個病人就一定是癌癥,只是根據自己多年的臨床經驗產生了高度懷疑,但如果這個病人不是癌癥,那么花2000 多塊錢做CT 檢查肯定會被視為過度醫療了,可如果當時不果斷讓他做這兩項檢查,肯定是漏診無疑。
周主任認為,臨床醫學是一門復雜的科學,醫生尤其是經驗不是特別豐富的醫生非常需要臨床診療指南的指導,而我國目前能符合臨床實際操作的診療規范付之闕如,現有的大多只是提供了一種臨床治療路徑,而從患者主訴到診斷落實這個過程的指導卻是乏善可陳。例如心梗患者在診斷明確后,治療方法基本是明確的,但是對于由主訴到確診心梗需要做哪些檢查卻沒有明文規定。例如,與心絞痛相類似的胸痛是心梗患者最早出現的癥狀,也是心梗患者最典型的癥狀。可是也有少數心梗患者沒有典型的胸痛癥狀,而是上腹部疼痛 (常被誤認為是患了胃穿孔、急性胰腺炎等病癥);部分患者的這種疼痛可擴散至下頜、頸部或背部等部位(常被誤認為是牙疼、骨關節痛等);還有一部分心梗患者無疼痛的表現,但在發病的初始階段可出現休克或急性心力衰竭。因此,對于諸如此類的牙痛、咽痛、頸肩痛、腰背痛患者,診療指南并沒有明確指出需要做哪幾項檢查才能確診。臨床上不得不做一些看似過度的檢查來明確是否是心梗,否則一旦誤診,病人能否存活將面臨嚴峻考驗。
北京中醫醫院急診科劉寶利醫生也有這樣的體會。他提到現在的診療指南大多都很刻板、教條,而急診科往往面對的是各種綜合性疾病病人,病情更為復雜且危重,診療規范那一套基本派不上用場。
故而,周主任認為現在我國的一些疾病診療指南只適用于某些教學醫院的診療常規,而并不是一個符合臨床實際要求的“金標準”。所以為了患者的利益,有時醫生也不得不逾越診療標準而采取一些“大包圍”的診療手段。
五花八門的診療指南亟待規范統一
我國臨床診療指南目前有這樣一個現狀:有些疾病擁有的各種不同版本的疾病診療指南不勝枚舉,然而質量卻良莠不齊,其中有些內容甚至相互矛盾,讓人無所適從(如抗凝治療)要求。記者試著在網上輸入“診療標準”的字樣,不乏各科專家要求建立統一的臨床診療指南的呼吁。混亂的現狀導致現實中很多醫生完全拋棄了診療指南的標準,不管水平高低,全憑“經驗”給患者看病,在一些小醫院尤其如此。
如今年上半年,河北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接到報告,一名患者在使用了神威藥業有限公司生產的清開靈注射液后死亡。該局安監處在對神威藥業有限公司進行檢查后,并沒有發現生產環節出現問題。“看了患者的用藥情況才發現問題。”這位處長說。患者就是普通的感冒發燒,但在兩個半小時之內,通過打點滴,醫生對其使用了包括清開靈、頭孢、病毒靈、胰島素等十幾種藥物。這是一個典型的過度醫療的例子,極富戲劇性的是,這位患者居然是所在醫院的副院長,正是他為自己開的藥,顯然沒有參照相關的診療指南,他對己尚且如此,那么這家醫院過度醫療的狀況便可見一斑了。
總之,當前過度醫療問題已引起社會、群眾的深惡痛絕,嚴重影響了醫院、醫護人員的聲譽,加深了醫患之間的矛盾及鴻溝。有專家說:“過度醫療將葬送我們的衛生事業。這不是聳人聽聞,不注意這一點,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固然遏制、杜絕過度醫療的措施應該是綜合性的,但是,其中最關鍵的措施是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臨床實際的統一的疾病診療指南和臨床路徑。因為盡管現在醫療的“度”看似掌握在醫生手中,可是由于沒有符合實際的統一的規定,所以在診療時醫生擁有很大的裁量權,而當符合我國國情與臨床實際的統一的疾病診療指南出臺后,醫療的“度”才明了,醫生方能準確把握。這樣的指南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衛生部部長陳竺在今年舉行的第十二屆全國實驗血液學學術會議上,以學者身份做了題為《通過應用規范臨床路徑按病種收費和以成本效果分析為基礎的新技術使血液病患者受益》的演講,而衛生部在不久前的一次會議上也提到,要“加快制定統一的疾病診療規范,探索臨床診療路徑,規范醫療機構行為,保障服務質量。”
然而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衛生水平相差甚遠,醫療衛生情況較為復雜,如醫院根據硬件和人員配備就可分為9 個層次,所以要想制定統一的疾病診療指南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但是若能落實,相信會對過度醫療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鏈接:診療指南的由來
上世紀70 年代David Sackett 等人認為臨床工作不夠嚴謹,完全根據個人經驗,經常出現謬誤,提出臨床醫療工作應以EBM(循證醫學)檢驗改善效果。美國心臟病學會(ACC)在上世紀80 年代起在EBM 基礎上逐步制定了一些臨床診療指南。1989 年美國聯邦政府為了改善醫療效果和服務質量,成立了一個特別機構——Agency for health career search and quality(醫療保健研究與質量局),后來又在Institute of medicine(醫學協會)協助下召集專家咨詢委員會制定了多種臨床工作指南,目的是使臨床醫學與時俱進保持領先,不但價格便宜,而且能提高醫療質量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