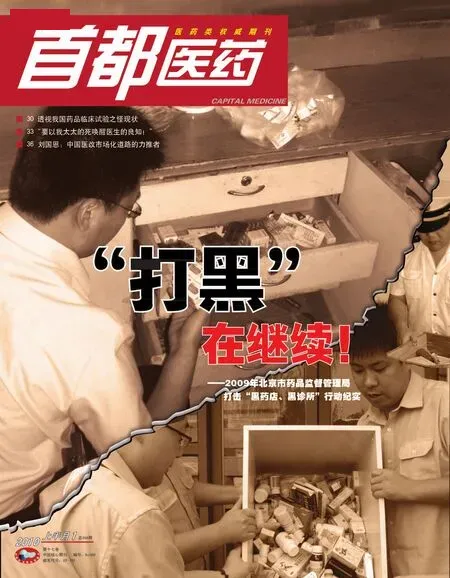LIUGUOEN劉國恩:中國醫改市場化道路的力推者

2009 年4 月,新醫改方案的公布就像投入靜湖中的一塊巨石,激起浪花朵朵、蕩出漣漪無數。由此引發的討論持續升溫。在這樣的日子里,劉國恩當然不甘寂寞。在去年6 月份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組織的“北京大學三井創新論壇”上,當著臺下很多醫改專家的面,他又“吵”起來了。
這次與他展開針鋒相對的辯論的是他的老對手、主張醫改公益化道路的代表人物李玲。實際上,早在新醫改方案征求意見時,兩人就各持己見、分庭抗禮,結果一路“打打殺殺”,直到現在。而且,可以預見的是,兩人之間的爭論還將繼續下去。
劉國恩與李玲,一個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教授,一個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教授;一個是醫改市場化的先鋒,一個是醫改公益化的旗手。兩人同因新醫改而風頭正勁、星光閃耀,在他們的身邊逐漸聚集起的“粉絲”越來越多。其實,他們私底下的關系非常不錯,但一涉及醫改中的某些關鍵問題,兩人馬上就“翻臉成仇”、堅守各自立場毫不退讓。
劉國恩,給人的感覺是特別精干,五十多歲的人了,還像中學生一樣在右肩上背一個鼓鼓囊囊的雙肩背包,讓人不得不感嘆留洋回國之人的瀟灑不羈。他舉手投足間,都讓人感受到激情四溢、活力無限,也許能成為運動飲料不錯的廣告代言人。
早在2008 年年末,就不斷有消息傳出新醫改方案很快就會出臺。人們盼星星盼月亮一樣期待著,想看看這次的新醫改會唱什么調。劉國恩等醫改專家參與了之前的意見征求與討論,對最終的醫改方案更是滿懷期待。終于,在一次又一次的“子虛烏有”之后,2009 年4月6 日,一拖再拖吊足了人們胃口的新醫改方案“千呼萬喚始出來”。
“醫改回歸公益性”,這是新醫改方案首先傳遞出的最明確的信息。很多人認為,這一定調,實際上已經為醫改的市場化思路宣判了死刑。長期以來公益化與市場化的轟轟烈烈的博弈,也許從此就以后者的全面潰敗而終結了。
但“到了黃河心也不死”的劉國恩還在“嘴硬”。“公益化目標不是反對市場化手段的理由”,他是那樣的理直氣壯、振振有辭。

▲劉國恩在北卡大學授課
在普通民眾對愈演愈烈的“看病難、看病貴”怨聲載道的時候,再去標榜“市場化”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市場化不是助紂為虐嗎?“市場派”先沒了市場。因此,劉國恩在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的一些節目里做的講座,“觀眾坐得稀稀拉拉的,幾乎沒有掌聲”。還有人指責他“別以為留過洋就可以抱住美國的模式不放”。
對于這些,劉國恩早就習慣了。“很多東西,你就要去探索、試點,不試怎么知道行不行?而且,不要忘了,真理往往是把握在少數人手中的”。
在自己有些孤單無助的時候,他會用“眾人皆醉我獨醒”這句話來給自己打氣。
“不作為比瞎作為好”
因為經常跟相關決策部門“對著干”,對現行醫療體制中的一些問題直指其弊,嘴下毫不留情,劉國恩不僅是專家,更是一位“磚”家,“拍磚”的行家。“假話廢話是好聽,但是沒意義。我也不想得罪人,只是沖著問題本身去的”。
但對于這次新醫改方案,劉國恩卻沒有“將拍磚進行到底”,而是一反常態,表達了不少肯定性意見。這看上去有些不像他的風格。頗有戲劇性的是,他這次大加肯定的一些內容,恰恰是大多數人廣為詬病的部分。他總是那樣的特立獨行、與眾不同。
新醫改方案甫一出臺,許多“磚家”便將早就準備好的“板磚”拋了過去,指責之聲鋪天蓋地而來。其中,最大的板磚是批評新醫改方案只有大的框架和方向,沒有實施細則。太多的“探索”、“試點”一類的字眼充斥其間,沒有一個板上釘釘的說法。于是人們進一步得出結論:決策部門不作為,是在逃避責任、應付民眾。這塊板磚看上去“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拍得合情合理、大快人心。
最近一段時間,劉國恩在全國各地走訪,發現很多地方對于新醫改方案中要試點的許多內容,遲遲不肯動作。“這離醫改方案發布都多長時間了?總是再等等再等等,三年的試點探索期一轉眼就過去了。沒有試點,還怎么總結經驗?又如何深化醫改?”
劉國恩有些納悶,對方卻理直氣壯:上頭沒有細則,我們怎么搞啊?劉國恩一時間有些哭笑不得:“中央怎么可能在短時間內拿出一套實施細則?就靠幾個專家、幾個領導坐在辦公室里想嗎?過去類似的教訓還少嗎?全國各地的差異這么大,一刀切的細則怎么可能通用?”所以,劉國恩認為,新醫改方案沒有實施細則反倒是正常的,如果有了所謂的細則,那一定是憑空想出來的,十之八九行不通。如果再放靠全國搞“一刀切”式的強制推行,那笑話可能就鬧大了。
在劉國恩看來,相關決策部門的“不作為”要比不懂裝懂的“瞎作為”好得多,表面上的內容空洞卻恰恰反映出工作中的積極務實。急功近利弄出一套細則來,肯定會壞事的。
“在新醫改條件下,各地沒有太多可供借鑒的現成經驗,需要自己來摸索。成功了,總結經驗之后可以考慮向全國推廣;失敗了,其他地區吸取教訓之后可以避免重蹈覆轍。這都是在為全國做貢獻”。所以,劉國恩希望各地能與時俱進,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積極探索。探索和試點本身就是對本次醫改最大的配合和支持。都在觀望,都在等待,都不敢跨出第一步,那么醫改就成了一句空話。
“我不怕人們不給我鼓掌”
劉國恩有些固執,有些不解風情,在民眾對“看病難、看病貴”恨之入骨的時候,他還在狂妄地喊著“市場化”的口號。他甚至語出驚人:公立醫院也要盈利!“不盈利就是可以浪費嘍。國家把納稅人的錢投進醫院,醫院更有責任把這些錢管好,只不過賺的錢不能裝進私人的腰包,而要用于醫院擴大再生產,更新設備,引進技術、人才等。”幸虧還有這番解釋,才稍稍平息了人們的憤怒。
在中國醫改中,“市場化”從來都是一個敏感的字眼。在普通民眾看來,它通常是與資本、逐利、競爭等詞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老百姓都已經看不起病了,醫院還要繼續“市場化”、繼續掙錢,那還讓不讓人活了?理所當然,鼓吹“市場化”的人比醫院還要可惡得多,不受歡迎是再正常不過了。
其實,劉國恩應該慶幸自己通常只給一些知識層次相對較高的人開講座,掌聲雖然稀稀拉拉不那么聲勢浩大,但畢竟還是有幾個“知音”的。如果他抱著自己的“市場化”論調去給老百姓講課,貨真價實的板磚可能就真的拍過來了。
如今,劉國恩早已適應了這種“曲高和寡”的感覺。好幾次去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錄節目,劉國恩贏得的掌聲通常都是最少的。“我早就習慣了,沒什么不好的感覺”。
“我不是刻意靠標新立異來搏出位,這是我內心的真實想法,我從來都是以嚴肅負責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發言的”——作為著名的醫改專家,劉國恩尊重民眾的想法,但不迎合、不忽悠。他覺得自己作為學者,負有引導輿論和民眾的責任。“人們不給我鼓掌很正常,總共不到半小時的時間,我們雙方還在辯論與交鋒,要人們一下子認同肯定有難度。但慢慢地,終究會有更多的人理解我的觀點”。
在看到新醫改方案中對于醫改公益性的定調后,按說劉國恩作為“市場與公益”之爭的失敗方,應該沉寂一段日子了。但他卻更為活躍與“囂張”,提出新醫改的公益性目標可以有多種實現方式,公益性不是否定市場化手段的理由。他還主張對公益性進行重新定義,指出公益性要通過醫療保障的支付力度和有效程度來回答,與醫療服務機構本身的屬性無關。“公益就是公眾受益,就是老百姓看病少花錢甚至不花錢。不管醫院是公是私,如果老百姓看病要自己來承擔醫藥費的大頭或全部,那就不叫公益了,只有自己需要拿出的一部分很少,才是公益。”這樣的論調不僅時髦,也有很強的說服力和可行性。
新醫改方案中關于“探索醫生多點執業”和“建立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與醫療機構、藥品供應商的談判機制”等內容的表述也讓劉國恩信心倍增,這正是他在之前的意見征求與討論中竭力倡導的,“看來有些話決策者還是聽進去了。”
對于醫改這樣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很多人對其前景并不看好。劉國恩也毫不避諱其難度與復雜性,但他充滿了信心。“我在很多演講的最后都用了‘任重道遠’這個詞,醫改不能一蹴而就,它的好多問題是長時間積累下來的,要解決也絕非一日之功,別指望著今天出臺一項措施,明天問題就完全解決了。不過只要大家積極探索試點、總結經驗,總會一點一點向好的方向發展。”
最初的夢想:做一名醫生
作為北大教授和醫改專家,劉國恩對自己目前的工作狀態感到很滿意:“可以站在更高的層面上,去關注醫療體制改革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并試圖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反映到政策制定當中去。如果我的意見是正確的,相關決策部門又碰巧采納了這樣的建議,那我就謝天謝地了。”

▲劉國恩與美國南加州大學的同事在一起
對于自己最終沒能成為一名醫生,劉國恩現在回過頭來看,了無遺憾。“醫生幫助的是一個一個的點,而我運氣好的話,受益的可能就會是一個面。”
但劉國恩最初的夢想很簡單,就是當一名醫生,一名不歧視農村人的好醫生。因為自己遭遇了太深的歧視,他不想讓其他人再有同樣的創痛。
在他的童年記憶里,籠罩了太多的陰霾。至于艱苦的生活條件,劉國恩并不放在眼里。但因為父親是流放落戶的,隨之而來的同鄉人的欺負和城里人的鄙視讓他極度郁悶。
高中畢業后,因為在村里文化程度最高,劉國恩就被合作醫療站“相中”,當起了赤腳醫生。沒有什么準備,前一天收到通知,第二天找了個大箱子,畫上紅十字,就跟著一位老中醫出診了。
在劉國恩的記憶中,當赤腳醫生有幾個好處:需要出診的時候就可以不用從早到晚地在山上砍柴;隔幾個星期合作醫療站就要開一次會,自然也能避開沉重的體力勞動。而且,隔幾個月說不定還能吃一回肉,打打牙祭。
1977 年10 月,國家開始恢復高考。當了一年半赤腳醫生的劉國恩,得知此消息后,立刻報名并參加了首次高考。當時他的想法很樸素,就是一定要讀大學,一定要去學醫,學成后一定要回到家鄉,要為家鄉貧寒的父老鄉親治病,不再讓貧苦患者遭受白眼。所以在填報志愿時,他在重點大學、非重點大學甚至中專等欄目里,從上到下填寫的都是醫學。
他的高考成績的確也是名列前茅的。雖然當時的備考條件艱苦到今天的孩子無法想象的程度。但是聰慧刻苦的他,通過努力,在全縣第一批高考名單中名列榜首。“劉國恩”這個鄉下孩子的名字,一下子通過高音廣播傳遍了全縣。
然而,命運卻在他的夢想馬上就要成為現實的時候,跟他開了個大大的玩笑。可以說,是這個偶然因素徹底改變了劉國恩一生的軌跡。
高考體檢之后,他和大家一樣,在家中焦急地等待通知。但是從第一批到最后一批,屬于他的錄取通知書始終沒有等來。絕望中,一通信息傳來,告知他的政審材料缺失。在那樣一個唯成分論的時代里,沒有政審鑒定就意味著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未來。
當時的他深陷痛苦之中,欲哭無淚,欲求無門。連縣機關的人也都說,這樣對待一個鄉下的小孩太不公平了。
天無絕人之路。在臨近大學開學的前一個月,他意外地接到了西南民族大學數學系本科的錄取通知書。那時,身為民族院校,西南民族大學準許特招成績優秀但其他方面不太“好”的學生,定向培養成為少數民族地區的師資力量。接到通知書后,劉國恩抓住了這次轉機,背著鋪蓋到位于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學數學系報到了。

▲劉國恩與美國南加州大學同事
也許是因禍得福,西南民族大學77級數學系,云集了一批政審或其他條件有問題但成績優異的尖子學生。在與他們的砥礪學習中,在老師的悉心傳授下,劉國恩在學業上進步神速。其時,改革開放的大潮正洶涌而來,經濟的發展開始成為主旋律。在這種大背景下,劉國恩又有了新的想法,要“時尚”一些,跟上時代的發展,學好經濟學,這樣將來才可能大展拳腳。他決定,要去讀經濟學的研究生。
然而,西南民族大學并沒有開設經濟學專業,劉國恩就到政史系去旁聽政治經濟學的有關課程,并買了一些書來自學。他報考了西南地區最好的經濟院校——西南財經大學的計量經濟與統計專業,既向經濟靠攏,又沒有完全拋棄數學。考試結束后,劉國恩沒報太大希望,畢竟是臨時抱佛腳,又沒有專業老師指導,就全當是碰碰運氣了。大四那一年,劉國恩像其他同學一樣,到鎮上的中學去實習。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可能就在這里當一輩子老師了。
意外還是出現了,劉國恩考上了!無論他本人,還是西南民族大學,或者是西南財大,都對這個結果大吃一驚。就這樣,劉國恩開始與經濟學結緣。
“美國的成功經驗完全可以借鑒”
仔細分析劉國恩的醫改思路,不難看出,其在很多方面都帶有濃重的美國印跡。這并不奇怪。
從西南財大研究生畢業后,劉國恩留校任教。一年多之后,命運再次向他垂青。當時,國家公費留學計劃要在各高校青年教師中選拔優秀的經濟學人才去國外留學,但是要到復旦大學去參加包括西方經濟學的綜合考試,合格者才能得到出國留學的機會。劉國恩獲得了學校的推薦,前提是他只讀過政治經濟學,從未系統學習過西方經濟學。初生牛犢不怕虎的他,利用從成都到上海坐火車的兩天時間,硬是把剛剛借到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鄒至莊老先生撰寫的英文經濟學教材的影印本囫圇吞棗地讀了一遍,然后便倉促上陣了。
又一次的不抱希望,又一次的驚喜降臨。劉國恩接到了出國留學的通知。喜出望外的同時,另一個問題出現了,出國究竟學什么?少年時的夢想再次浮現,劉國恩當即寫信給自己惟一閱讀過的美國計量經濟學教科書作者Damodar Gujaradti 教授,向他詢問有沒有把醫學和經濟學結合在一起的系科。Gujaradti教授立即向他推薦了在紐約城市大學研究院執教的衛生經濟學大師Michael Grossman 教授,于是劉國恩毫不猶豫地填報了紐約城市大學研究院,并于1986年始了自己在美國的求學之旅。
漂洋過海來到異國他鄉,劉國恩最初的日子并不好過,一切都顯得那么陌生。生活上不習慣也就罷了,最要命的是語言溝通上的障礙。聽不懂老師講的課,筆記也記不全,劉國恩只好買來一臺錄音機在課上錄音,課后再翻來覆去地聽。
辦法總比困難多,在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之后,劉國恩不再感到無所適從了。1991 年,他在紐約城市大學順利取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但他并沒有滿足自己學業上的進步,而在考慮如何將所學的西方衛生經濟學理論用于中國的醫療衛生實踐領域,這是他的夢想。他了解到哈佛大學蕭慶倫教授是國際上研究中國衛生經濟的學術權威,于是他再次“投信問路”。這位著名的華裔經濟學家被這位優秀青年學者的一顆炙熱的中國心所打動,于是全額資助劉國恩在哈佛大學的博士后研究,并讓劉國恩在他領導的研究項目中承擔計量經濟學分析的重任。
1994 年初,由于嶄露頭角的研究潛力,劉國恩受聘于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擔任助理教授,開始了第一份在美國大學的教職。從這時開始,劉國恩的學術生涯發展迅速,成果顯著,最終受到了美國公立大學中資格最老的北卡羅來納大學的青睞,2000 年他接受北卡的邀請并擔任終身教授之職。
從1986 年來到美國到2006 年辭掉北卡大學終身教授的職務回到中國,劉國恩在美國生活了20 年。這20 年的浸淫,毫無疑問對劉國恩醫改思路的逐步形成與發展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種位于大洋彼岸的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醫改模式即便完美無瑕,移植到中國來必然也會走樣,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公民素質、不同的社會環境都注定了照搬照抄的荒謬可笑。更何況,美國的醫療體制本身也正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

▲劉國恩與薩克斯教授(“休克療法”之父)

▲劉國恩在人民大會堂主持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論壇
于是,很多人指責劉國恩的醫改思路是“照抄美國”。劉國恩的回應是:“美國道路當然不是我們學習的模型,誰也不是,中國只能走自己的路。但一些國家醫改中的成功經驗,美國的可以借鑒,德國的可以學習,印度的也可以參考。”
“我很慶幸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人的一生,其實就是不斷選擇的過程。不同的選擇,指向不同的風景,可能陽光燦爛、風光旖旎,也可能愁云慘霧、蕭索黯淡。
2006 年2 月,劉國恩做出了一次重要的選擇:棄北卡而選光華。當時,很多人不理解他這種“瘋狂”的舉動,北卡的終身教授意味著一輩子無憂無慮、穩定閑適的生活,不知有多少人夢寐以求而不得,他卻棄而去之,回到中國做大學教授。
也許只有劉國恩自己才明白這次選擇的意義。這實在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劉國恩甚至考慮了三年才最終做出了這樣的一個選擇。
2000 年之前,中國的經濟學研究領域沒有衛生經濟研究之說,衛生健康研究只在公共衛生學院、醫學院或者藥學院這些只和醫藥相關的大學里才有。但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衛生領域的現狀和發展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國際經濟學界對此領域的研究也越來越重視,而這個領域本身所面對的各種機遇和挑戰也越來越明顯。
面對這種情況,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果斷決定,率先開設衛生經濟與管理學系,填補國內在這一領域的空白,盡快與世界接軌。
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去哪里找一個真正懂行的好車頭呢?放眼國內,實在找不出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只能把目光轉向國外,并進一步瞄準了衛生經濟學研究起步較早的美國。最后,縮小“包圍圈”,并最終鎖定了北卡大學的劉國恩。
找到合適的人選,這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怎么請到手,才是關鍵。光華管理學院拿出了足夠的誠意,時任副院長的張維迎親自赴美,與劉國恩徹夜長談。在北大的歷史上,一個領導飛到美國去請一位老師,這種情況是極為罕見的。
這下輪到劉國恩頭疼了。該不該去呢?自己已經在美國有了非常穩定的工作和生活,要放棄這一切去新挑起一副擔子,值不值得呢?
在長達三年的時間里,劉國恩半年在北卡,半年在光華。他還在考察與衡量。面對記者,劉國恩并沒有虛偽地大談特談“為了祖國做貢獻”。他毫不掩飾自己的“私心”,“我得考慮有沒有發揮的空間,有沒有發展的平臺,能不能適應等一系列的問題”。實際上,他找到了合適的平臺,能把自身潛力盡力挖掘出來,既成就了自己,又為國家做了貢獻。
經過考察分析,劉國恩認為中國的醫藥經濟學研究剛剛起步,發展空間很大,而醫療衛生體制還很不成熟健全,正好大有可為。如果成熟了健全了,反倒掀不起什么浪花。“醫藥經濟學就是以人們的健康為目標,在給定醫療資源的前提下,作出最優化的選擇,取得最大化效益的學問。在當下的中國,這樣的教研很有現實意義。”最終,劉國恩下定決心,辭去了北卡大學的終身教授職務,成為光華的全職教授。
“在美國寧靜、穩定,一切井然有序。而中國像極了一個大工地,整天都在緊張忙碌著”,劉國恩早已適應并習慣了這種充滿激情與活力的感覺。
現在回過頭來看三年前的那個決定,劉國恩慶幸自己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我趕上了中國新醫改的進程,并能親身參與進去,有機會憑借自己的知識積累去影響新醫改進程。我的思想、建議或觀點,不管對與錯,總有很多人在傾聽,這些都令我感到鼓舞和振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