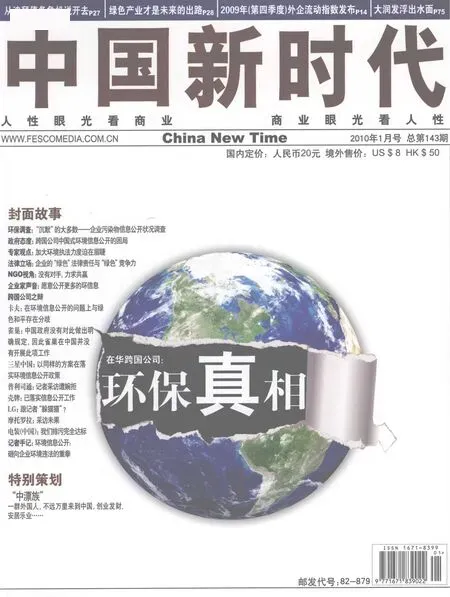企業的法律責任與“綠色”競爭力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糾紛調解部部長侯佳儒:
傳統觀念認為,企業從事任何環境保護活動,都必然以其經濟上的損失、利益損害為代價,因為企業為治理污染和實現清潔,就要增加自身的私人成本,從而導致其產品價格的提高和產業競爭力的下降,因此解決環境問題對于企業是一種純粹的負擔,因此企業視環境保護為“累贅的負擔”、“巨額的破費”,視政府及環保團體為“敵人”,視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環境管制與環境保護活動為“勝負分明的游戲”。這種觀念促使企業對任何環保活動、環境立法都產生抵制和對抗,并因此提高了環境執法的成本。但隨著當代社會經濟運行模式逐漸發生重大轉變,環境保護不但成為現代社會主流價值,它也正對現代商業游戲規則發生重大影響。一個越來越將成為現實的趨勢是,企業主動承擔環境保護的法律責任,不僅是作為企業公民守法的體現,也有利于提高企業自身的競爭力。
在國外一些國家,企業為回應來自包括競爭者、消費者、政策制定者等在內的各種壓力,努力探索各種富于創新的解決環境問題的辦法;而國外環境立法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通過更嚴格的環保標準來促使企業更有效的利用資源,從而加強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美國的波特和林德教授都毫不諱言:“與其他國家的法規保持同步或是略有超前,比照國外的無需執行同一法規標準的競爭者,將可能的競爭劣勢最小化是非常重要的。……當美國的標準領導著世界的發展潮流時,美國的企業就有可能獲得先行優勢。不過美國的標準比國外的競爭者過于超前或者差距過大,相關的產業也會步入歧途。”可以看出,關于設置怎樣嚴格的環境標準,發達國家立法有著精明準確的計算,這背后掩蓋的是通過環境立法把環境問題作為爭取本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優勢手段的企圖。西方一些學者提出“自然資本主義”的概念,認為企業承擔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是當代社會走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同時又指出,企業在從事自然保護方面存在巨大商機,因此企業經營者應迎頭趕上,否則將在新一輪的經濟角逐中被淘汰。
究其原因,在于將企業環境立法納入可持續發展戰略,標志著企業經營已確立了新的商業游戲規則,這是企業無法左右的事實,物競天擇,惟適者生存。因此有遠見的企業應主動出擊,在新的商業游戲規則下取得主動。對此,西方社會已形成普遍共識,這從西方國家環境立法的三個明顯特征就可看出:
首先,從環境立法的嚴峻程度上看,西方環境立法總是適度保持對其他國家環境立法的同步或者超前,其動機與其說出自保護環境,不如說是旨在保持相對于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優勢;其次,從法規的制定和有效實施方面看,西方國家環境立法,企業及相關產業自始至終全程主動介入;第三,從法律形成機制看,尤其要注意許多新的環境標準的提出,并非出自國家的強制實施,而是通過企業自律組織、企業主動認證環境標準得以實現——這表明,西方社會多數企業明確認識到環保與盈利并非對立,在新的經濟模式下,反而是必須予以把握的商機。因此企業從事環保,不但不再是嚴刑峻法下的被迫行為,而是企業要通過內部嚴格 行 業自律來加以保障的自覺行為;企業接受 ISO9000、QS9000/TS16949、TL9000、AS9000、HACCP、ISO14000、OHSAS18000、SA8000等體系認證,目的就是為了產品能在國內外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讓產品領先國際市場,擴大企業發展空間。

可以看出,究竟環境保護立法如何影響企業的經濟績效,這個問題要看我們制定何種環保法規,要看企業經營遵守何種游戲規則。壞的法規將損害競爭力;好的法規則有助于提高企業競爭力。那種在國際經濟競爭中以犧牲環境保護來獲取比較優勢的國家發展戰略,已經面臨越來越多的困境。相對于發達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環境保護立法相對寬松,一些發達國家的巨型企業為規避本國環境保護的嚴刑峻法,就以發展中國家國際環境立法相對寬松為契機,把落后、污染、能耗、淘汰的產業部門,利用目前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由發展中國家承擔巨額的環境保護治理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而另一方面,由于發展中國家環境立法落后,因此國際貿易領域的環保條款常常構成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現實障礙,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可見,隨著環境保護日益成為影響國際、國內商業競爭的重要因素,企業經營如果不符合環境立法要求,不僅要承擔高額的環境違法成本,更可能在商業競爭中被踢出局。在這方面中國企業已深受其害,有諸多慘痛教訓,據不完全估算,中國每年至少有70多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綠色壁壘”的影響,而且還有逐步擴大的趨勢。
事實上,企業應當承擔環境保護的法律責任已是當代環境立法的趨勢,并且在許多重要的國際性條約、文件中都有體現。如1987年《布倫特蘭報告》中,提出要貫徹可持續發展有七項具體要求:“保證公民有效地參與決策的政治體系;在自力更生和持久的基礎上能夠產生剩余物資和技術知識的經濟體系;為不和諧發展的緊張局面提供解決方法的社會體系;尊重保護發展的生態基礎的義務的生產體系;不斷尋求新的解決方法的技術體系;促進可持續性方式的貿易和金融的國際體系;具有自身調整能力的靈活的管理體系。”后六項要求細細品來,莫不與企業的環保活動息息相關,而且這些要求日益被國際性條約、宣言所重申、所具體化,并漸漸演化為當代越來越多國家的立法政策。因此,這也是當今世界各國企業環境立法不得不面對的重要現實。
中國環境法律、法規中對企業保護環境的法律義務做出了許多規定,但總體看來,約束仍然比較寬松,立法者的一個擔心在于,過于嚴格的環境保護立法可能會削弱我國在國際上的經濟競爭力。的確,國際貿易領域的商業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制度的競爭。但問題在于,嚴格環境保護立法究竟會削弱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還是會增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很難有個簡單的結論。
目前世界貿易格局下,一國環境保護立法對企業而言是把“雙刃劍”,一個國家好的企業環境立法宛如“利器在手”,它有利于擴大本國的國際貿易,有利于抑制巨型跨國企業的投機行為,有利于保護本國環境;但壞的企業環境立法卻可能鼓勵跨國企業轉移落后技術和淘汰的產業部門,招致本國環境污染并“授人以柄”,削弱本國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甚至使本國企業無法進入國際市場。而我們今天選擇什么樣的環保立法,這個問題等同于我們選擇“利器在手”還是“授人以柄”的未來。通過降低環保標準來對本國企業污染浪費行為予以規制,這種縱容和姑息只會削弱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是現代企業不能承受的“呵護”和“溺愛”;而僅僅視環境問題的解決為企業的社會義務,而忽視環境問題可能構成企業生存、發展的嚴峻挑戰,這種環境立法對企業無異于“慢性扼殺”。僅僅視環境問題的解決為企業的社會義務,而忽視環境問題可能構成企業生存、發展的嚴峻挑戰,這種環境立法對企業無異于“慢性扼殺”
中國的環境立法應當加強對企業環境保護法律責任的要求。企業承擔環境法律責任,就是要要打破片面的經濟績效決定論的觀點,要打破過去掠奪式的生產經營模式,要促使企業發展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企業不可因追求自身眼前的經濟利益而忽視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違反法律污染環境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在文明和法制日益進步的當代社會,違法的企業、污染環境損人利已的企業也必然受到社會的譴責與排斥,其經濟效益也不會持久。加強企業的環境保護責任,還要強調企業自覺地保護環境。保護環境是一種法律責任,更應該成為企業的自覺行動。完全依賴于法律監督、管理、制裁的環境保護是低效率的,而自覺地守法、自覺地保護環境才是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坦途。當今歐洲環境保護的許多法律規范正是起源于自覺保護環境的企業協議和行業規范,如著名的ISO14000環境管理認證,以及一些歐洲國家在電子廢物污染防治的規范,最早都是企業和行業的自覺行動。這些環境保護的先進企業在為社會環境保護做出積極貢獻的同時,也提高了自身良好的社會形象,進而提高了自身的市場業績和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