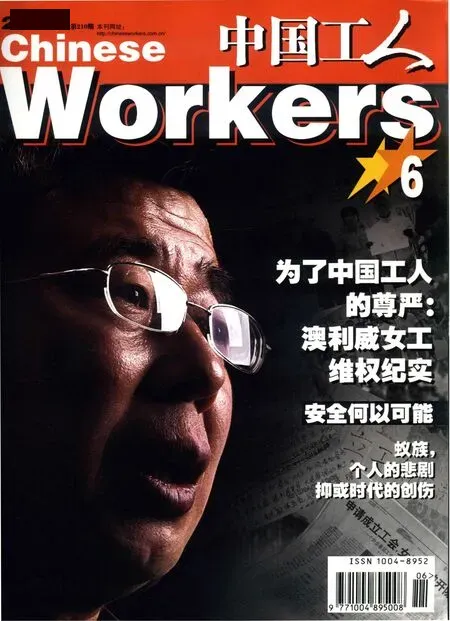日本收入分配雜談
中國政法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 劉 星
日本收入分配雜談
中國政法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 劉 星
在市場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特別是重大變革的時期,掌握各種資源的階層或個人在收入上總會走在時代的前列。收入與分配不僅可以看出社會消費的特點,也可以了解社會總體的發(fā)展方向。收入既反映了國民經(jīng)濟的強弱,也反映了國民物質(zhì)生活的水準(zhǔn),而對收入如何進行分配則可以反映更多的問題,諸如收入與家計、社會消費、貧富差距的關(guān)系,甚至社會結(jié)構(gòu)的變化。
與我國只有一水之隔,在西方人眼里又同屬“東方”的日本的收入分配與我國明顯不同。盡管近幾年隨著日本經(jīng)濟的持續(xù)低迷和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盛行,收入和分配的差距呈擴大趨勢,但相對而言,日本的收入分配仍具有濃厚的“平均主義”色彩,反映在社會結(jié)構(gòu)和社會心理上則是大量的中產(chǎn)階層的出現(xiàn)以及全民的中產(chǎn)階層意識。
日本是世界國民生產(chǎn)總值最高的國家之一,根據(j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購買力平價(PPP)統(tǒng)計,2007年日本國民生產(chǎn)總值約4.35萬億美元,人均約3.4萬美元。其國民的整體收入自然也在發(fā)達之列。可能是為了鼓勵納稅,日本國稅廳從1983年到2005年每年都會發(fā)布一個高納稅者排名表(1983年以前是高收入排名,2005年以后因保護個人隱私廢止),由此可以推出收入的多少。
2005年納稅最多的是一家投資咨詢公司的高管,2004年一共交了近37億日元(約合3700萬美元)的稅,由此推算出其年收入超過了100億日元。當(dāng)年納稅前10人中2人是公司高管,8人是公司最高負(fù)責(zé)人。前100人中33人與轉(zhuǎn)讓股權(quán)有關(guān),而通過不動產(chǎn)交易獲利納稅的只有5人。可見,“炒股”、“高管”這些“高收入職業(yè)”在全球化浪潮的波及下也在日本有所斬獲。由于日本持續(xù)的經(jīng)濟低迷和不動產(chǎn)泡沫的破裂,不動產(chǎn)行業(yè)沒能再成為高收入的主要來源。
當(dāng)然,對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如此高收入者似乎脫離了實際,更接近“現(xiàn)實生活”、至少“可望”的不是個人,而可能是某個階層或職業(yè)。哪些階層屬于高收入階層呢?根據(jù)統(tǒng)計資料,在日本平均收入最高的職業(yè)是配音演員,排在第二位的是暴力團(黑社會),第三位是律師,隨后是職業(yè)運動員、民航飛行員等。大體上平均年收入在1200萬日元(約12萬美元)以上。可這些也都是“非現(xiàn)實性的職業(yè)”,專業(yè)性要求很高,能夠從事這些職業(yè)的人也是鳳毛麟角,盡管“可望”,但似乎也屬于“不可及”的范疇。
高收入職業(yè)再往下推移,還包括消費生活助言師、房地產(chǎn)鑒定士、稅理士、私人偵探等,他們都在800萬日元(8萬美元)左右。就平均工資而言,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數(shù)額了。這些職業(yè)相對更多了些平民化色彩,但也與高利潤行業(yè)和新興行業(y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比如房地產(chǎn)鑒定士自然與房地產(chǎn)有關(guān),稅理士也就是幫助進行諸如報稅等的工作,而消費生活助言師則是比較時髦的職業(yè),他(她)們向人們提出如何更合理地進行“現(xiàn)代生活”的建議。相信隨著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fā)展,在高收入層中也會出現(xiàn)這些名目繁多的服務(wù)業(yè)專業(yè)人士。
那么,公務(wù)員的收入如何呢?日本公務(wù)員是指各級政府系統(tǒng)的公職人員以及國會、法院、國立學(xué)校與醫(yī)院、國家所屬部門的所有人員,共約450萬人左右。盡管日本的公務(wù)員系統(tǒng)在日本國內(nèi)屢遭惡評,但實際上無論在數(shù)量上還是與GDP比例關(guān)系上,即使在發(fā)達國家也處于高質(zhì)高效的水平(根據(jù)日本的統(tǒng)計,每萬人擁有公務(wù)員數(shù),日本在發(fā)達國家中是最低的,公務(wù)員與GDP之比也只遜于美國)。
日本公務(wù)員(國家和地方)的工資金額是國家人事院參照同期全國平均工資的標(biāo)準(zhǔn)設(shè)定,以體現(xiàn)“為人民服務(wù)”的宗旨。公務(wù)員的工資應(yīng)滿足兩方面的要求,一是能夠吸引相對高水準(zhǔn)的人才從事服務(wù)于國民的公務(wù)員工作,二是不能讓公務(wù)員工資明顯高于社會的平均工資而導(dǎo)致給國民以公務(wù)員高高在上的印象。前者要求公務(wù)員收入走高,后者則要求收入“含蓄”。總體上,由于公務(wù)員的工資不能像企業(yè)那樣隨著收益進行浮動,特別是上調(diào),所以公務(wù)員的工資會相對高一些。在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時期,公務(wù)員的工資增長速度往往趕不上企業(yè)員工工資的增長速度。在日本經(jīng)濟的鼎盛時期,甚至出現(xiàn)過有公務(wù)員的收入增長遠(yuǎn)遠(yuǎn)趕不上民間收入的增長速度,以致到了年底,政府不得不多支付公務(wù)員一個月的工資以穩(wěn)定軍心的現(xiàn)象。

而在經(jīng)濟蕭條時期,公務(wù)員的收入也不會下降得過快,鐵飯碗也就變成了金飯碗。2007年度公務(wù)員的平均收入與民間相比,國家公務(wù)員的平均收入是662萬日元,比前一年上升0.55%,地方公務(wù)員為729萬日元,上升0.04%。上市企業(yè)平均收入為589萬日元,上升了0.87%,民間企業(yè)平均為435萬日元,減少了0.46%。也就是說,公務(wù)員的平均工資上升,而民間反而在下降,因此最近幾年在日本國內(nèi),對公務(wù)員不與民同苦的不滿時有流露。當(dāng)然,公務(wù)員特別是一般的公務(wù)員也有自己的苦衷,比如加班多且少有加班費,節(jié)假日少,較為嚴(yán)格的財務(wù)制度也使得他們幾乎沒有多少灰色收入,更談不上“被腐敗”的機會了。
1999年的“年家計調(diào)查報告”(總理府)將日本家庭的實際收入分為五個等級,第一等級(收入最低的20%)實際月收入為32.6萬日元,消費22.9萬日元。第五等級(收入最高的20%)分別為93.9萬日元與51.1萬日元。實際收入差為61萬日元,消費支出差為28萬日元。可以看出,日本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最高收入層和最低收入層之間的收入差只有2.88倍。在分配上,最高收入層與最低收入層之間更是只差2.25倍,還沒有收入差高。另一數(shù)據(jù)稱日本員工和老總的收入平均相差10倍,而美國平均是30倍。近幾年全球汽車產(chǎn)業(yè)獨領(lǐng)風(fēng)騷的豐田公司3名最高決策者的收入只有美國福特公司最高決策層的1/10。這些都說明日本在收入分配上濃厚的平均主義色彩。
2007年日本總務(wù)省的調(diào)查勾畫了日本家庭的典型構(gòu)圖。我們暫且把這個家庭稱為鈴木(日本人口最多的姓)家吧。鈴木家一家三口人,鈴木先生47歲,是公司職員,鈴木太太則沒有正式工作(日語里把家庭主婦稱為專業(yè)主婦),只打一些零工補貼家計,他們有一個孩子。在2006年,全家月收入52萬日元,其中鈴木先生收入43萬,太太打零工5萬(一周工作10-12個小時),孩子也打點零工,大約掙1萬日元。其他包括存款的利息、炒股以及到期保險金的返金大約3萬日元。鈴木先生的收入是12個月的工資以及一年兩次的一次性獎金(年終獎和夏季獎金)的收入總和,比一般的月工資多10萬日元。當(dāng)然,這52萬收入中需要扣除稅和社會保險等費用,實際到手的收入約44萬日元。
這筆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呢?根據(jù)統(tǒng)計,鈴木家是這樣分配收入的:伙食費6.9萬,家具被褥等家庭消費4.4萬,水電2.2萬,保健醫(yī)療1.1萬,交通通信4.6萬,教育1.9萬,娛樂3.1萬,其他支出7.7萬,合計約32萬。這樣,每個月還有12萬日元的盈余,但生命保險的保險費和房貸等還需出資5萬日元。也就是說,日本平均每個家庭每個月有7萬日元的剩余。除此之外,鈴木家還有存款772萬日元,其中6成是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3成是生命保險,1成是股票等有價證券。
日本屬于發(fā)達國家中的發(fā)達國家,整體收入高也在情理之中。從上述一系列的數(shù)字可以看出,日本用于衣食住行的費用仍然是較低的,即使加上社會保險和住房還貸等,仍然能有相當(dāng)一部分結(jié)余。也就是說,除了“硬性支出”外,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不少。同時,如果按照平均收入和平均支出分析,衣食住行這些最基本的支出只占家庭總收入的不到一半,這說明高收入和生活必需所占比例的相對低下,使得人們對收入的分配多樣化。
收入的增加、分配和社會消費的變化是緊密相關(guān)的。無疑,收入的增加必然帶動分配的增加和變化。無需多言,可供分配的收入增加了,人們自然要去考慮如何消費,如何在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費之外尋找新的消費點;而反過來,社會消費的趨勢又帶動了人們對收入增加以及進行更進一步分配的意愿。
另外也可看出,總體而言日本國民始終保持著比較高的儲蓄率,少有“超前消費”和“信貸消費”的傾向。日本的高儲蓄率曾被認(rèn)為是推動日本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但如此,較高水平的儲蓄率也使得普通日本人對經(jīng)濟不景氣的反應(yīng)似乎總有些“遲鈍”。這次世界金融危機美國很多家庭失去了工作和房子,開始認(rèn)識到儲蓄對生活的價值,而對于大多數(shù)日本家庭的影響,也僅僅限于是否要更謹(jǐn)慎地進行消費。“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儲蓄成為確保家計穩(wěn)定的重要保證。
其實上述數(shù)字更反映了日本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日本式的平均主義以及由此帶來的普遍富裕和中產(chǎn)階層的穩(wěn)定與中產(chǎn)階層意識。在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日本往往被樹為平均主義的典型,而平均主義帶來的則是更多的日本國民成為中產(chǎn)階層。在日本經(jīng)濟最受世人矚目的80年代,對日本的贊譽之一就是“全民的中產(chǎn)階層化”。
其實戰(zhàn)前日本并非如此,特別是從20世紀(jì)初到20世紀(jì)30年代期間,在工業(yè)化快速發(fā)展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嚴(yán)重貧富分化現(xiàn)象,這也是導(dǎo)致日本最終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日本實行了民主制度改革,工會組織的力量得以加強,勞動階層可以通過合法的途徑提出諸如改善工作環(huán)境、提高工資待遇的訴求。但是,盡管有了合法的訴求途徑,卻不能自動使得勞資關(guān)系變得和諧,特別是在收入等涉及勞資雙方直接利益的問題上。戰(zhàn)后初期,日本的勞資關(guān)系相對比較緊張,勞資糾紛不斷,甚至還發(fā)生過流血沖突。
20世紀(jì)50年代后,企業(yè)一方面受到來自社會、工人乃至政界的壓力,一方面也受益于經(jīng)濟的恢復(fù)和發(fā)展,逐漸認(rèn)識到穩(wěn)定的勞資關(guān)系有利于企業(yè)的持續(xù)性發(fā)展,也有利于緩解社會矛盾。日本經(jīng)營史的研究者認(rèn)為,20世紀(jì)5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企業(yè)家和資產(chǎn)階級盡管處于支配地位,但卻放棄了對企業(yè)利潤的壟斷,而傾向于將財富分配給員工和國民。在企業(yè)和社會的努力下,日本在戰(zhàn)后“創(chuàng)造”了中產(chǎn)階層 ,實際上也就創(chuàng)造了一種平等的概念。
在制度上,企業(yè)從報酬制度到生產(chǎn)經(jīng)營管理均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從而對提高大多數(shù)勞動者的收入起到了積極作用。日本企業(yè)制度中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長期穩(wěn)定的雇傭關(guān)系和行之有效的企業(yè)內(nèi)職工培訓(xùn)體系,這兩點都與收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前者不僅保證了員工不會僅因業(yè)績差等工作能力問題而被解雇,并且還包括了一套有利于收入穩(wěn)定增長的工資制度。
日本企業(yè)的工資體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工齡工資,也就是說參加工作后,隨著工齡的增長,工資也會隨之相應(yīng)提高,這一部分工資與職工的業(yè)績沒有必然關(guān)系。另一部分是職能工資。員工到了一定工齡之后,盡管職稱上不可能得到提升,但是可以根據(jù)技能評定等手段獲得相當(dāng)于某些職稱的工資級別。因此很多日本大企業(yè)出現(xiàn)了獨特的“借進借出”關(guān)系,即員工在二三十歲時的收入少于業(yè)績(一部分業(yè)績收入借給企業(yè)),而四五十歲時收入則多于業(yè)績(從企業(yè)借回業(yè)績收入),而到退休時業(yè)績與收入基本一致。可以說,日本企業(yè)員工的收入制度再配合上長期雇傭制度,體現(xiàn)了日本企業(yè)平均主義的特點。當(dāng)然,企業(yè)也得到了回報,日本員工的敬業(yè)和效率都得到了世界的承認(rèn),也促進了日本企業(yè)的發(fā)展。
同時,日本企業(yè)還在引進美國員工培訓(xùn)制度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了獨具特色的日本員工培訓(xùn)體系。企業(yè)投入了大量人財物力從事職工培訓(xùn),不僅保證了員工可以帶薪受訓(xùn),還刺激了員工對工作的積極性,客觀上使在報酬和培訓(xùn)上的投入通過員工的貢獻得到了回報。毫無疑問,穩(wěn)定的雇傭關(guān)系和有效的企業(yè)內(nèi)職工培訓(xùn)體系是企業(yè)為了擁有一支熟練高效的職工隊伍、穩(wěn)定軍心的重要一環(huán)。客觀上,員工也得到了很大的利益,逐漸形成了雙贏的勞資關(guān)系。
另一個重要轉(zhuǎn)變就是資方對藍領(lǐng)階層支付報酬方式上的變化。戰(zhàn)前,日本企業(yè)中的白領(lǐng)階層和藍領(lǐng)階層各有其工資制度。白領(lǐng)階層的工資實行月薪制,按月拿工資,并且可以根據(jù)工齡享受加薪。而藍領(lǐng)工人則仍實行計時制工資,按照勞動時間領(lǐng)取報酬。另一點區(qū)別則在一次性獎金的分發(fā)制度上,白領(lǐng)能領(lǐng)到的一次性獎金大約是2至4個月的工資,這與現(xiàn)在的慣例基本上一致,而藍領(lǐng)只能領(lǐng)到兩個星期以內(nèi)的獎金。在戰(zhàn)后,隨著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工會的力量壯大,藍領(lǐng)階層的工資制度最終與白領(lǐng)階層相統(tǒng)一,使得這兩個決定收入差距的因素都在根本上得到了改變。
當(dāng)然,即使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證,也不能保證資方就會自動自愿地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從勞動者階層的角度看,如何進行斗爭與妥協(xié)也十分重要。收入增加的一個重要推動要素就是日本工會與企業(yè)所形成的微妙的共存關(guān)系以及每年就漲工資形成的“春斗制度”。戰(zhàn)后經(jīng)過民主改革,日本的工會(主要是大企業(yè)工會)都會進行某些活動并提出某些要求,以顯示工會的價值。比如組織工人進行五一集會,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等。
20世紀(jì)60年代以后,這種集會逐漸成為不成文的制度和勞資間的默契。每到春季來臨,工會就會提出下年度希望漲工資的金額,企業(yè)則根據(jù)經(jīng)營情況給予答復(fù),這種交涉模式被稱為“春斗”。 春斗的成敗與漲工資與否掛鉤,并成為勞資之間達成妥協(xié)的最佳工具。至少可以看出,伴隨著經(jīng)濟的高速增長,戰(zhàn)后日本的收入調(diào)節(jié)向著平衡各方利益的方向發(fā)展,在制度和社會規(guī)則上注重實踐“共同富裕”的理念。
日本國民收入的快速增長開始于20世紀(jì)60年代中后期。60年代初,為了平息因美日安保條約簽訂造成的國民的不滿和國內(nèi)政治上的不穩(wěn),池田內(nèi)閣推出了“國民所得倍增計劃”(國民總產(chǎn)值在10年內(nèi)翻一番),試圖將國民的注意力從政治引向經(jīng)濟。至少從結(jié)果上看,這一經(jīng)濟發(fā)展計劃的確為日本國民收入的增長奠定了物質(zhì)基礎(chǔ)。據(jù)統(tǒng)計,進入6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工資的上升率都以10%以上(10%~15%)的速度遞增。從1960年到1973年,日本城市消費水平提高了83%,農(nóng)村提高了150%,消費結(jié)構(gòu)的重點由飲食服裝等生活必需品的充實轉(zhuǎn)向住宅、汽車、教育以及娛樂。
平等主義式的收入分配政策造成的一個直接結(jié)果就是大量中產(chǎn)階層,或者說中產(chǎn)階層意識的形成。工資收入上升幅度高于物價上漲幅度,國民實際收入不斷上升,消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在消費上,大眾消費社會得到了擴大和發(fā)展,而帶來的一個社會心理的變化就是社會階層逐漸消失,國民開始普遍持有“中流意識”。

1958年的國民生活輿論調(diào)查顯示,一半的國民覺得自己屬于“中層里面的下層”和“下層”,而到了1973年,61%的人覺得自己是“中層里面的中層”,被稱為“一億總中流化平等化”模式。而在20世紀(jì)80年代的經(jīng)濟鼎盛時期,更是有近90%的人表示自己擁有中產(chǎn)意識,使得日本出現(xiàn)了“全民中產(chǎn)化”的社會現(xiàn)象。沒有明顯的貧富差距,再加上日本國民比較內(nèi)斂的國民性格,在分配和消費上也就出現(xiàn)了所謂的“均質(zhì)化”現(xiàn)象,除了少數(shù)十分富裕的階層外,很多日本國民的生活和消費都處在相對接近的層次上。在美國,不同收入階層的人在消費上也會分化成不同的階層,每個階層有自己固定的消費場所,而在日本并不明顯,至少在大多數(shù)日本國民的意識中,日本社會實現(xiàn)了“平等”。
中產(chǎn)階層的收入與分配往往是促進社會消費的最為可靠的力量,因為盡管中產(chǎn)階層不能進行“高消費”,但卻可以進行持續(xù)穩(wěn)定的大量消費。根據(jù)日本學(xué)者的一種計算方式,在購買同一類型的商品時,高收入階層支出10萬日元,中產(chǎn)階層支出7萬日元,低收入階層支出3萬日元。如果按100萬人的市場計算,1958年,高收入階層占4%,中產(chǎn)階層占41%,低收入階層占55%,那么合計消費就是10萬×4%+7萬×41%+3萬×55%萬=492億日元,而如果按照1973年中產(chǎn)階層化之后,同樣的算式就是10×8%+7×64%+3×29%=615億日元。可見大量的中產(chǎn)階層要比少數(shù)高收入階層的購買能力更強。
全民中產(chǎn)階層化的意識也影響到了消費。如果大多數(shù)老百姓認(rèn)為自己成為了或可以成為中產(chǎn)階層的一分子,他們就會進行可以被確認(rèn)為中產(chǎn)階層的消費,從而也影響著日本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與發(fā)展。在全民中產(chǎn)階層化的潮流中,家電、汽車、紡織產(chǎn)業(yè)等日本的支柱產(chǎn)業(yè)也都開始指向適合中產(chǎn)階層需要的產(chǎn)品生產(chǎn)。價廉物美的產(chǎn)品是中產(chǎn)階層的首選,而日本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正適合了這種需求,因此這些支柱產(chǎn)業(yè)的產(chǎn)品少有高端更無低端。同時,為了適應(yīng)全民中產(chǎn)階層化的趨勢,與面向少數(shù)高收入階層進行高利潤銷售的歐洲銷售模式不同,日本的銷售模式將重心置于向不斷擴大的新中產(chǎn)階層大量銷售價廉物美的產(chǎn)品。
可以說,日本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與中產(chǎn)階層的收入分配實質(zhì)上形成了相輔相成的互動關(guān)系,消費指引分配,收入促進消費,平等主義式的收入分配模式影響著整個經(jīng)濟生產(chǎn)和社會消費結(jié)構(gòu)的形成。日本社會發(fā)展的過程再次證明,如果拋開對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的爭論,擁有穩(wěn)定的較為充分的收入與分配能力的中產(chǎn)階層的出現(xiàn)和壯大是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重要指數(shù)。
與此相對照,我國的中產(chǎn)階層大約上升到了22%,盡管相對發(fā)達國家還比較低,但應(yīng)該說已是一個不小的進步。可是,由于大量的收入被用于還貸、子女教育,再加上沒有可靠的醫(yī)療保險制度,中產(chǎn)階層的社會承受能力還比較脆弱。如果中產(chǎn)階層尚且如此,對于大多數(shù)的中低收入階層這種無形和有形的壓力就可想而知了。對于社會來講,收入的增長固然是一個必要的因素,但是通過收入增進平等意識和穩(wěn)定的心理,從而進行合理和較為自由的分配,進而促成多樣化的消費,對于社會的穩(wěn)定和諧更加重要,因為即使總體收入不斷上升,如果沒有穩(wěn)定有序的制度作為保證,還是無法促進合理多樣與可持續(xù)性的分配與消費。
這幾年日本的收入差距也出現(xiàn)了擴大的傾向。在自由主義理論支配的經(jīng)濟全球化沖擊下,更多的競爭機制被導(dǎo)入了日本經(jīng)濟和日本企業(yè)。在失業(yè)者增加的同時,一部分企業(yè)的報酬制度也轉(zhuǎn)向注重業(yè)績的能力主義,拉大了個人收入的差距,同業(yè)企業(yè)之間的員工收入也出現(xiàn)了差距拉大現(xiàn)象,終身雇用、年功序列的工資體系以及企業(yè)內(nèi)的保障制度等日本傳統(tǒng)的雇傭體系成本漸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另外,日本國民平等的社會心理也發(fā)生了變化。在經(jīng)濟構(gòu)造的變化下,更多的人開始接受在收入上的“機會平等主義”的價值觀,就是說,只要大家在起跑線上是平等的,那么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在“弱肉強食”的競爭中,其結(jié)果各不相同也是理所當(dāng)然的。這與日本傳統(tǒng)上對平等的認(rèn)識大不相同,在一些新興企業(yè)和行業(yè)頗為流行并開始更為猛烈地向傳統(tǒng)企業(yè)行業(yè)滲透。
即使如此,對收入分配的傳統(tǒng)意識在日本仍然十分強勁。在如何對待臨時工雇用的問題上似乎就可以看出對收入平等的執(zhí)著。本世紀(jì)初,日本政府對企業(yè)采取了一系列“規(guī)制緩和”的措施,其中一項就是允許大型制造業(yè)可以更自由地雇用臨時工。在這一松綁政策下,很多大企業(yè)雇用了臨時工或鐘點工,這樣可以節(jié)省諸如培訓(xùn)費、勞保費、獎金等很大一筆開支。世界金融危機后,企業(yè)首先從這些臨時工開始裁員,于是媒體也開始了報道,批評臨時雇用制度無法保證臨時員工的收入,侵犯了他們的勞動權(quán)益。
在各個媒體競相報道,厚生勞動省(類似于我國的人保部)進行了調(diào)查,初步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只有數(shù)千臨時工已被或?qū)⒈唤夤汀<词谷绱耍降葘ΥR時工的輿論導(dǎo)向已經(jīng)形成,并成為政黨斗爭的政治工具。去年執(zhí)政的民主黨始終表示要采取保障勞動者權(quán)益的措施,其中就包括改革臨時雇用制度,鼓勵和支持企業(yè)雇用正式工等。去年年底,厚生勞動省決定在近期廢止大型制造業(yè)可以雇用臨時工的政策,這些無疑都會提高民意對政府的支持率。由此給我們的啟示是,難道不應(yīng)該尋求一種讓絕大多數(shù)人滿足或有滿足感和平等感,為此需要讓某些階層放棄一部分權(quán)益的更為合理、和諧的收入分配制度嗎?


日本社會發(fā)展的過程再次證明,如果拋開對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制度的爭論,擁有穩(wěn)定收入與分配能力的中產(chǎn)階層的出現(xiàn)和壯大是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重要指數(shù)。
欄目主持:王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