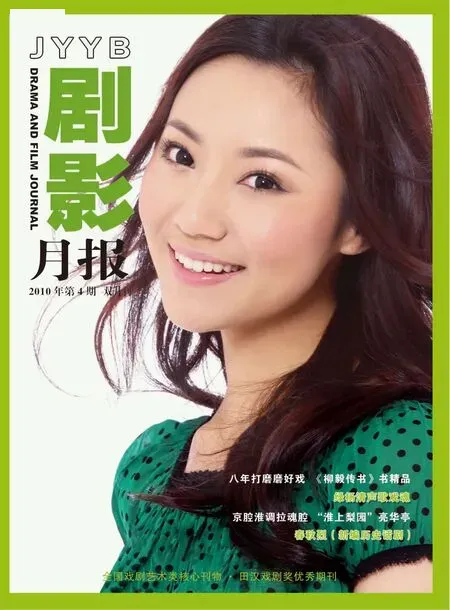音樂劇表演的舞臺行動規律——淺談音樂劇《吉屋出租》中的人物
■魏瀟
引言
所謂的音樂劇表演其實和戲劇表演沒有什么不同,因為音樂劇本身就是戲劇表演的一種。戲劇表演要求演員以接近生活的舞臺語言和舞臺動作,作為表演主要的創作手段,在扮演角色時要真正的從內心到行為完全投入到角色當中,從而感染和征服觀眾。不過音樂劇表演不僅僅運用了接近生活的舞臺語言和舞臺動作,而且還運用了歌唱和舞蹈等的藝術手段來表現生活。然而,創作手段的豐富,藝術形式的多樣,終極點都是為了更好地詮釋劇情,表現人物。演員在舞臺上或歌或舞或言語都要通過人物的戲劇行動來呈現,“動作是一切戲劇表演藝術的基礎,也同樣是音樂劇表演的基礎。”因此,演員必須重視舞臺行動規律在音樂劇表演中的作用。
一.行動是音樂劇表演藝術的基礎
音樂劇的表演是戲劇性的表演,因此行動也是音樂劇表演藝術的基礎。從舞臺藝術上來看,演員在舞臺上扮演角色、展現生活的一切活動,都要通過行動來展現,而行動在戲劇中的基礎作用是早已被古今中外的戲劇大師們認真總結和充分認定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強調:“在舞臺上需要動作,動作、活動——這就是戲劇藝術、演員藝術的基礎。”①盡管戲劇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不同的國度有著不同的風格與流派,創作的觀點也不盡相同,但所有的戲劇作品都沒有離開用行動來表現。對于演員來講,要把劇本中的情節、人物性格表現出來,只能通過舞臺上人物的行動來展現。音樂劇表演也一樣,劇作家,曲、詞作家所結構的故事,只能是通過演員在舞臺上的真聽、真看、真感受和語言、行動來加以刻畫的。以《吉屋出租》為例:這部搖滾音樂劇在1996年1月,紐約市的NewYork Theatre Workshop首演,1996年4月29日之后轉往百老匯,在41街的Nederlander Theatre繼續演出,并在2006年的3月1日成為百老匯史上第七長壽的劇碼。《吉屋出租》同時獲得東尼獎及普立茲獎的肯定。這出音樂劇改編自普契尼的歌劇《波希米亞人》,劇情著重于一群窮困的藝術家和音樂家,即使在愛滋病的陰影下(在“波希米亞人”中是肺結核)仍在紐約的“字母市”掙扎努力生存。
在這部音樂劇中,無論是一開始《Rent》中租房者拒交房租,對房東,對社會的抗議,還是在《LaViBoheme》中暢快釋放思想,自由的舞蹈。每一處精彩的歌舞場面無不是和戲劇情境緊密相連,和戲劇行動密切相關的。而mimi這一角色在《Rent》這部音樂劇中的重要性恰恰正是在于歌,舞及表演的全面整合。不管是劇目剛開始時的斷電之后,她積極的參加到抗議的隊伍當中,還是抗議結束之后她主動和roger的“sayhi”的一系列舞臺行動,都可以直接的反映出mimi的人物性格,她是一個精力旺盛敢愛敢恨的狂野型姑娘。而在《IShouldTellYou》這首歌中的mimi卻給觀眾展現出了她柔情的一面,她大膽并溫柔的向roger表白,而當感情得到回應時的沉醉更加展現出了mimi的柔情。緊接著之后的《LaViBoheme》中mimi又用她狂放的歌舞來展現她對愛情的炙熱以及對“波西米亞”精神的向往。上述例證中可以說明:在舞臺上的任何一種手段都應是帶有一定的行動性,無論體現這種行動的手段是歌唱、舞蹈還是臺詞。如果說行動是演員的基礎,那么行動無疑也是音樂劇表演的基礎。
斯坦尼曾精辟地指出:“演員的藝術是舞臺行動的藝術,在戲劇中,只有通過行動其表現才有力量,令人信服。行動是舞臺表現力的主要手段。只有通過積極的、有目的的、有機的行動,才可以體現人物形象的內心生活,揭示作品的思想構思。演員的技術和創作方法都應當完全從屬于這個任務。”②音樂劇的歌、舞、劇表演不是簡單話劇加唱、話劇加舞,不是歌、舞、劇等手段的簡單拼裝,而是一種在戲劇框架下的有機的整合。這種整合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戲劇沖擊力和表現力,其實就是音樂劇的表演注重將人物的體驗與體現的方式與舞臺行動聯系起來,將表演的內容和形式與舞臺行動聯系起來,從而使得音樂劇的歌唱、舞蹈、語言等手段具有了更新更美的藝術價值。就以 《AnotherDay》中mimi的表演為例,通過演唱與行動的整合從而達到舞臺應有的說服力與感染力,在這首歌的前奏階段mimi就瘋狂的親吻了roger,這個行動進一步表現咪咪對愛情的渴求和敢愛敢恨的心理,在這首歌的進行當中mimi時而依偎在roger背后輕撫roger,時而長跪在舞臺的長桌上,這一切的行動都表現出她對愛情的渴求。如果單單只是唱而沒有行動、表情和肢體語言的話,就難以表現出mimi當時非常迫切,掙扎甚至哀求的心理。也就無法準確的傳達給觀眾人物的內心活動。所以從音樂劇的表演來看,舞臺行動起著巨大的基礎性作用,不能在理論上正確地理解舞臺行動,“整合”就失去意義;不能在實踐中正確的運用舞臺行動,表演就失去魅力。因此,我認為,舞臺行動是音樂劇表演藝術的基礎。
二.舞臺行動在音樂劇中的作用
1.舞臺行動的多樣性
音樂劇表演是一種集歌、舞、劇手段于一體的綜合性的戲劇表演,因此,它的舞臺行動的手段也是綜合性的。不僅具有以注重制造“生活的幻覺”的再現性的表演手段,還有以注重“詩化”的表現性的表演手段。再現性的舞臺行動以生活化的寫實動作和語言為主,表現性的舞臺行動以歌唱和舞蹈為主。再現性的舞臺行動多處于沒有歌、舞呈現的部分,而表現性的舞臺行動則多處于歌、舞呈現的部分。歌、舞方式的舞臺行動在音樂劇中運用得最為普遍。如果說,話劇中的舞臺行動手段主要靠語言和生活化的形體動作體現的話,那么音樂劇中的舞臺行動手段就更加豐富了,它有歌、有舞、有語言,還有接近生活的形體動作。尤其是歌唱和舞蹈在劇中成了戲劇行動的主要表現手段,成了呈現舞臺生活、體現人物行動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與語言動作與生活動作一起,承擔了揭示戲劇矛盾、推動情節發展、體現人物內外部性格與行動的重要任務。
2.舞臺行動的特點
在戲劇中,舞臺行動是戲劇導演、演員以劇本為依托,通過二度創作,有針對性地選擇、提煉、加工、升華,并典型化地在舞臺上展現生活的藝術活動。作為同屬戲劇表演的音樂劇,其舞臺行動與話劇中對舞臺行動的要求并無二致。僅有的差異在于創作、選擇、提煉、加工的過程中,音樂劇的舞臺行動手段更多地依靠歌唱與舞蹈,而不是單純的運用臺詞和生活化的形體動作。
3.形體行動與心理行動
音樂劇表演中,心理行動與外部形體行動的密切關系也體現得非常之明顯。例如:《吉屋出租》中mimi的唱段《OutTonight》、《Lightmycandle》等都屬于外部行動的形式。觀眾一看就明白這段歌曲表達的是什么意思,那段舞蹈傳遞的是什么情感。形體行動是完成某種心理行動的手段,同時,心理行動則決定著形體行動的性質,舞臺上的任何動作都需要帶有目的性,演員的一舉一動都在觀眾注視下,觀眾必然要去了解動作背后的含義,所以沒有毫無目的的動作,盡管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
在音樂劇舞臺上,歌、舞的呈現都有著強烈的心理行動予以支撐,他們反映著人物內心情感和戲劇沖突的具體內容。例如:如果把《吉屋出租》中的那首反映mimi在和roger因為誤會而分開后所演唱的那首《withoutyou》抽離了人物的具體行動,它僅僅是一首簡單的情歌。但是如果將它與行動結合:mimi感到寒冷的蜷縮、和roger深情的擁抱,融合于歌曲,就賦予了人物心理行動的內含,讓人回味無窮。倘若歌唱與舞蹈沒有賦予行動的內含,就如同沒有心理行動支撐的形體行動,空虛而缺少戲劇感染力了。
三.音樂劇舞臺行動的運用
1.舞臺行動與舞臺任務
作為“二度創造”的舞臺演出,音樂劇更直接地表現為一種歌舞化的戲劇呈現。舞臺演出中所展示的人情世故和氣象萬千,無不需要合格的音樂劇演員去傾情演繹,載歌載舞的演員們也必須準確地把握劇中人物的個性,以便完美地呈現角色。
歌舞表演是音樂劇表演舞臺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形式上區別于話劇表演之處。所以,處理歌舞場景和處理臺詞一樣,演員首先需要尋找該段落中人物完成舞臺任務的心理動機,要研究人物的臺詞、唱段、舞蹈動作,從中發現行動,挖掘其內在的含義。以《吉屋出租》中《Lightmycandle》為例,mimi內心對roger有著難以名狀的感情,但礙于自己是女生,又感到對方有著拒人千里之外的冰冷態度,于是借助停電后點蠟燭為由去接近對方,表達自己對對方的愛慕。在排練和表演中必須充分的抓住mimi這個人物內心的掙扎,一方面她是大膽的自信的,而另一方面因為自己的病情和工作她又是自卑的,當她被roger問及工作的事情時她顯出了超出年齡的無奈和現實,但她又時時刻刻暗示著自己的愛慕。只有準確的把握了角色心理的自卑和必須要含蓄示愛的舞臺任務,才能掌握該段舞蹈行動的基調,讓舞蹈呈現出兩人情感碰撞的微妙所在。如果不明確舞臺任務,不了解mimi的心理行動,這段舞蹈就會顯得單一而形式化,甚至讓人不知所謂,失去作為音樂劇舞蹈特有的藝術魅力。
2.舞臺行動與規定情境
任何舞臺行動都受到其舞臺規定情境制約。戲劇情境作為戲劇作品的基礎,由三種因素構成:劇中人物活動的具體時空環境;對人物發生影響的具體的情況──事實、事件;有一定特性的人物關系。如《吉屋出租》發生于圣誕夜,這是人物活動的具體時空環境,而突然的停電是對人物發生影響的具體的情況,還有mimi和身邊朋友都有同樣的疾病是一定特性的人物關系。一般地說,在各種因素中,最重要的、最有活力的因素是人物關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認為,演員創造角色所面對的“規定情境”包含的內容更為廣泛。“這是劇本的情節,劇本的事實、事件和時代,劇情發生的時間和地點、生活環境,我們演員和導演對劇本的理解。”③
四.結語
音樂劇由于歌舞化的高度綜合,使它重視人物形象的外部表現,但是它同樣要求演員必須喚起對人物情感活動的體驗,進行一種內心生活的創造,像角色一樣在舞臺上用自己的身心行動,感受著。只有這樣才有生動的舞臺形象誕生。因此,音樂劇演員必須掌握歌舞化的技術條件,除此之外,還必須具備創造性的舞臺想象力和敏銳的節奏感受力,并且充分的理解和執行有機、生動的舞臺行動,將音樂的旋律化作人物心理活動的律動,才能達到在固定的音樂中進入舞臺情感體驗的境界,從而塑造鮮活的人物形象。
注釋:
①[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二卷,林陵、史敏徒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頁
②格·克里斯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學派演員的培養》,李珍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頁
③格·克里斯蒂:《歌劇導演藝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夏立民、吳一立譯,文化藝術出版社,第3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