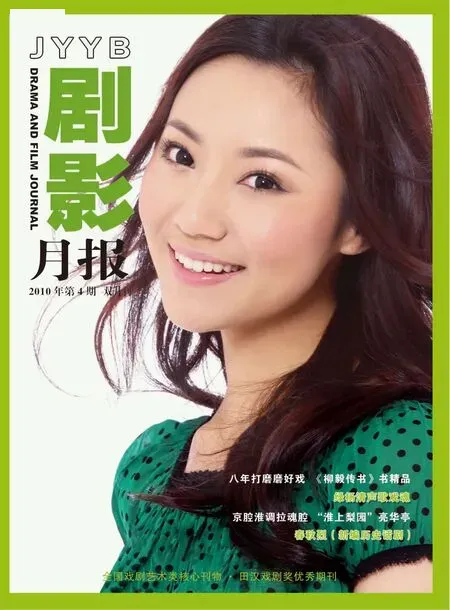方言與戲劇
■楊彥
方言與戲劇
■楊彥
語言,既是我們表演創作的內容之一,同時也是表演藝術創造的重要手段。
語言,永遠是和形象的思想、任務、動作與規定情境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演員是依據劇本的臺詞進行語言的二度創作的。這種創作,并不是簡單的背誦,做機械的舌尖運動,而是為了認識臺詞所包含的豐富的思想內涵,把它當作推動想象的主要材料,研究角色的天性及思想過程,進而掌握角色的第二天性,演員只有學會用角色的思想來思想,用角色的情感來體驗,已經成為劇中角色,掌握了角色的自我感覺,演員才有權利代表他的角色說話。無論在舞臺上,還是在影視中,語言藝術都能以它的魅力,給人們以藝術的啟迪,聽覺的享受。所以掌握好人物的語言,并運用言語塑造人物形象,是演員提高表演創造水平的一個重要任務。
所以,在我曾主演的話劇《夜店》,小品《鐘點房》,情景劇《娛人碼頭》及參演的電視劇《霓虹燈下的哨兵》等等中,我在詮釋石敢當,豆子哥,豹仔,二連長王士愛等人物時,不但從人物的外部形體特征中去尋找感覺,更在人物的語言上下足了功夫,貼進角色,尋找更適合角色背景的語言,并做了嘗試——運用方言(諸如徐州方言,安徽蚌埠方言,南京話,東北話,四川話,上海普通話及山東濟南方言等等)來詮釋人物,以求使人物更豐滿更具形象感!
一.什么是方言
方言是語言的變體,是地區性語言。方言可分為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兩大類:
①地域方言:一般說來,同一種地域方言集中在一個地區,也有的是移民把它帶到遠離故鄉的地方。
②社會方言: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人因為職業、階層、年齡、性別等不同,口語、措辭、言談也會有差別。
戲劇作品中的方言常常既有地域性又有社會性,是戲劇表演者把握人物文化、性格的可靠依據。“言為心聲”,方言在交代人物身份,刻畫人物深層心理,抒發細膩情感等方面,比之于普通話有更大的優勢。因為方言是真正的來自于生活,和人物的情感有著難舍難分、天然一體的牽連。
二.方言是訓練表演初學者的“良藥”
演員走上舞臺,面對黑洞似的觀眾審視自己的千百雙眼睛,或者是面對攝像機的鏡頭,有時連一些老演員也難免會心理緊張。對于初學者,初出茅廬的演員來說,這種情況就更為常見了。這種緊張往往會使演員失去應有的控制,頭腦中出現空白,心臟急速跳動,呼吸變得急促,聲音變了腔調,面部出現痙攣,有時甚至會全身戰栗,忘記了臺詞。盡管這種極端緊張的狀況在演出中為數不多,但演員在創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多余的緊張。因此,演員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釋放天性”,天性解放,消除緊張情緒,讓自己能夠自如地真實地生活在舞臺上。但戲劇舞臺上的環境并不真實,它是以虛構和假定的樣式存在的一種現實,這對于表演初學者又是一道障礙。那么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答案就是,讓演員們在舞臺上從說自己的方言做起。因為方言是他們各自最為熟悉的語言環境,比起普通話,他們運用的會更自由,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阻力。這對提高表演初學者的自信是很有幫助的。從說話開始,方言就是“良藥”!
三.方言與塑造人物
演員在熟悉掌握本地區方言及普通話的基礎上,還應該了解并掌握若干種其他地區的方言。
方言的話語,除了傳達信息,往往透射出一方人們的性情喜好,處事和言談的特點。在本地人和異鄉人的眼中,這種話語能顯示出地方風韻,傳達出鄉土的情趣。
會說方言不僅是演員的一種機能,更是塑造人物的一種技術。例如:(特型)演員在塑造偉大領袖人物(像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時,就涉及到這個問題,這些偉人們大都操著地道的方言。在外部特征上,化妝師可以幫助解決;而在人物語言上,則完全依靠演員個人去完成了。倘若演員運用的是標準、流利的普通話去塑造他們,難免會使這些人物的形象成為符號,失去了活生生的人的真實感。再如,我曾在塑造《夜店》中石敢當的形象時,有意識地將他的語言狀態,由劇本所給予的書面語言轉化為方言——山東話。立刻拉近了角色與第一自我的距離。由于人們的慣性思維,山東人一貫留給人身材高大、粗壯、魯氣十足的形象,這是石敢當的形象所需要的(人物職業位警察),正好與他做事情畏首畏尾,行動緩慢,甚至低三下四追女人形成反差,極具喜劇色彩。又如:胡適先生曾竭力推崇的一部中國純方言小說韓子云的《海上花列傳》,“……雙玉進前,與淑人并坐床沿,雙玉略略欠身,兩手都搭著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著雙玉頭頸,把左手按住雙玉心窩,臉對臉問道:’倪七月果一笠園,也像故歇實概樣式一淘米來浪說個閑話,耐阿記得……’”翻譯成普通話:“我們七月里在一笠園,也像現在這樣坐在一塊說的話,你記得嗎?”意思雖然一毫不錯,神氣卻減的多多了!——方言,刻畫人物是其特有的長處。一般,人們的思考總是用自己的方言進行的,聽口音可辨是何方人氏,解方言可釋心靈密碼。
四.方言的兩種藝術載體
一是戲曲,二是紀錄片。一古一今,一舊一新。
①藝術家族中,戲曲是方言擅長的一種重要表法形式。中國的地方戲曲,據不完全統計有300多種。他所傳演的語言形態都是各自的方言,如北京的京劇,山西的晉劇,陜西的秦腔吉林的吉劇,河南的豫劇,上海的滬劇,浙江的越劇等等,甚為壯觀,反映了各地的人文地理,風土人情,熔鑄了大量的文化信息。
②紀錄片,新興的藝術形式,是技術的產物,但他所攝錄的對象是最原生的,最真實的客觀存在。在鏡頭記錄下的時空內,人們交流的方式是最質樸的方言。當代有很多導演采用紀錄片的手法拍攝電影,用以尋找最真實的生存狀態,如李揚的《盲井》,片中演員操著地道的河南話。
五.方言的幽默細胞
一句陜西式的呼喊:“安紅,餓像膩!”成了張藝謀《有話好好說》中的經典臺詞。一時間更成為許多年輕男子的口頭禪,這是方言的魅力,是方言與生俱來的幽默細胞引起的反應。
中國著名的幽默大師侯寶林先生,也曾以方言為素材,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相聲段子。
其中有一篇名為《方言與戲劇》,里面有這么一段:有兩人在一個院里,一個在東房住,一個在西房住。那天都在睡覺,突然間,一屋房門一響,,另一屋發覺了,兩人開始對話:“喲嗬!那屋咣鐺一下子門響,黑更半夜這是誰出來了,一聲不言語,怪嚇人的!”/“啊—是我,您哪,哥哥,您還沒歇著呢?我出來撒泡尿,沒外人,您歇著您的吧,甭害怕,你吶!”/“黑更半夜的穿點衣裳,要不然凍壞了可不是鬧著玩的,您一發燒就得感冒嘍”/“不要緊的,哥哥,我這兒披著衣裳吶,撒泡尿我趕緊就回去,您歇著您的吧,有什么話,咱明兒個見吧,您吶!”這么簡單的一件事,晚上上個廁所,費了這么老半天話,在語言上有明顯的地域特色——北京話——夠貧!有沒有簡單些的表達方式呢?有!山東話!同樣這件事,三個字一句就可以表達清楚:“膩四誰?/借四我/上哪去?/上便所”。還有比這更簡單的表達——河南話!也同樣是這件事,一句一個字就解決問題——那屋房門一響,這屋發覺了,說:“誰?/我/咋?/尿。”完全相同的一件事,表達上竟有如此大的差別。多么生動,讓人忍俊不禁!
這些詼諧幽默的生活中的小例子,其實不勝枚舉,就在你我的身邊。他們實實在在地從生活而來,是人們最樸素最自然的流露,毫無修飾。然而,恰恰就是這種樸實無華的地方語言,一經搬上舞臺,他的幽默特質,便綻放出無限的光芒!
長久以來,在中國的小品舞臺上,許多著名的演員用各自家鄉的語言,塑造著各式各樣,性格各異的人物形象,將笑聲傳遞給千家萬戶!例如,趙麗蓉始終如一的唐山方言,魏積安以“伙計”為口頭禪,將山東方言進行到底;尤為突出的是東北方言,有趙本山、范偉、高秀敏、潘長江、鞏漢林等等一大批演員。特別要提出的是由趙本山、范偉、高秀敏組成的“東北鐵三角”,不但活躍在小品舞臺上,同時也在電視熒屏上有所建樹。被廣大老百姓所熟知的電視劇《劉老根》、《馬大帥》,及近來捧紅了眾多東北演員的《鄉村愛情》等的熱播,將東北人的樸實、機敏、幽默,表達得淋漓盡致!
說到方言的幽默性,那就不得不提到情景喜劇了。情景喜劇是比較純粹的喜劇,比一般的戲劇又高了一步,它要讓大家高頻率發笑,幾分鐘甚至幾十秒鐘就得出效果。多年來,情景喜劇的地域性越來越明顯了,有北京特色的《閑人馬大姐》,上海特色的《新七十二家房客》,西北風格的《西安虎家》,廣東韻味的《外來媳婦本地郎》,及東北風格的《東北一家人》。方言化業已成為了情景喜劇的重要標志性特征。
六.結語
盡管目前,在電影、電視及話劇中,規范了普通話仍然是主流的語言形式,但戲劇工作者們越來越追求藝術的真實質感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可見源自生活的方言,這一個非正規的語言形式,會有著十分廣闊的發揮空間,因為它是真真正正的生活體現者,是土生土長的藝術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