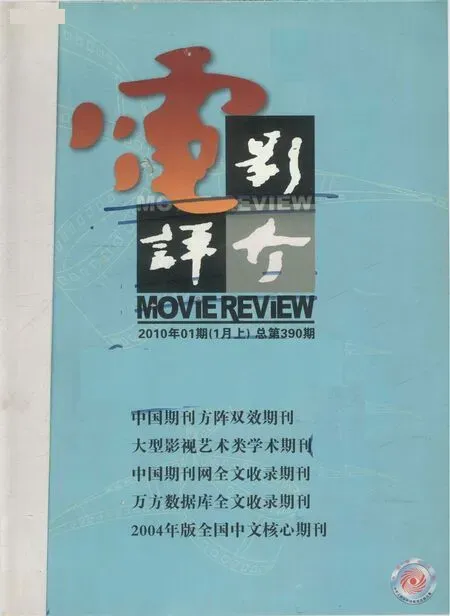意識中的反思到態度上的寬容
第五代導演主要是指“文革”時期被耽誤學業,落腳在鄉村插隊或工廠從事體力勞動,新時期考入電影學院的第一批導演們,以及相近年齡經歷而80年代開始創作的青年導演們。[1]其中,張藝謀是第五代導演的重要人物,在他的影片中,用色彩強烈的優美畫面深刻反映了被壓抑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張揚了個體意識,體現文化反思的意味。而所謂的“第六代”,即學院派年輕導演,更多是90年代后有零散作品面世的新近導演們。[2]其中賈樟柯便是第六代導演的重要人物。從第六代導演的生活閱歷看,他們生活的接觸面相對狹窄,每人身上背負的文化包袱顯然沒有那么沉重。[3]從賈樟柯的片子上看,他關注的是人性,關心的是人性背后的隱痛,對現實無奈的寬容。本文通過論述張藝謀和賈樟柯的影片看到,雖然張藝謀在影片中展示的是對個體生命的張揚,表面上是反傳統,但是他并沒有真正支持反傳統,他的骨子里仍然是對社會約定習俗的認可。他對生命的張揚僅僅是反思。賈樟柯展示的是對人物隱痛的關注,雖然沒有提到反傳統的角度,但是對人物隱痛則表達出寬容。從張藝謀到賈樟柯,是意識到具體的深化,是反思到寬容的深化。
一、完美的畫面展現人性的釋放
張藝謀是公認的形式主義大師,在影片的畫面上頗費功夫。《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中對造型空間的拓展,《秋菊打官司》里故事片和紀錄片的手段完美地結合一起,《有話好好說》對運動鏡頭的嘗試,張藝謀在形式上不斷求變,他的實踐也給中國電影開辟了新的道路。[4]除了形式多變,張藝謀還比較注重色彩,畫面構圖,光線。例如《黃土地》影片以土黃為主調,但在幾個段落中,大量拍攝紅色:轎簾、紅蓋頭、紅衣紅褲、紅腰帶、紅腰鼓、紅花紅馬……[5]除了黃色和紅色,《黃土地》還很注意黃、黑、白、紅色的搭配,黃色的土地,黑色的粗布棉襖,白色的羊肚毛巾和紅色的嫁衣蓋頭。在光線上,《黃土地》光線以“柔和”二字為主。外景多用早晨、傍晚的光效,內景用大量的散射光和柔光照明。在個別場景中,有意識運用明亮陽光構成大反差,加強視覺印象。[6]而《一個和八個》,影片色彩就以黑白灰為主調,其他任何鮮艷的色彩都不要。《一個和八個》雖然以黑白為主調,但是很注重光線反差,在內景中,運用房屋結構所造成的明暗光區;在外景中,運用強烈陽光下造成的亮面和陰影。全片幾乎完全采用自然光,個別內景中用少量燈光。[7]在《英雄》中紅色和墨色的運用,《十面埋伏》大面積綠色的運用,都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視覺享受。
在聲音的處理上,張藝謀也頗費心思。按照張藝謀的說法,《紅高粱》對音樂總的要求是國粹化。《紅高粱》一直用淡淡的音樂,音樂的張力主要都在他們嘩啦嘩啦表現出來。[8]在樂器選用上,主要運用嗩吶和中國大鼓這兩件樂器。而《一個都不能少》全部用的是河北民間一帶的小調和民樂。在《我的父親母親》中,張藝謀則認為這個音樂不拘泥于全部用民樂或者是民間小調,采用了一種中西結合的構思,但原則上是獨奏樂器還都是東方化的,但也使用了合成器,同時加進了西洋音樂,主旋律只要求好聽。[9]在《英雄》中,聲音也是一個亮點,除了在兵器的碰撞聲,還配上京劇的吶喊、叫白、念白。
由此而見,在畫面和聲音上,張藝謀花費了一番心思。更多的時候,看張藝謀的電影就是在欣賞一幅幅優美的圖畫。傳統的音樂與優美的畫面結合起來,帶給觀眾的是強烈的感官享受。但是在畫面和聲音上的精雕細琢,看似完美的畫面,傳統的聲樂的深處,卻是影片對人性的深刻反思,對個體意識與社會制度沖突下的反思。例如《紅高粱》體現的是個體生命的張揚,《大紅燈籠高高掛》體現的是女性爭奪寵愛和利益的風波,是生命欲望和物質利益的角逐,《菊豆》體現的是愛情與人性與世俗的沖突等等。從內容上看,張藝謀僅僅是關注被壓抑的個體意識,以及個體精神在壓抑的狀態下爆發和舒展,是人性的釋放。
二、紀錄性電影語言對人性的寬容
賈樟柯的電影,沒有像張藝謀那樣對畫面進行精雕細琢,他所拍攝的生活場景,日常生活的瑣碎的事情,鏡頭所到之處也是日常之景,影片所闡述的也是生活本身的敘述。賈樟柯的鏡頭是克制的。他常常將自己和攝像機限制在空間以內的某個位置,然后從不超越也不試圖超越這個位置。他的鏡頭所能做的,就是靜靜地觀望。賈樟柯的這種影像風格,實際上仍然是基于他個人一貫以來的敘事原則。攝像機的鏡頭攝錄下來的,出于生活本身的偶然,沒有刻意和特定。它們只是生活本身的片段。將具體的若干空間從生活空間里抽離出來,從而完成對于生活本身的敘述。[10]
在賈樟柯電影里,畫面和聲音都看似隨意。如果說張藝謀電影的背景唯美,那么賈樟柯電影的背景則務實。主要體現在是大量新聞背景的運用,大量廣播音的運用。例如在《站臺》里,劉少奇的平反,國慶35周年的閱兵……這些整個中國政治生活的大事件,通過背景音的廣播喇叭被穿插在影像之外,而且新聞事件與劇中人物息息相關,直接影響著他們的命運;《小武》中,新聞也以幽默的方式跟劇中人物產生互動;《任逍遙》也運用了大量的新聞背景,充斥著21世紀的國家大事,但新聞背景呈現出夸張煽情的面貌,完全游離于劇情之外,與劇中人物也幾乎沒一點兒關系。當《任逍遙》里那兩個年輕人冷漠地站在一群對著電視機歡呼的人群中時,這里對新聞背景的運用所暗示的訊息已經同《站臺》里完全相反了。[11]雖然新聞背景的運用在賈樟柯的這三部電影里呈現出漸行漸遠的走向,但是新聞背景在影片中的運用,模糊了電影和現實的界限,帶給觀眾很大的現實感,同時通過廣播音,可以看到時代變遷和社會景深。
賈樟柯電影還喜歡運用流行歌曲。例如他影片中刻意選擇了許多當年的流行歌曲,比如前面提到的兩個片段,《小武》里一首王菲的《天空》,《站臺》里一首羅大佑的《是否》,都深刻地表達了人物的情緒,并且足以表現人物當時所面對的命運。[12]除此之外,《心雨》、《江山美人》,《霸王別姬》等流行歌曲的運用,加上街上的各種噪音:自行車、卡車、摩托車等等,這些都給影片帶來強烈的現實感,把人的情緒帶回到當時的年代和心境,也折射出當時的時代氣質。也正如賈樟柯自己所說的:“我的原始想法就是讓我的影片具有一定的文獻性:不僅在視覺上要讓人看到,1997年春天,發生在一個中國北方小縣城里實實在在的景象,同時也要在聽覺上完成這樣一個紀錄。這樣,我就根據劇情發展的需要,特意選擇了那一年卡拉OK文化中最流行、最有代表的幾首歌,或者說最“俗”的幾首歌,尤其是像《心雨》,幾乎所有去卡拉OK的人都在唱這個東西——那種奇怪的歸屬感。這些東西實際上又都是整個社會情緒的一種反映。譬如《愛江山更愛美人》那樣一種很奔放的消沉,還有《霸王別姬》里頭的那種虛脫的英雄主義……都正好就是我在影片里想要表達的。這些東西在聲畫合成的時候,很好地幫助我烘托了影片的基調。”[13]
總體來說,無論是廣播音還是流行歌曲,展現的現實主義基調,讓人感覺是影片的故事與現實距離很近。從題材上來講,賈樟柯的《小武》是一部打破現實和電影之間界限的電影。《小武》是對那種“唯美”電影的反叛,很多創作者認為和社會接觸會降低電影的美學含量,但其實完全可以通過美學的方法來談論社會這個話題。藝術家注重小人物的日常瑣碎生活,表現他們生存的艱難,個人的孤獨無助,賈樟柯采用了一種“還原”生活的“客觀”的敘述方式,這中間就透露了他的創作企圖:不做主觀預設地呈現生活“原始”狀態。賈樟柯的創作切入了過去“寫實”電影的盲區,他站在現實面前,觸摸到現實的脈動,又不拘泥于現實,看到了現實背后的內在力量。[14]《小武》中對小偷等這些邊緣人物的關注,體現了賈樟柯對人生的另類關注。小偷只是一個職業,在這個職業背后,小武還是一個人,這個人依然重親情,講義氣,尊重愛情。所以,影片中對小武的關注,在更多程度上體現的是對人性的溫暖關懷,是一種對生命的寬容和溫情。
三、從反思到寬容,由冷漠到溫情
有學者指出,第五代電影創作的重要特征是文化反思與哲理思考的自覺意識。[15]第五代“文革反思”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以重提被壓抑的“個人話語”開始的。這一話語所蘊含的第一層面是“人道主義”的內容,即遵從人生的真實,尊重生命的權利和維護人格的尊嚴。[16]
張藝謀是第五代導演的重要人物。他真正擅長的題材,是那種富含文化底蘊的、有內在張力的題材。[17]他的大部分影片中也正是對生命的尊重和人性的解放。例如《紅高粱》中對生命的張揚,人性的解放。《菊豆》中對被壓抑人性的釋放。他的影片多數突出地表現了個體意識對傳統觀念的反思,僅僅是停留在反思這個層次,在反思的背后并沒有提出合理的解決方式。而他對主女主人公的命運安排,也是個性欲望和個體意識擴大化,將跟人命運與社會沖突矛盾放大,在個性意識在社會約定俗稱規矩面前,張藝謀選擇了遵循社會規矩,他導演下的女主人公的命運選擇了符合約定成俗的結局:女性有個性意識,但這種個性意識在現實社會下得不到合理表達,如果擴張個性意識,很有可能走向悲劇下場。例如《紅高粱》:女主人公九兒被日本兵流彈打死。《代號美洲豹》:女護士阿麗突遭男友劫持,慘遭殺害;解放軍少校梁北亦光榮犧牲。《菊豆》:女主人公點燃一把大火,將自己連同染坊的“黑屋子”一同燒毀。《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女主人公突然發瘋了。《秋菊打官司》的女主人公一直想要一個“說法”,待到“說法”有了,卻反使她惶然不知所措又大惑不解。《活著》的結尾基本上正常,但它給人的總體印象仍是該死的人卻沒有死;該活著的人卻并沒有活著。[18]從這一角度不能看出,張藝謀骨子里是傳統的,他對生命的壓抑僅僅是關注,并沒有勇氣去寬容,也并沒有真正反抗。所以,在他影片中,在完美的畫面背后是對人性的關注,對命運的冷峻深思,對個體意識的冷漠。張藝謀具有反傳統的意識,但是他并沒有反傳統的局限,電影所表現的是對被壓抑的人性的關注,但是僅僅是關注,骨子里對人物的命運還是傳統的看法,女主人公的最后下場也符合傳統觀念對此類女性的命運解讀。
而賈樟柯的名字已不僅僅是一個導演的符號,他是新時期某種電影文化的一個縮影。他的四部劇情長片展示了當代中國電影十分罕見的真實品質,他對當下社會的直面輯錄、對底層人物細膩而貼切的描繪,以及平靜從容的敘事,給我們帶來的不只是撫慰,還有心靈的震撼和精神的共鳴。[19]有人說,賈樟柯發現了中國的鄉鎮,我想這并非溢美之詞,事實上,他不僅為我們展現了獨特又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中國鄉鎮(即使是以都市為背景的《世界》,也讓我們看到大都市骨子里的鄉鎮氣息),他更以對小地方小人物的準確把握,讓我們窺見了全球背景下的大中國。觀看他的影片,我每每驚嘆于他對細節的捕捉,對道具的深入開發和運用,更重要的是他對世態人情平靜而高超的體察,看似漫不經心,實則獨具匠心。[20]
在賈樟柯電影中,我們看到的是他對邊緣人物的關注,對人性的關懷,對人另類性情的溫情關懷。例如,《小武》中,避開了他運用不正當手段圖謀利益的一方面,而這方面往往也是他生存的最主要方面,而著重描述他善良的一面。在現實生活中,或許小偷友好是他性格的深層特點,但浮光掠影地展現出來,這浮光掠影的一瞬間被賈樟柯抓住了,并且將它擴大化。盡管如此,賈樟柯對小偷重情義的一面的關注足以體現他的寬容。他對底層從容、樸素的寫實,處處留露出對另類人性的寬容和溫情,對小武的寬容,對小姐的寬容等等。這與張藝謀對人性反抗的冷漠態度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學者所說,賈樟柯是新生代導演中藝術現實表現最動人的一位。他觀察世界和認識生活的深度是獨特的,作品的真實坦蕩與內在溫情相互襯托。[21]賈樟柯對邊緣人物的關注,對劇中人物的命運的安排,本身就是一種寬容和溫情。
綜上所述,張藝謀的影片,會給觀眾強烈的視覺享受,雖然他在影片里舒展了個體意識,但是骨子里,他只是欣賞這種個體意識,他并沒有充分肯定并支持這種個體意識,他內心深處是傳統的,他對人性的張揚僅僅是停留在反思階段,對人性的張揚也沒有給予足夠寬容。而賈樟柯的影片,從日常瑣碎的角度拍攝,注重日常細節的手法,對另類人性的關注,恰恰體現了他對人性的寬容。所以,從張藝謀到賈樟柯,我們看到了,對被壓抑人性的關注,到對被壓抑的人性的關懷,對邊緣人物的寬容,對邊緣人物的溫情。可以說是,是從意識形態到具體人物,從反思到寬容,從關注到溫情,這恰恰是認識事物的線索,是認識由表層到深層的深化。
[1]周星《中國電影藝術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2月,第260頁。
[2]周星《中國電影藝術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2月,第310頁。
[3]陸邵陽《中國當代電影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第133頁。
[4]陸邵陽《中國當代電影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第83頁。
[5]張明《與張藝謀對話》,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26頁。
[6]張明《與張藝謀對話》,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25頁。
[7]張明《與張藝謀對話》,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3頁。
[8]張明《與張藝謀對話》,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41頁。
[9]參見張明《與張藝謀對話》,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2月,第179頁。
[10]林旭東,張亞璇,顧崢編《賈樟柯電影——站臺》,中國盲文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30頁。
[11]參見倪震《北京電影學院 故事——第五代電影前史》,作家出版社,2002年2月,第101頁,第227頁。
[12]參見倪震《北京電影學院 故事——第五代電影前史》,作家出版社,2002年2月,第228頁。
[13]參見格非,賈樟柯《一個人的電影》,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64頁。
[14]參見陸邵陽《中國當代電影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第139頁。
[15]周星《中國電影藝術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2月,第261頁。
[16]陳捷《第五代電影:現代性的追求與反思》,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12月,第43頁。
[17]黃曉陽《印象中國——張藝謀傳》,華夏出版社,2008年8月,第91頁。
[18]陳墨《張藝謀電影論》,中國電影出版社,1995年6月,第223頁。
[19]格非,賈樟柯《一個人的電影》,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78頁。
[20]格非,賈樟柯《一個人的電影》,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81頁。
[21]周星《中國電影藝術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2月,第3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