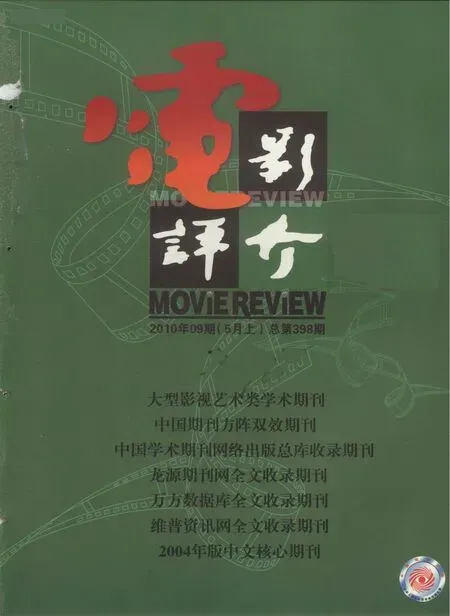話語與愛情的極致呈現(xiàn):法國導(dǎo)演埃里克?侯麥的系列影片《四季故事》
埃里?克侯麥?zhǔn)欠▏娪暗囊欢蝹髌妫鳛橛绊懥薮蟮姆▏吕顺彪娪斑\(yùn)動(dòng)的五位《電影手冊》派主將之一,侯麥的電影似乎是最不露鋒芒、最具文學(xué)特色的(侯麥本人確實(shí)首先以文學(xué)家的身份出現(xiàn))以及、也可能是最缺少變化的導(dǎo)演,當(dāng)侯麥的同僚戈達(dá)爾、特呂弗、里維特、夏布羅爾等人以一部又一部驚世駭俗、藝術(shù)暴動(dòng)式的影片、論文問世時(shí),他和他的影片卻確始終創(chuàng)造和延續(xù)著一種傳統(tǒng),一種在法國藝術(shù)(包括電影)中經(jīng)久不衰的、一種敏銳、飽含智慧而又不羈的藝術(shù)觀念。侯麥的作品既有一種古典主義氣息(區(qū)別于特呂弗那種折中的古典主義電影),又具有現(xiàn)代電影的特征。侯麥以描寫愛情見長,影片通常以人物對話支撐整部影片。 1989年到1998年間拍攝的《春天的故事》、《夏天的故事》、《秋天的故事》、《冬天的故事》(《四季故事》)是侯麥半個(gè)世紀(jì)電影生涯中所創(chuàng)作的第三個(gè)也是最后一個(gè)系列,之前分別有《六個(gè)道德故事》和《喜劇與諺語》系列,《四季》系列也是侯麥拍攝的最后幾部現(xiàn)代劇,之后侯麥的創(chuàng)作轉(zhuǎn)向古裝劇(《貴婦與公爵》、《三重間諜》和最后一部作品《阿絲特蕾與塞拉東的愛情》),直至2010年1月侯麥以89歲高齡與世長辭。《四季》系列延續(xù)了侯麥一貫的獨(dú)特美學(xué):言語(Parole)、話語的使用,侯麥的電影的故事全部以人物的對話支撐,人物的對話體現(xiàn)出的人物的思考、焦慮乃至表現(xiàn)出的的愚蠢都原原本本地展現(xiàn)在銀幕上,每部電影看起來像是記錄了許多場的對話,一場戲就是一次對話,實(shí)際上話語的完全展現(xiàn)呈現(xiàn)的卻是一副“神經(jīng)質(zhì)的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復(fù)雜的內(nèi)心世界的驚人圖景[1]。
一、愛情、等待、選擇與巧合:情節(jié)與敘事
《四季》的故事均以愛情為主題,《春天》講教哲學(xué)的中學(xué)女教師讓娜來到聚會上認(rèn)識的女孩兒娜塔莎家里寄住,并且認(rèn)識了娜塔莎的單身父親伊戈?duì)柡退贻p的女友伊芙,和伊芙相處不好、甚至懷疑伊芙偷竊自己項(xiàng)鏈的娜塔莎有意撮合自己和伊戈?duì)栆源嬉淋剑屇绕鋵?shí)也與伊戈互相產(chǎn)生好感,兩人獨(dú)處接吻后,讓娜又掙脫出來回了巴黎,兩人在娜塔莎家里找到了丟失的項(xiàng)鏈,消除了一切猜忌,回歸風(fēng)平浪靜;《冬天》里的菲莉希在兩位男友馬克桑斯和路瓦克之間游移不定,其實(shí)心中在盼望五年前因意外失散的情人、也是菲莉希小女兒的父親夏爾的出現(xiàn),本來完全無望的等待卻遇到了奇跡,應(yīng)該在美洲的夏爾就在家門口的公共汽車上出現(xiàn)了;《夏天》中,大學(xué)生、業(yè)余作曲家帕斯卡來到海邊小城迪納爾等待女友雷娜,期間認(rèn)識了熱情、知性的女招待瑪戈,和在舞會上邂逅的迷人性感的索萊娜,雷娜后來也不期而至,同時(shí)面對時(shí)冷時(shí)熱、陰晴不定的三個(gè)女孩的帕斯卡完全不知所從,影片最后一個(gè)買錄音機(jī)的電話為帕斯卡解了圍,他背上背包瀟灑地離開小城,“留下瑪戈一人獨(dú)自等待”;《秋天》也許是四季中最圓滿的一部喜劇,四十五歲的單身母親瑪嘉利在自家葡萄園種葡萄,兒子的女友、也是瑪嘉利的忘年好友羅欣以及好朋友伊莎貝拉都打算分別將前男友哲學(xué)老師和征婚廣告上認(rèn)識的男子杰拉德介紹給瑪嘉利,卻又不完全舍得拱手相讓,明白過來的瑪嘉利雖然也有失望和怨氣,卻表現(xiàn)出比兩位女友更難得的大度、坦率,最終收獲了與杰拉德的愛情。
侯麥在《四季》中依然將攝影機(jī)對準(zhǔn)現(xiàn)代生活中日常生活的人,大學(xué)生(《夏天》中的帕斯卡、瑪戈,《秋天》中的羅欣,《春天》中的娜塔莎)、知識分子特別是教師(《秋天》中的哲學(xué)教師,《春天》里的讓娜)和書商(《冬天》中的路瓦克、《秋天》里的伊莎貝爾),中產(chǎn)階級和小資產(chǎn)階級。情節(jié)一如既往地侯麥風(fēng)格:愛情的等待、愛情的選擇、愛情的巧合。《四季》中的主角基本都在等待,等待雷娜(帕斯卡)、(空空地)等待夏爾(菲莉希)、等待遲來的愛情(瑪嘉利);他們又都面臨著愛情的選擇,面對男友和伊戈?duì)柕淖屇龋ā洞骸罚鎸θ齻€(gè)男人的菲莉希(《冬》),三個(gè)女人的帕斯卡(《夏》)以及面對兩位優(yōu)秀男子的瑪嘉利(《秋》);情節(jié)的發(fā)展和結(jié)束又來自侯麥戲劇化編排的巧合:《春》里五人在郊外別墅的相遇,《夏》中同時(shí)與三位女孩定下的約會以及最后帕斯卡獲得的脫身理由,《秋》中婚禮前后發(fā)生的一系列巧合,《冬》中在公車上遇見失散五年男友極致的、事實(shí)上是奇跡(Miracle)的巧合。每部影片通過巧合全部回歸道德,看似風(fēng)平浪靜的戲劇化圓滿結(jié)局,明眼的觀眾早已看出背后的風(fēng)起云涌,結(jié)局并不是表現(xiàn)的重點(diǎn),情節(jié)的進(jìn)程,人物的話語以及在行動(dòng)時(shí)的心理狀態(tài)才是侯麥要展現(xiàn)的,正如侯麥自己所說:“我不說,我呈現(xiàn)”( "Je ne dis pas, je montre")。
《四季》的劇作手法同前兩個(gè)系列一樣,都是描寫愛情“擁有之前”的欲望發(fā)酵的過程[2]。然而《四季故事》在敘事上還是與之前的兩個(gè)系列相比有自己的特點(diǎn)。首先,《四季故事》在形式上基本采用全知全能的的視角,一切人物和劇情通過場景以及人物對話客觀的記錄下來,這里我們可以拿侯麥早期的《六個(gè)道德故事》做以比較,《道德故事》中的故事以第一人稱為視角,并且以大量的角色的畫外獨(dú)白帶領(lǐng)觀眾體驗(yàn)角色的經(jīng)歷,由此或許可以看到侯麥得某種創(chuàng)作軌跡,一種更加透明、客觀和簡潔的風(fēng)格的形成;其次,《四季》中作者視點(diǎn)依然具有性別,《四季》中以女性為主,只有《夏天》以男大學(xué)生帕斯卡為視點(diǎn),帕斯卡、菲莉希、瑪嘉利、讓娜其實(shí)都代表某種作者的視點(diǎn),盡管作者的視點(diǎn)并非完全認(rèn)同與劇中人物的視點(diǎn),作者隱藏在攝影機(jī)后冷靜地講述, 侯麥的電影要達(dá)到兩種境界:一種是故事, 人物用自己的目光看待世界, 這要比作者的主觀視點(diǎn)更直接、更敏感, 因?yàn)槿宋锸窃谇榫持校涣硪环N是紀(jì)錄,然而侯麥的紀(jì)錄與 “真實(shí)電影”和 “直接電影”的紀(jì)錄不同,它不是“從現(xiàn)實(shí)中來”,是一種“貼近現(xiàn)實(shí)”的劇情電影[2],一切都是侯麥精心編排好了的,他的電影幾乎從沒有過即興成分[3]。
二、話語與對白使用的極致:聽覺與畫面
關(guān)于侯麥影片中著名的“話語”,譯自法文 “l(fā)e parole”一詞,指電影中由人的聲音傳達(dá)出的語言能指,包括獨(dú)白、旁白、對話、歌詞(《夏天》中的《海盜女之歌》是最明顯的例證)等,在“言語”(le verbal)的意義上,也包括字幕。[1]侯麥電影中的敘事涉及的只是一個(gè)未完成的動(dòng)作,人物的情況和存在方式要比事件本身更加重要[4],而在人物的情況與狀態(tài)幾乎全部來自話語,話語在《四季》中突出表現(xiàn)為人物的對白、對話,旁白這一侯麥之前電影中的重要元素在《四季》中不再出現(xiàn)(《克萊爾的膝蓋》第一次放棄使用畫外音的旁白),《四季》系列將侯麥電影的。影片中的人物仿佛個(gè)個(gè)都有說話的嗜好,不斷地談?wù)搻矍椤⑺囆g(shù)、文學(xué)、宗教(侯麥同布烈松一樣具有天主教背景)和哲學(xué),最好的例證是《春天》中的哲學(xué)教師與伊戈?duì)柤捌渑岩淋皆谝黄鸫笳劦摹跋闰?yàn)綜合判斷”以及《冬天》中在路瓦克家關(guān)于哲學(xué)、奇跡和來世的討論,有趣的是這兩處的談話,分別都指向影片的主題,讓娜和娜塔莎的“先驗(yàn)判斷”與在菲莉希身上所發(fā)生的“奇跡”。日常的談話也是影片表現(xiàn)的內(nèi)容,坐車走路時(shí)的談話、閑談甚至見面時(shí)的寒暄流露出角色的情緒、狀態(tài)、想法,甚至他們的窘迫和謊言也一覽無余,他們的嘴在表達(dá)一種意思,而眼神和身體卻告訴我們不同的信息,比如《夏天》中帕斯卡面對三個(gè)女孩的不同說辭,《冬天》中菲莉希要跟馬克桑斯去內(nèi)維爾時(shí)對路瓦克的解釋 。分析侯麥的影片需要注意視覺的畫面和聽覺的畫面的辯證關(guān)系,視覺畫面不用多講就是我們看到的銀幕上的的畫面表現(xiàn),而聽覺畫面是一種精神層面的畫面,電影的聽覺元素(音響、話語和音樂)經(jīng)過人腦的加工,在腦海里浮現(xiàn)出一種圖景,電影的聽覺畫面類似于文學(xué)中讀者通過對文字的讀解在頭腦中形成想象的畫面。這種畫面雖然受到文字意義的限制,但因文字是抽象的物質(zhì)存在,故讀者的主觀意識會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 因而這種畫面始終存在著某種隨意性[1]。而在侯麥的電影中,視覺畫面卻充當(dāng)了“話語的傀儡” (吉爾?德勒茲語)。侯麥的視覺畫面相比于安東尼奧尼等的以視覺見長的導(dǎo)演顯得毫無意義,《四季》中出現(xiàn)的都是極其普通的生活場景,公寓、街道、餐廳、海灘、田間,畫面的色彩都是影片中景物和物體的固有色,影像成為僅僅是承載話語的一個(gè)布景。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對侯麥來說, 拍一個(gè)場景就是拍一場對話。侯麥拍攝對話的美學(xué)原則是將銀幕上的對話場景最大限度地表現(xiàn)得與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實(shí)際場景一致.[1]在拍攝對話時(shí),正/反打仍是侯麥記錄對話的主要手段,與好萊塢式正反打不同的是,侯麥?zhǔn)褂玫溺R頭都呈現(xiàn)出人的大半身體,在記錄角色話語的同時(shí)展現(xiàn)角色的眼神與身體活動(dòng);《四季》中也有許多鏡頭是固定的, 對話者都在一個(gè)畫框內(nèi),《冬天》、《春天》那兩場重要的討論就發(fā)生在同一畫框中。 當(dāng)拍攝街道、海灘上的對話場景時(shí),他多使用跟鏡頭,比如《夏天》中帕斯卡與雷娜、瑪戈在海灘的對話和《秋天》中瑪嘉利與伊莎貝爾在田間的對話,這是因?yàn)楸尘安粩嘧兓?反打在這里不再適用[4]。
結(jié)語
焦雄屏說:《四季故事》是侯麥對心靈、知性及現(xiàn)代人彼此征逐的探索,溫厚、深情,不吁嘆也不扭曲,四個(gè)季節(jié)成為注重場面調(diào)度和細(xì)致心理活動(dòng)的侯麥的最好隱喻[3]。侯麥一如既往地關(guān)注生活中瑣碎卻真實(shí)可見的情趣,關(guān)注愛情、倫理和道德,最重要的是關(guān)注人和人性,無論是“道德”“諺語”“四季”都是對人性真善美的真誠探索,他在晚年用完整記錄的內(nèi)容豐富的話語、真實(shí)連貫的空間與精心編排的精美情節(jié),仿佛畫家的畫筆,描畫出人間四季的動(dòng)人圖景。
[1]劉捷. 愛情故事還是戀人絮語? ——埃里克?羅麥爾系列影片中的話語[J]. 《當(dāng)代電影》2003.6.
[2]衛(wèi)西諦. 《阿絲特蕾與塞拉東的愛情》:侯麥最后的愛情神話[J]21 世紀(jì)經(jīng)濟(jì)報(bào)道/2008 年 /4 月 /28 日 /第 035 版
[3]焦雄屏. 法國電影新浪潮(上、下)[M].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
[4]米歇爾?賽爾索(法)李聲鳳 譯. 埃里克?侯麥——愛情、偶然性和表述的游戲[M].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