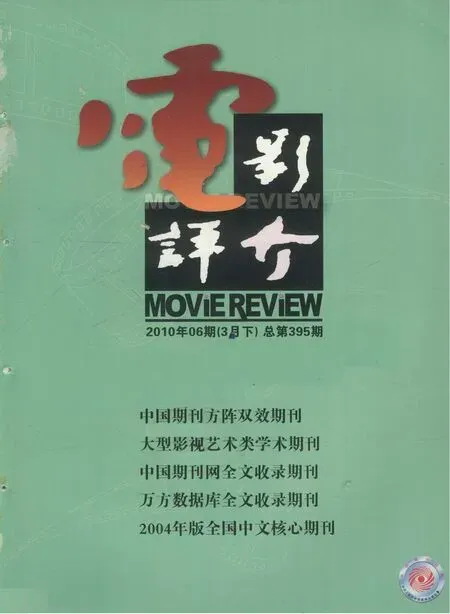論維多利亞時代女性小說中的花園意象
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的諸多女作家——如勃朗特姐妹、喬治?愛略特、蓋斯凱爾夫人等——作為一個群體,在英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擁有不容忽視的地位,這不僅是因為她們終于沖破千百年的沉默,在寫作領域真正發出了女性的聲音,更重要的在于,她們對傳統與現實的思索,達到了真正的深度。而這些女作家使思考形諸于形象的技巧,也達到了真正的嫻熟。這種成熟在其小說的重要意象——花園——中體現得極為明顯。
維多利亞時代著名的散文作家約翰?羅斯金在其作《百合——談王后的花園》卷首,從希臘文的《圣經?舊約》中引用了一段話:“你要感到高興,啊,干旱的沙漠;讓沙漠上充滿歡樂,遍地開滿百合一樣的花朵;約旦的荒蕪土地將生長出茂密的林木”(《以賽亞書》35:1)。[1](59)雖然這是一篇論述婦女地位、作用及教育的文章,但花園在維多利亞人心目中的神圣象征由此可見一斑。
在基督教文化的傳統中,“花園”是具有鮮明宗教色彩的意象。以花園象征天堂,以人的樂園隱喻神的國度是從《圣經?創世紀》便已開始的傳統。伊甸園是一座靜謐和睦的花園,在那里,亞當與夏娃及其統領的飛鳥、走獸、游魚過著井然有序的生活,不必經受饑寒的摧折,也從未感到智慧的痛苦。人間的亞當擁有神的形象,地上的伊甸園也是天堂在人間的投影。于是,從亞當的時代開始,人類漂泊一生、上下求索的精神家園便與花木扶疏、陽光明媚的花園有了某種內在的聯系。
此后的基督教世界中,現實生活和藝術作品都常以花園作為寄托精神信靠的物質載體。修道院內院以噴泉為中心的花園是隱修者心目中天堂的寫照。拉斐爾的名畫《美麗的女園丁》用花園中溫柔嫻靜的女子表現天堂里純潔安詳的圣母。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小說也常把花園同人類的最終歸宿相提并論。“在我不得不去的地方,會有春天,還有鮮花,不凋花和絢麗的禮服”[2](113),這春光似海、人花相映的花園正是《南方與北方》里垂危的貝西心馳神往的天堂。
但是另一方面,維多利亞時代又是一個在傳統與變革之間不斷徘徊、不斷受到沖擊的時代,這些沖擊,不但來自于教育水平的提高所導致的對傳統信仰的反思,亦來自于自然科學的發展。于是,神學,便在科學思想與圣經世界之間小心翼翼地尋找著使二者和睦共處的良方,關于天堂的兩種概念由此產生。其一,天堂是浩淼蒼穹中人類永遠無法知曉、受到神圣崇拜的上帝之城。其二,天堂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思想的狀態,在那里,不論世俗的愛還是神圣的愛都能得以圓滿。“在科學的時代里,天堂最低限度可以被描述為此岸世界道德精神高度完善的狀態”[3](122)。愛上帝并愛人如己是基督教最大的誡命,由此推衍出信眾對個人道德的重視。道德的完善無疑表明了人在自己身上實現了上帝的目的,同時亦拉近了人與上帝的距離。因此,這種向上天飛升的心靈狀態同樣把天堂的傳統功能付諸實際。這種思想變革所喚起的宗教觀念的變遷明顯體現在女性小說的花園意象里。
無庸質疑,維多利亞小說中的花園,往往成為重要情節上演的場所,不過,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筆下的花園卻有顯著的不同。在男作家那里,花園儼然是天堂的象征,它總是與充斥偽善欺詐的城市截然對立,在喧囂的天地中偏安一隅,文明與秩序、溫情與愛戀,都在都市中這寧靜的角落悄然上演。而為了保證夢想的完美與持久,就必須斷絕花園與城市的往來交通,因為只有當城市的的污穢丑惡無法對花園構成實質性威脅時,花園才能成為“和平的處所,一個不僅用以躲避一切傷害,而且借以排除一切恐懼、懷疑與分裂的場所。”[4](295)因此,男作家的花園是和諧美麗的,但也是與世隔絕和缺乏變化的。實際上,男作家筆下“理想花園的品質——美麗、封閉、蒼翠宛若荒漠綠洲——也正是理想的家的品質”[5](227),天堂一般寧靜美麗的花園展示出的其實是男性作家溫馨然而世俗的家庭理想。
與男作家整飭明麗、遺世獨立的人間天堂相比,在女作家的作品中,和花園相聯系的天堂不再是那個受到頂禮膜拜而遙不可及的場所,也并非與作者對家庭懷有的世俗愿望相連,它更多地表達了一種與天堂、神圣相貼近的心靈狀態,一種以全部力量愛上帝和他的一切創造物的精神境界。
女性小說的花園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的內涵。
首先,開放性是花園的主要特征
“基督教的精神永遠是愛——一種完全無私的精神,一種尊重他人并為他們尋求最高的善的行動。”[6](153)這種愛促使人們走出封閉的自我,從恩怨悲歡里掙脫出來,向廣袤的世界敞開胸懷。與之相應,女性作家的花園便不再是封閉和私密的場所。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作家喜愛流連于遠離城市的鄉村原野,她們作品中的花園往往和周邊的山野田園水乳交融,與大自然的山川河流、草木禽鳥相依相伴的花園便具有了空間上的放射性,正如露西的學校是被市內大花園環繞著,周圍是向遠方延伸出去的原野(《維萊特》)。與此同時,空間上的放射性也帶來心理上的延展性。這樣的花園總是無法拒絕來自外界的信息,即使象貝克夫人那樣曲徑通幽、防守嚴密的花園也因為毗鄰男校宿舍而時常受到“神秘修女”的滋擾(《維萊特特》)。
空間與心理上的開放性決定了這樣的花園不太可能把園中人的行為與情懷封閉在院墻之內。走出花園,走出個人的喜悅和憂傷時常是園中人不約而同的情感取向。在感情方面遭受挫折的凱特潤娜,穿過如織細雨和城堡花園的憂傷凄涼為管家送去御寒的圍巾(《牧師情史》);阿格尼斯走出霍頓莊園沉郁的花園看望病中的南希?布朗并為她誦讀圣經(《阿格尼斯?格雷》);卡羅琳在花園的玫瑰樹旁踏上墻邊一塊曾作為十字架底座的石雕斷片,從那里,“她打墻頭望出去,眼前是一片寂靜的田野”[7](677)。正是在這芬芳吐艷的玫瑰樹旁,卡羅琳得到了愛情的誓言,也是在十字架的基石旁,她興致勃勃的構想著自己將為社會福利獻出的綿薄之力。這些花園中的女子并不滿足于與世隔絕、安逸悠閑的家庭生活,也不僅僅為愛情理想的實現歡欣雀躍,她們總是把目光投向花園以外的生活場景,與此同時,也把無私的關懷和無償的寬恕投向世人的苦難和來自外界的傷害。
其次,基督教的愛同樣給予人們高度自律的精神,使他們在自己身上尋求上帝的榮光
這種完善自我的理想作用于花園場景中,構成其趨向完善的特質。與維多利亞時代崇尚優雅穩健的社會風潮相輔相成,女性小說的花園是雅致整潔的,花園中的女孩子也常常成為使其特質得以維持的護花使者。露西說“我使自己成了生長在密密叢叢灌木叢中的一種淡而無色花朵的園丁;我掃除了遠處塞滿一把粗木椅上的去年秋天的殘枝枯葉”[8](134)。在男性小說中,花園的艷麗多姿常與女子的輕盈美麗交相輝映,而女性小說里,花園的潔凈則與女孩子靈魂的純潔相得益彰。女主角為花園的完美付出的不懈努力實際上正是她們對自身心靈完善性的孜孜以求。所以在現實中,露西清掃著花園中的殘枝敗葉,在內心里,她也克制著浮躁自私的情緒。
同時,花園的非完美狀態也暗示出園中的女子道德行為的瑕疵和心靈的陰影。在《南方與北方》里,瑪格麗特曾為保護哥哥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對警察撒謊,此后,這個謊言一直使她備受困擾。當她重訪魂牽夢縈的南方老家時,眼前的花園已非纖塵不染的舊時景象,喧鬧、混亂是花園今日的情景,也暗合瑪格麗特備受煎熬的心境。外部世界與內心世界的改變都令她黯然神傷又深受觸動,于是她向貝克先生坦白了良心上的罪過,這時,往日的寧靜翻然歸來。告別故園的時候,她發現“整個地方又充滿了從前那種迷人的氣氛……陽光這么燦爛,生活這么寧靜,這么充滿了夢一般令人快樂的情趣”[2](651),而在內心里,她也“忠心祈求自己能有力量獨自昂首泰然地面對上帝,從此永遠只說真話,不作假事”[2](668)。可以說,女作家對完美花園的追求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她們對宗教道德的堅持。
第三,花園因為具有趨于完善的特質,那么,在這一趨向完善的過程中,它又是富于變化的
戴維?洛奇指出,所有小說都可視為成長小說。蕓蕓眾生,平凡也好,杰出也罷,都難免會像漂泊了千百年的希伯來民族那樣,經過曠野的歷練才能達到應許之地。從愚鈍到睿智,從稚嫩到成熟,不是一段平坦和短暫的旅程,而心靈的天堂狀態(heavenly state)也并非與生俱來,它必然經過人世的起承轉合方能日臻完善。與其相應,女作家筆下的花園也不是恒久美麗的,從荒蕪到繁盛,花園的變化往往與女主角信仰的成長息息相關。
例如,在小說《簡?愛》里,簡?愛的生命是一連串“離開”與“停留”的歷程,其中貫穿著對愛的追尋,她的每一次離開都是因為愛的缺失,而在每一個棲身之所,她都會對愛的內涵有更多的認知。小說中的花園便記錄著這種精神的成長。年幼的簡不能容忍絲毫歧視,像異教徒一樣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她奉行的準則,所以,初到勞渥德學校時,那里的花園是蕭瑟荒涼的。海倫的虔誠善良使簡狂暴的靈魂有所感悟,花園也呈現出清新爽朗的春日景象。在桑菲爾德,當羅切斯特站在簡和各種宗教思想之間,當愛情幾乎成為她“進天堂的希望”時,花園中那株被閃電擊倒的老橡樹卻似乎在暗示遺忘上帝的律法將會遭到何樣的懲罰。只有在簡摒棄了以自我為中心的盲目愛情之后,只有羅切斯特誠心懺悔之后,芬丁的花園才成為賜予他們寧靜生活的樂園。“沒有一個女人比我更加同丈夫親近,更加徹底地成為他的骨中骨,肉中肉”[9](423),此處,出自《圣經?創世紀》的典故暗示出這個曾經得不到愛、渴望愛的小姑娘經過痛苦的歷練,終于懂得了以愛上帝為基礎的最神圣高尚的愛。
綜上所述,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中,不論是嚴肅冷靜的作品,還是浪漫抒情的文字,花園都是人物活動至關重要的場景。男性作家封閉美麗的花園總在提醒我們,一場風花雪月的愛情故事正在拉開帷幕,臺上搬演的永遠是亞當重返伊甸園的渴望,但這份渴望的焦點大多凝聚于樂園中舒適安逸的生活。與之相較,女性作家的花園是開放性、完善性與變化性的整合,它處處暗示出夏娃的智慧:天堂的意義并不僅僅是衣食無憂、兩情相悅,它的真正內涵在于那份與上帝無比親近的神圣感念。
[1]羅斯金.羅斯金散文選[M].沙銘瑤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
[2]蓋斯凱爾夫人.南方與北方[M].主萬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3]Michael Wheeler, Death and Future Life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4]阿薩?勃里格斯.英國社會史[M].陳淑平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5]Michael Waters , The Garden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 Scolar Press , 1988.
[6]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觀[M].蔣慶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
[7]夏洛蒂?勃朗特.謝利[M].曹庸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
[8]夏洛蒂?勃朗特.維萊特[M].謝素臺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9]夏洛蒂?勃朗特.簡?愛[M].祝慶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