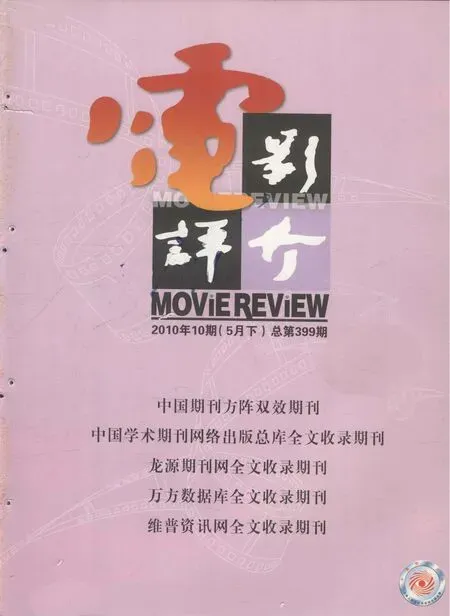新中國17年(1949-1966):紀錄片美學形態及特征
法國19世紀文藝理論家丹納在其《藝術哲學》中曾這樣闡述:文學藝術的產生和發展需要以一定的客觀現實為基礎。植物生長需要“自然氣候”——溫度、濕度;文學藝術的發展需要“精神氣候”——種族、地域和社會;“精神文明的產物和動植物界的產物一樣,只能用各自的環境來解釋。”而這里的“精神氣候”和“環境”,主要是指社會背景和時代特征。時代對藝術最大的影響就是社會觀念,也就是思想意蘊的開掘。
紀錄片是電影發展的初始形態,紀錄片以記錄不可復現的時間流程而顯示出特殊價值,它猶如時代的多棱鏡與社會的萬花筒,在一系列眾多的紀錄片所關照出的特定時代和特定社會的文化精神中,我們總可以觀察到一幅幅社會生活的斑斕圖景,總可以折射出不同時代的風云起伏和滄桑變遷。
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內涵的紀錄片,一定離不開特定的時代精神和時代情緒,離不開社會生活中涌現出來的為人們所普遍關心或感受的矛盾與問題,離不開在觀眾中引起巨大思想沖擊的社會思潮。
新中國17年紀錄片美學形態的發展也與中國的社會變遷這一大背景緊密結合,作為“歷史的立體檔案”和“現實的文獻筆記”,中國紀錄片美學形態發展的自身邏輯也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不斷沖擊,與不同時期的政治氣候緊密關聯,由此,紀錄片的創作觀念也被政治觀念所深刻地改寫。
這正如電影史學家所言:在由多種因素組成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起根本作用的因素是在社會變革與傳統文化影響下的政治文化。中國電影生存與發展的文化環境,如此直接、如此強烈地受到政治的影響。抓住了這點,也就抓住了這一時期電影所處的文化環境的根本特點。[1]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首都北京30萬軍民齊集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盛典。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布典禮開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就位后,樂隊高奏《義勇軍進行曲》,54門禮炮齊鳴28響。在莊嚴雄壯的國歌聲中,毛澤東主席親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毛主席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宣讀了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要求全體指戰員,迅速肅清國民黨軍隊的殘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接著開始了陸、海、空軍的閱兵式。首都北京和已獲解放的廣大城鄉人民,沉浸在翻身解放的喜悅和慶祝勝利的狂歡之中。”[2]來自各制片廠的40余位攝影師奔赴全國各地共同記錄下了迎接這一歷史時刻到來時的壯觀景象,并編輯為紀錄片《新中國的誕生》。
1949年—1966年,新聞紀錄片由戰爭年代的以軍事報道為主,轉為對軍事、政治、經濟情況的全面報道。一九五三年政務院根據形勢的發展,進一步指明新聞紀錄影片的任務、內容和作用。隨后,在中國共產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指引下,影片題材范圍逐步擴大,表現形式更為豐富多彩,但發展的道路是曲折的。由于極“左”路線的干擾,新聞紀錄影片一度出現題材狹窄、形式單調和虛假的現象。中共中央對新聞紀錄影片做出要“更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反映時代歷史特點”的指示,新聞紀錄影片的攝制也在不斷維護其真實性的辨析中發展前行。這一時期出產的紀錄片共計有長紀錄片239部1506本,短紀錄片2007部3632本,新聞期刊片3528本,其中也有一些思想性與藝術性都較好的影片。[3]這些影片和著時代前進的步伐記錄下了新中國前進中的發展和變革。
一、新中國十七年紀錄片美學形態及其特征分析
有一首民歌說得好:
“什么藤結什么瓜,/什么樹開什么花,/什么時代唱什么歌,/什么階級說什么話。”這也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4]
1、以形象化政論為基本特征。這一時期的新聞紀錄片直接接受了列寧對紀錄片的指示(定義):“這種新聞片要具有適當的形象,就是說它應該是形象化的政論,而其精神應該符合我們優秀蘇維埃報紙所遵循的路線”。由于受前蘇聯電影創作觀念的影響,“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成為當時的創作宗旨。紀錄片創作者們十分注重政治氣氛和時代脈搏的把握,以及典型環境(即,時代環境和人物生活的具體環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注重新聞性和時效性,強調作品的時代特征。由于“17年”我國政治上的封閉,造成沒有機會學習國外優秀影片,加之,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使得不少創作者 “不求藝術有功,但求政治無過”,致使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不能得到很好地發揮,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斗爭、陰暗面都不敢在影片中有所反映。
這樣,“17年”紀錄片所表現的主要內容就當然是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所要求的內容,它承擔著文以載道的使命。革命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成為紀錄片塑造人物的美學追求。典型性成為紀錄片選擇人物、事件及塑造人物的標準。“紀錄片靠選擇典型事件和典型環境,拍攝典型人物的行動來表現生活。”[5]
新中國十七年紀錄片,踏著時代的脈搏,記錄了一個“意氣風發”歲月里人們的所思所想。這一時期,經過土地改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使得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使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社會階級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作為“手拿攝影機的布爾什維克記者”,攝影師們“以飽滿的工作熱情,投入到火熱的現實生活中,投入到斗爭最緊張的地方,記錄了時代的風云,社會的變革,記錄了新事物的出現,新人物的成長……”它給我們留下了一份鮮活珍貴的影像資料,同時在對其藝術形式的探索中,紀錄片創作也走過了一條曲折的發展之路。
2、值得總結的經驗及存在的問題:
(1)值得總結的經驗:
新中國“17年”紀錄片藝術形態的發展曾形成過兩次高潮,其經驗是值得總結的:
其一,是領導重視,有“雙百方針”的指引,有周總理的關懷。為藝術家們提供了創作空間。其二,是藝術的民主性。使得藝術發展和藝術上的民主緊密聯系在一起。其三,是尊重藝術規律。開展了對紀錄片藝術規律的二次學術討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紀錄片制作手法的把握,使得題材范圍有所擴大,風格樣式開始出現多樣化。
這一時期拍攝的紀錄片有對抗美援朝的記錄,如:《抗美援朝》(第一、二部)、《反對細菌戰》、《英雄贊》(1956年)、《交換病傷戰俘》等。有對國家政治生活大事的記錄,如:《偉大的土地改革》(1954年上映的長紀錄片)、《煙花女兒翻身記》、《踏上生路》。有對國家經濟發展情況的記錄,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國民族大團結》;還有新影廠創作的紀錄片《新聞簡報》、《百萬農奴站起來》、《歡騰的西藏》、《征服世界最高峰》、《正義的審判》、《人道的寬待》等,以及記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建設的影片,如:《鞍鋼在建設中》、《第一輛汽車》、《長江大橋》等,以及《亞非會議》(1959年拍攝)、《祝賀》、《劉少奇主席訪問朝鮮》、《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還有八一廠(1952年建廠設有紀錄片創作室)拍攝的較有影響的紀錄片,如:《戰勝怒江天險》、《通向拉薩的幸福道路》、《移山填海》、《英雄戰勝北大荒》、《綠色的原野》、《軍墾戰歌》、《灤水情》《戰勝洪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第二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5年攝制完成)等等,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生活及發展建設情況。
“17年”中曾創作出過一批富有藝術魅力、具有時代特征、人物性格鮮明生動的紀錄片。
(2)存在的問題:
這一時期的紀錄片,其風格樣式仍以新聞報道和政論形式為主,強調影片的政治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功能。由于還沒有把新聞片、紀錄片等從藝術手法上進行嚴格的區分,因此,許多影片仍是主題先行,即按照創作者的主觀意圖,有選擇地拍攝素材“唯我所用”,在剪輯中運用“蒙太奇”手法,強調解說詞的引導功能和畫面的歷史見證價值,起著宣傳片的作用。
這樣的紀錄片,在藝術手法的表現上,長鏡頭的運用較少,蒙太奇的運用較多。由于蒙太奇講究鏡頭與鏡頭之間的組接給觀眾帶來的感受,注意鏡頭的運用和表現,從而有強烈灌輸的意識。但從理論上來說,長鏡頭的客觀“再現”性,能更好地達到寫實的目的,尊重記錄的真實;蒙太奇以主觀地“表現”為主,達到寫意的目的。長鏡頭側重于讓觀眾自己去看、去思考去想象;蒙太奇則帶有強制的性質,以便灌輸。如常有這樣一類的鏡頭:人民翻身解放了,后面出現藍天白云等釋義性鏡頭。用鏡頭組接的力量來達到灌輸的目的。蘇聯的表現性蒙太奇理論,恰好適應于政治的宣傳教育要求,成為歌頌時代主旋律理想的創作方法,但無論注重“再現”還是“表現”,這一時期的紀錄片都承載著教化的功能。只是不同的片子在主觀性的尺度把握上,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對于“17年”的不少紀錄片中存在著虛假、說教、拔高、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有學者對這一時期的電影現象曾做過這樣的分析,主要原因是[6]:1、“電影直接為政治服務”,這使得許多影片無可避免地重犯了“直、露、多、粗”的毛病,為了讓影片中的人物去服務于政治,不得不淹沒了人物個性。特別是大躍進時代拍的大部分影片,幾乎都是直接為政治需要而拍攝的應景片,缺乏藝術生命力。2、“沒有深入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僅從宏觀的角度來看,“17年”影片在表現時代、表現時代精神、表現重大題材方面,積累了一套創作經驗;但從微觀的角度來看,這些影片無法把筆觸深入到各種人物的內心世界,特別是在展示復雜人物的內心世界方面都很欠缺,更談不上去挖掘人性,唯恐被扣上“人性論”的帽子。3、“很少借鑒外國電影的藝術成就”,由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應“是一種真實表現生活的歷史的開放的體系”,[7]但那時中國卻在反修的口號下,一味模仿四十年代后期早已陷入教條主義泥潭的前蘇聯電影(內容已變得蒼白,虛假,藝術形象已完全被社會學公式所代替),而繼續堅持著這套“形象化政論”的創作模式,很少學習并借鑒當代外國電影中許多好的藝術手法和成功的經驗。4、“對電影本體的研究基本沒有展開”。
二、政治因素對紀錄片創作的影響
縱覽“17年”的中國紀錄片畫廊,在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和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新聞紀錄片報道了新中國各方面的發展和成就,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和社會價值。
隨著1956年“雙百方針”的提出,紀錄片的題材范圍一度擴大,出現了多種風格樣式。曾出現了紀錄片創作的一段高潮,雖仍以反映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為主要內容,在表現形式上,仍以新聞報道和政論為主,但已開始有了反映人物、名勝古跡、自然風光、文物、手工藝等多方面內容的影片,以及人物傳記片,批評性影片和散文式,抒情式影片等。
但由于1957年“反右”斗爭擴大化,電影戰線開展“拔白旗”,這使得曾經展開的關于“形象化的政論”是否能概括了新聞紀錄電影的特性;新聞紀錄電影不應只是“報紙的兄弟”,還應是“藝術的姐妹”;紀錄片與現實生活與藝術與政治的關系;紀錄片的社會功能以及如何更好地表現社會生活;如何拓展多種風格、樣式的紀錄片等等理論問題,由于“左”的干擾,不能展開爭鳴,影響了創作的發展,從而也帶來了題材面狹窄、表現一般化、只求數量不求質量的惡果。
1958年,在“左傾”思想的進一步干擾下,整個社會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現象越來越嚴重,這在當時拍攝的新聞紀錄片中都有所反映。同時,這些浮夸、虛假的報道也對當時“左”的風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結束語
紀錄片在我國的發展初期曾受到前蘇聯“形象化政論”的影響。使得蘇聯人大開大合的蒙太奇的創作手法,被運用在了很多的作品中。新中國“17年”,雖然對這種“形象化政論”的不同風格及其表現形式有過不同程度的嘗試并進行了一些有效的探索,但由于當時高昂的政治氣氛,使得這種探索也僅僅停留在紀錄片作為“工具”的屬性上。
“17年”紀錄片美學形態及其特征的發展,如同一只在大海里航行的船,經常遇到風浪的襲擊,但它還是在曲折中,從各個角度記錄下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由于這一時期,政治導向與社會背景對紀錄片所呈現出的形態特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使得這種主流意識形態的紀錄片,雖然記錄了時代,記錄了時代精神,記錄了“典型人物”,但卻忽略了對電影美學特質更為重要的在探索個人命運和精神世界方面的表現、追求。從而使這一時期的紀錄片創作更多地呈現出“形象化政論”的美學特征。
注釋
[1]孟犁野:《電影藝術》,1993年第6期33頁
[2]靳德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河南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3頁
[3]《當代中國電影》(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五編,第35頁
[4]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載《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675頁
[5]《紀錄新的時代》,中國電影出版社,1966年4月第1版,第24頁
[6]舒曉鳴:《中國電影藝術史教程1949—1999》,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37—139頁
[7]《蘇聯現實主義問題討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