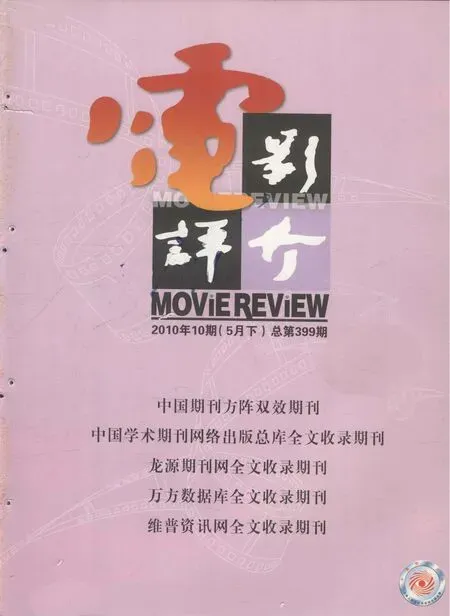片段之美與記憶之美——阿侖?雷乃的電影創作
四川教育學院 林 潔
片段之美與記憶之美
——阿侖?雷乃的電影創作
四川教育學院 林 潔
作為法國“左岸派”電影的代表人物,阿侖?雷乃總以其獨特的探索精神推動著法國電影的發展,貫穿在影片的代表性元素始終是生命的遺忘與記憶、交織的過去與現在、偶然的相遇與表象的神秘。
阿侖 ? 雷乃 遺忘 記憶 過去 現在
一位導演,貫穿他影片的代表性元素始終是生命的遺忘與記憶、交織的過去與現在、偶然的相遇與表象的神秘,那反過來思考,他的影片該有怎樣一種電影語法?哪種語法才能更為精準地表現上述主題?“打亂電影文法的作品”這一評論用于一部電影之中,無論給予的是肯定還是否定,其本身已經指出了導演創新了電影手法,同時也指出了影片的獨有風格。作為法國“左岸派”電影的代表人物,阿侖?雷乃總以其獨特的探索精神推動著法國電影的發展,而探索與獨創本身,便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塞納河左岸獨樹一幟的風格還不足以使阿侖?雷乃的名字輝煌世界影壇,更為重要的是他能以藝術的方式來表現他所關注的內心記憶、戰爭和政治主題,而這一表現方式始終會以一種撞擊觀眾內心深處的影象風格展現,雷乃對電影技法高超的掌控能力使觀眾以一種回顧的方式進入內心或歷史最隱秘的地方反思,片段牽動整個思維,在個人的命運中映射特定歷史事件,由此引發的思考指向的是未來,于是,所有的思考貫穿歷史與未來,點滴的、個體的又是宏大的、人類的,形成了接收者意識中回憶與思索的貫穿性,這一貫穿性恰恰與雷乃的影片流動過程不謀而合。
阿侖?雷乃的魅力在于善于用獨特的思維和視點來觀察世界,他的作品中沒有接受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超現實主義等等任何一種引領現代藝術的現代哲學思潮,而是合乎規律地具有意識形態的虛無主義成分。這在現代藝術中,是一并不少見的現象。阿爾貝?加繆曾就此點論證說:“由于現代藝術是虛無主義的,所以它始終在形式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掙扎。”不同的是雷乃的虛無主義成分沒有頹廢元素,而帶有明顯的積極傾向,那是一種藝術探索的積極,帶入藝術作品中便是探索純粹的藝術,探索藝術本身,“以便通過藝術和借助藝術在藝術自身創作過程中提煉一定的哲理、一定的哲學——美學觀念和一定的政治——意識形態觀念,這是不足為怪的。”[1]藝術本身表現世界觀,這在藝術之鄉法國傳統的藝術界諸如文學、美術等領域有著不少成功的嘗試。
一、微妙的和諧
現代藝術的一種表現便是將內在精神物化為形式的過程,雷乃善于把他所關注的內心記憶、戰爭和政治主題放入藝術的純粹形式中加以表現,使這些主題的影片具有一種詩意的,更有沖擊力的新的反映世界的角度,它通過藝術審美貼近人的靈魂深處。這樣便可以理解,為什么雷乃為這一純粹藝術化的創作所做的探索而嘗試的題材會是由最具有豐富造型表現手段的視覺藝術——繪畫——開始的了。
美術片是二戰期間起源于意大利的一種片種,在藝術家眾多的法國得到進一步發展,而雷乃的影響及成就最大。繼第一部成功短片《梵高》(1948年)之后,緊接著又是與繪畫有關的《高更》(1949)、《格爾尼卡》(1950)、《雕像也在死亡》(1950)。一個導演如此執著地在影片中詮釋繪畫題材,無疑是在追求藝術形式中截然不同的形式感和微妙的和諧,阿侖?雷乃以這種方式追求現代電影與現代繪畫思想的和諧,藝術的魅力也許正是在融合不同的美感,以求得最大程度的感染力與震撼力。在形式與內容完美結合這一點上,表現梵高、高更、畢加索、非洲藝術是雷乃與畫家創作意識的共鳴,如畫作本身,這是藝術家世界觀的表達。這些影片中所表達的雷乃的思想關注也正一直貫穿他一生的影片創作。這些特有的視覺元素與主題思想正是雷乃影片固有風格的早期征兆。
早期大量的短片拍攝是阿侖?雷乃訓練自己蒙太奇剪輯和場面調度的一種方法,《梵高》是他早期記錄電影的代表作。影片通過記錄梵高的繪畫作品記錄了梵高的一生,通過分析純藝術現象,使影片具有著震撼人心的藝術價值。梵高、高更、畢加索以及20世紀現代派繪畫大多數流派從不隱藏繪畫的筆觸,這一形式已完全屏棄精雕細鑿的寫實表現手法,使繪畫過程——筆觸表現——的價值得以實現。這無疑與雷乃的影片風格極為相似。安德烈?巴贊的“長鏡頭”美學思想對“新浪潮”有著重要影響,雷乃卻采用大量的時空跳接:凌亂無序的視覺表現,不同時間發生的事交叉閃回,現實與想象、夢魘交錯——精確的透視法則已不能滿足人們表達世界的欲望,如實的現實描摹更與另一種真實毫不相干,混雜的異質的甚至可以是粗糙的表現也許才是再現內心現實主義的更好方式。梵高在他強勁的筆觸和高純度色彩中表現處于悲慘生活中的人對生命的熱愛和自然界的深切歡樂;畢加索使用粗獷凌亂散漫的造型在《格爾尼卡》中憤怒聲討法西斯暴行;雷乃在閃回與片段表現的蒙太奇中闡釋他永遠的內心主題。片段——不同于傳統的“總體結構”,是人們的另一種全新的空間知覺,從片段入手,從局部入手,細節的敏感正與人們掌握信息和運用信息的過程相吻合。人的信息掌握過程是片段性的積累,信息的運用也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個別元素便可能將零散的信息貫穿起來,藝術家規劃各個元素,隱含性地揭示主題,接收者在這些信息中感知各種元素可能隱含的意義。
二、視聽的形式
雷乃在創造著形式與風格,同時雷乃似的形式與風格也是雷乃影片的生命。
注重對藝術的純粹形式和非理性的追求,敘事結構上往往采用內心獨白、思維變奏與內心程式等敘事結構。影片的多敘事層面構成濃密的復調元素,各元素如同纖維交織,看不出明顯經緯脈絡,卻嚴密地織成一個整體。由此在時空處理上看起來更為自由隨意,卻是遵循著另一種嚴密:在表象的隨意之下精心嚴密地刻畫內心,傳達情緒。他并不著力記錄客觀真實,也不關注冷靜公正的記錄,而是要傳達人物內心的主觀思索,探詢另一層面的主觀真實。阿侖?雷乃就是這樣“打亂了電影文法”。
(一)視覺空間
構圖與燈光是導演作品風格最為直觀的視覺體現。雷乃是一個高度依賴視覺形象表達的導演,他總以較為膨脹的方式結構畫面(有時甚至接近于英格瑪?伯格曼的逼視鏡頭),膨脹至景框邊緣給予一個突然的斷裂,有時還運用長時間充滿景框的抽象的局部畫面,由此帶來的無限張力反映導演厚重的思考。與諸多現代電影不同的是,雷乃在故事片的光線的運用上沒有刻意追求光線的積極與跳躍,而是采用不帶主觀意味的自然光,柔和的現實主義的灰色調泛出溫和的詩意氣氛。在記錄片《格爾尼卡》里,雷乃采用大量特寫鏡頭再現畢加索的名畫,將畫作以動態的、具有時間維度的方式記錄。畢加索的《格爾尼卡》是一幅采用凌亂的視覺效果和粗糙的造型再現1937年法西斯對西班牙小鎮格爾尼卡的野蠻轟炸行徑的壁畫,雷乃采用活動的方式分割壁畫為若干小的部分,再逐塊加以片段研究,重新組合(雷乃化整為零再以各種方式對片段加以組合的電影技法也許就來源于此),強烈的構圖忠實了畢加索原畫的畫面藝術表達,用電影化的手法將靜態的壁畫注入動態效果,帶給觀眾的是繪畫藝術與電影藝術的雙重感受和沖擊。構圖上最具形式感的影片《去年在馬里昂巴》是雷乃的代表作,這部影片里空間畫面的處理更為個人化、內心化、情緒化。很多時候的畫面似乎是一幅靜態的照片,僵硬并呆滯而遙遠清冷的畫面帶給觀眾間離感,間離感也同樣屬于片中主角的內心世界。
(二)間斷結構的縫合
雷乃嫻熟的蒙太奇技法在《梵高》、《高更》、《格爾尼卡》、《雕像也在死亡》、《夜與霧》、《對世界的全部記憶》、《笨乙烯之歌》等短片中可見一斑。《夜與霧》采用照片、資料片將黑白的,彩色的,過去的,現在的納粹集中營的資料交叉剪輯,惟有這一回顧剪輯方式有效地營造了集中營極其恐怖的氣氛。雷乃用極為現代化的剪輯手法來安排影片的結構。在《廣島之戀》、《戰爭結束了》、《去年在馬里昂巴》等影片中,雷乃將他的剪輯技巧用到了完美無缺的程度。跳接、閃回,意想不到的切入鏡頭將影片的外在節奏和表象時空結構得無比精致,對人類精神領域的探索與挖掘就在獨特的剪輯節奏中以迥異于傳統的線形敘事結構的方式中展現出來。
(三)攝影機的自在世界
在雷乃的影片中,攝影機是決不會沉默的。無論是作為記錄片的《格爾尼卡》和《夜與霧》,還是作為故事片的《廣島之戀》、《戰爭結束了》、《去年在馬里昂巴》,雷乃喜歡不停移動攝影機,在畫框內外建構劇情,使攝影機的運動有著不可缺少的敘事功能。鏡頭的移動記錄了法國國家圖書館里漂亮的巴洛克建筑(《對世界的全部記憶》);特寫,移動和變焦鏡頭賦靜態的油畫于動態感受(《梵高》、《高更》、《格爾尼卡》);靜止的過去與流動的現在帶給觀眾回顧的陣痛和對未來的深切思考(《夜與霧》)。伊芙特?皮洛認為,當各種不同的運動形式可以靠自身表現力探索意義的時候,運用空間的真正自由和空間結構表達思維的能力便告成熟。《去年在馬里昂巴》中,攝影機的敘事功能運用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攝影機的移動創造了獨立的攝影機世界,撲朔迷離。影片的開頭,就似乎是攝影機的對空間環境從無到有的創建。攝影機在一座空曠豪華的旅館夢幻般緩緩游移,細致地觀察精巧華貴的室內裝飾,地板,走廊,天花板的鋪設,房間的布置,移過飄忽的迷宮,當出現人物時,人物幾乎完全靜止,同時攝影機繼續優雅緩慢移動,整個過程似乎在欣賞,又象在尋找著什么;相伴這一切畫面的,是與攝影機移動節奏同樣緩慢的畫外音:
“又一次……在這長長的走廊中,又一次,我向前走著……在另一個世紀的建筑物中,在豪華的、巨大的、巴洛克似的旅館中,走廊接著走廊,看不到盡頭……我又一次向前走著……”
攝影機沉著緩慢的移動占據著影片的絕大部分,如同一個優雅冷峻的觀察者與思索者。類似的,影片《斯塔維斯基》中攝影機對一幢建筑物的描寫還可以找到《去年在馬里昂巴》的影子。
(四)聲音
對白在雷乃的影片中并不多見,總帶以簡短而不明確的模糊特征。畫外音是用得較多的形式。R?波布克認為畫外音起著復雜的作用,提供聲畫一致和聲畫對位的情緒價值。《去年在馬里昂巴》可以說是一部以攝影機和聲音共同構建的影片,聲音在抽象和具體之間展開,聲音的延展過程就是一說服過程,說服的結束就是電影的結束。影片多處采用非現實的聲畫對位法,用聲音和畫面清晰構建出兩條線索,即在現實的今天講述去年在馬里昂巴發生的事,使影片呈現出分別以聲音和畫面組成的多聲部。聲音在本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旅館水池邊,男子告訴女子,去年曾相會并承諾過一年后再次重逢一起出走,女子并不相信此事,然而在這之后男子在不同場合不同地點反復地對她講述去年在馬里昂巴約會的每一細節,當男子講述這些細節時,講述的聲音清晰無比,細節描述得如同當時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給女子甚至是觀眾勾勒出一次清晰的馬里昂巴之約,與講述的聲音對位的畫面卻僵硬并符號化。究竟眼前的現實是夢幻還是對女子來說夢境般的“去年在馬里昂巴”之約是夢幻?音響和畫面的矛盾突出了影片的矛盾與離奇效果。《廣島之戀》開頭部分,解說記錄片畫面聲音的是情人之間的對白。音樂的節奏,含義豐富的詩意的對白,流動的影象,流暢的移動攝影,牽引著觀眾的觀看欲望,同時以抒情化的形式替代了記錄片解說的說教意味,戰爭的悲劇強烈撞擊觀眾的內心。需要指出,音樂常常配合著雷乃慣用的移動攝影,化入化出的畫面,在多部影片中起著不可替代的情感塑造作用,這似乎已成為“雷乃式蜂窩餅”的基本特征。
伊芙特?皮洛在《世俗神話》一書中說道:“電影語言獲得新的能力,……它正在尋求一種獨特的最有效的平衡,……這是電影敢于打破常規之處。實際上,只有當一種語言完全確立,并且成為允許各種變體存在的系統的時候,個人的慣用法和偏離常規的表達式才能存在。眾所周知,新的信息來源于否定常規的出人預料的事物。” 阿侖?雷乃的電影語言便是這樣一個系統,它帶著誘人的成熟之光,盡管雷乃本人認為他的某些分析思維復雜性的影片暫時還粗淺和幼稚,盡管也曾被視為“語言學”怪癖,然而他與同時代的電影大師一樣,將電影本體美學推向了一個至高點,他所開拓的全新風格成為電影研究上現代電影永恒的范例,最重要的資源;其局部藝術經驗出現于各種類型甚至是商業影片的運用里。
三、生命的遺忘與記憶——永恒的母題
普魯斯特將記憶分為兩種:有意識的記憶和無意識的記憶。有意識的記憶存在意識之內,有刻意記憶的成分,無意識的記憶是在人的思維中很常見的感知知覺,偶然的或者非常次要的也許是不相關的信息常常引起整個的,重要的,一連串的聯想記憶。普魯斯特的記憶理論可以用來解釋雷乃使用“怪癖”的電影語言描寫內心世界的原因。
遺忘總在復活,記憶總與未來相通。很多時候,所謂忘記并不是真正的忘記,深藏的記憶總免不了在某一剎那被當前的某個事件、某種感覺忽然喚醒,這一喚醒還會指向或遠或近的未來。《廣島之戀》,在日本的真愛復活了記憶,不同的城市,相同的戰爭陰影,相同的愛情,主人公在逃避什么?《夜與霧》,被認為是最獨特的戰爭題材記錄片,是對戰爭最負責任的思考。影片的內容與形式同樣都是在對生命的遺忘與記憶這一情緒的強調中展開,從這個角度描寫,才能最深層地從每個人內心喚起對戰爭的反思。納粹的集中營曾經只是一塊普通的土地,后來它隔離了來自阿姆斯特丹、波蘭或其他什么地方的“劣等人”,今天,它已經破敗,“往昔犯人們走過的地方,種子已經長成植物(解說詞)”,未來,是未知,還等著書寫,寫下的內容會帶著反思后的痕跡嗎?《夜與霧》中的反思而不是指責和道德評判基調,是二戰后長久的眾多的戰爭題材記錄片中最為獨特的一點,反思,審視記憶中的過去應該遠比指責更有現實意義吧,這是雷乃作為電影導演對那段歷史,對人類的特殊貢獻。優雅的《去年在馬里昂巴》更是將記憶與遺忘探討得出神入化。《我愛你,我愛你》的科幻時空、《戰爭結束》的未來推測、《穆里埃爾》的冷漠時序……似乎存在一種力量使雷乃在他的一部又一部影片中著迷地對時間進行描寫,對記憶進行深層思考。
保持記憶就是保有良知,忘記是對記憶的否定,對現在的背叛。有記者問:“有人說,您是生活在記憶中的導演,您是否感到不快樂?”雷乃回答:“這適合所有的人,我不喜歡記憶這個概念,對我來說,未來也是記憶的一部分。”雷乃以記憶注視未來,以形式創新電影美學,盡管他的電影創作已歸于沉寂,然而電影史上留有雷乃影片重要的一筆;藝術家不能是謊言的傳播者,在題材涉及政治與戰爭時,雷乃的藝術良知與藝術心靈一樣,在電影史上同樣有著不可替代的位置。
[1] 康多爾戈夫.《異化的記憶與忘卻》.《世界電影》.1992年5期
[2]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3]雅克?奧蒙、米歇爾?馬利.《當代電影分析》.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伊芙特?皮洛.《世俗神話——電影的野性思維》.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年版
[5]鮑桑葵.《美學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6]《世界電影》.1992年5期
[7]《我的電影觀念和我的創作》.阿侖?羅伯—格里葉著.卞卜譯
林潔,四川教育學院美術系講師。
10.3969/j.issn.1002-6916.2010.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