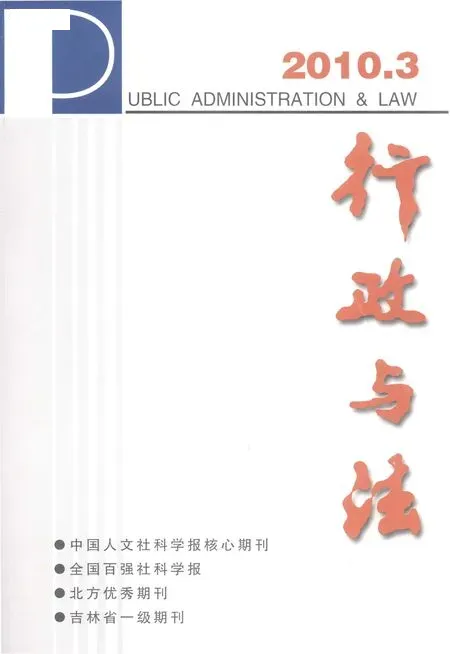金融危機背景下政府投資法價值取向初探
□ 孫 放
(上海政法學院,上海 201701)
金融危機背景下政府投資法價值取向初探
□ 孫 放
(上海政法學院,上海 201701)
面對我國政府投資的社會現實,透析復雜自適應性社會系統基礎可以發現,政府投資在我國所扮演的角色已遠遠超出公共物品提供及國民經濟發展 “引動水”的角色。本文探討了政府投資角色多元與社會多層次效用期待背景下的法律應然價值取向,提出了在公共利益價值取向指引下的可量化價值標準。
政府投資;復雜自適應系統;法律規制;價值取向
一、政府投資法的需求與目標
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給人類提供了更新知識、革新制度的良好機遇,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考切入點。回顧金融危機歷程,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此次危機中“贏得敬意”,[1]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政府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出4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及相關一攬子措施 (具體計劃為從2008年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政府擬新增投資1.18萬億元,加上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共約4萬億元),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穩步增長。從經濟學角度看,中國政府的投資效果如何,可能需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檢驗才能知道。但本文的關注點是法學,金融危機類似一個“放大鏡”,它放大了政府投資的法治化需求。我國政府投資面對金融危機的考驗是在傳統的“誰來投”、“用什么投”、“投向哪兒”和“怎么投怎么管”等理論及實踐方面的困擾,金融危機背景下的政府投資又恐怕會因投資的“短期非常態大量額外”供給而被盲目利用,造成“為投資而投資”。其中,重復建設、環境壓力、濫權、尋租等不良社會后果都有可能出現,從而付出 “無法可依”的政府投資行為的社會成本代價。所以,在特定背景下,筆者就政府投資的老問題與新需求在法制層面予以探討。
我國政府投資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建國初,對于政府投資我們需要進行理論上的梳理、考察、定位、反思與前瞻。政府投資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它要求我們不能再重復在沒有理論支持下進行的政府盲動投資。因為從橫向看,政府投資影響到多種社會目標的實現;從縱向看,政府投資又有代際間深遠的歷史意義。對政府投資的社會期待是既能夠增加公眾受益的公共服務數量,也能夠提高公眾受益的公共服務質量,但社會現實是流向自利性項目的資金從總體上降低了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益。政府是有限理性且信息不充分的,政府所提供的投資與所達成的公共服務效益往往是有限的。在沒有一個社會最優方案的前提下,政府投資可以說是一個選項方案。不可否認,政府投資體制在某種程度上鑄就了“中國的奇跡”。因此,我們現在面對的不是應不應該由政府投資的問題,而是如何規范從而引導其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當政府投資時,它應作為一個經濟實體,與社會上存在的經濟實體一樣參與同一個市場,與其他實體遵循相同的游戲規則。所不同的是,政府投資摔倒了可以“重來”;而其他實體在投資失敗后可能會傾家蕩產,殘酷的市場不會再給其第二次機會。當然,政府投資失利后可以“重來”的機會并不是市場恩賜的,而是因為政府有著一批忠誠的投資人,即納稅人仍會矢志不渝地無償提供資本金,對政府來講無論這些錢稱為稅收還是財政收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借此“翻盤”。單從經濟上講,政府是“不倒翁”,這是其他投資實體所望塵莫及的。所以,面對政府投資行為,首先它不應是經濟行為、社會行為、政治行為,而應是法制行為。因其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引領、調控等社會效應,我們首先需要將政府投資視作有待法律規范的問題;并且政府投資法律規范的價值定位應超然于政治體制、社會意識形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因為在法價值引導下的政府投資行為應是“穩定可預期的”、“擔當社會責任”的,即無論所處的是何種國家性質、社會意識形態、社會發展階段,也無論政府投資一元錢還是10個億,只要是政府作為主體的投資行為都應在共同價值取向指引下遵循相同的法律原則與法律程序,從而達到可預期的社會價值目標。
通常認為,只要是投資都有風險,都會有失敗的概率發生,何況政府也是有限理性。這正如股票市場投資,股市投資失利,虧損一定會發生,除非是巴菲特。①(美)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投資者”,他自1954年開始從事投資基金業務,至今近60年。當初從籌資10.5萬美元起家至今,他所擔任董事局主席的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已成為美國第一高價股上市公司,2008年3月30日收盤價108990美元/股,總市值近1059億美元。其實巴菲特的投資秘訣僅是因為奉行了 “價值投資理論”,②價值投資理論是指通過對上市公司內在價值的研究分析,然后比較證券市場價格,以此來決定股票買賣策略的一種投資理論。并在60年中按照鐵的投資紀律操作。首先,巴菲特的不敗紀錄告訴我們,在投資領域理論指導實踐的重要性并且可以彰顯出效益。我們的政府投資可能也存在類似的可以彰顯出效益的理論,只是我們還沒有認知。否則,我國不會在建國60年來主要的40份政府工作報告中,認定“盲目投資”為14次;認定出現“投資過快”8次;認定“重復建設”現象存在3次。③筆者研究了我國1954、1955、1956、1957、1959、1960、1964、1975、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年共40份《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統計得出數據。其次,在證券投資市場中,投資者掌握了投資理論或原則是遠遠不夠的,至關重要的是還要有鐵的紀律。對政府投資而言,法律的作用恰恰就是投資紀律。法律應規范甚至強制政府執行投資理論或原則。任何一次違反都要有人來承擔責任。
二、從“復雜系統”視角認知政府投資的法價值取向
首先,我們需要對政府投資的宏觀對象 “社會系統”④社會系統是指處于特定區域和時期、享有共同文化并以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按照一定的行為規范相互聯系而結成的有機總體。有一個深入的理解,即它具有什么樣的特性?政府投資在這個社會系統中充當什么樣的角色?其次,基于該社會特性,社會系統是否會對政府投資產生反應,產生什么樣的反應?第三,法律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法律扮演角色的價值取向應該是什么?
其實,任何一個經濟主體、企業主體和個人主體在社會生活中幾乎從來不可能是封閉的、自我發展的,至少是不可能完全任其發展的。在社會經濟系統中,這些主體都是通過相互適應和相互競爭而經常性地自組織和再組織,使自己形成更大結構。在每一個階段,新形成的結構會產生新的突然涌現(Emerge)的行為表現。社會系統,實質上就是一門關于涌現社會效應的科學。美國桑塔費學派將社會系統稱為 “復雜適應性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⑤1984年,一批美國的物理學家、經濟學家和計算機專家成立了桑塔費研究所(the Santa Fe Institute,SFI),提倡跨學科綜合研究方法,通過交叉研究,提出了復雜適應性系統的概念。復雜適應性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中的復雜性是指系統的多層次、多因素性、多變性、各因素或子系統之間以及系統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隨之而來的整體行為和演化;適應性是指系統的成員(Adaptive Agent)能夠與環境和其他主體交互作用,主體在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中不斷學習,積累經驗,并據此改變自身的結構和行為方式,CAS理論的核心思想是適應性造就復雜性。復雜適應性系統理論的提出本質上是對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類社會系統作了一次技術性處理,從而使我們所抽象出來的本質特征在各個層面上有系統地充分展現出來。正如自然科學需要在試驗前對待測樣品作適當的技術處理才能在試驗中最有效地獲得試驗結果一樣,復雜適應性系統的提出使得社會系統的本質特征以一種能被更加充分接觸和理解的方式被深入研究。對于社會生活來說,從一定的視角上看,一個社會的形成其實就是在一個確定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諸多解說相互沖突、磨合、融合的過程,并進而獲得一種關于生活世界的相對確定解說,因此,影響了人們的習慣性行為方式,構成“制度”,形成文化的共同體。[2](p2)在人類社會,這樣的系統包括很多子系統,例如:文化、經濟、法律制度。我們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發現涌現出效果的基本規律從而控制涌現的路徑和社會效應。
在這樣復雜適應性的社會系統中,是一個由許多平行發生作用的“主體”組成的網絡。每一個主體都會發現自己處于一個由自己和其他主體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個系統環境中;每一個主體都不斷地根據其他主體的動向采取行動和改變行動。在內部,主體間的非線性互相作用被稱之為自組織力;在外部,該系統不斷地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的交換,被稱之為他組織力。社會系統也就是自組織力與他組織力相結合的涌現結果。但這個復雜適應性社會系統的控制力又是相當分散的。社會系統所產生的連續一致的行為結果,是產生于作用體之間的相互競爭與合作,如經濟領域正是這種情形。這也是處于金融危機中的社會經濟系統,無論怎樣調整銀行利率、稅收政策和資金供給,經濟的總體效果仍然是千百萬個人的無數日常經濟決策的涌現結果。但因該社會系統絕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系統,且不斷與外界進行能量、物質交換,所以,每個“主體”在環境中會隨著環境的變化不斷強化某些行為。“主體”將自己組織為前后連貫的結構或秩序,從而產生預期的行為表現。這意味著現實世界是社會體系,經濟制度中每個主體都會隨著外部提供的強化力量而存在相同的關聯性。
在這個社會系統里,市場結構就是主體通過對資源、勞動力、貨物和服務等外界的條件需求與交換來自發組織和運轉的。但作為以國家為單位的社會系統又都面臨一個問題,即如果讓主體都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如何獲得整體的利益?在德國,解決這個問題靠的是人人都關注自家窗外的他人。[3](p124)而在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影響下,這恐怕是不能被接受的。我們需要在社會各領域,經濟領域也不例外,存在更有感召力的力量作為不斷提供物質、能量的源頭。正如美國著名學者理查·A·穆斯格雷夫認為的那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一個國家社會經濟增長的初級階段,政府投資在整個國家經濟總投資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以便為社會經濟發展進入“起飛”的中級階段奠定基礎。而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中級階段之后,政府繼續進行公共部門投資,而此時的公共部門投資將逐步成為日益增長的私人部門投資的補充。但在經濟發展的所有階段,隨時都可能出現市場失效問題,并影響社會經濟的有效運行,因此,政府始終要通過公共部門投資的活動,來進行與保持必要的宏觀調節。[4](p228)
政府投資作用的對象是一個開放的、動力的、能夠自適應的并涌現出反應效果的社會系統。它的社會系統定位決定了它的社會系統預期。但因為社會系統又是在外力組織下的各主體相互作用下的涌現結果,所以,把系統解構的理念恐怕不能實現政府投資外力的組織效果。因為就社會經濟領域來看,個體的投資行為代表不同的社會利益團體,實現不同的社會團體利益偏好;但整體利益絕不是個體利益簡單累加之和。甚至在社會系統中,個體利益之和有時小于整體利益。因此,在復雜適應性社會系統的背景要求下,政府投資一定要站在公共整體的角度,絕不能再用“還原論”來指導政府投資的價值定位。整體在社會學中與之相對應的是個體,而在法律主體理論中,整體與公共、個體與私人相對應,從權利論上講是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所以,當我們用社會復雜系統的視角來定位政府的宏觀投資價值時,只有當政府投資作為體現公共利益的驅動器,才能實現社會系統的整體效益涌現。
三、我國政府投資的邏輯前提——“諾斯悖論”的證偽
對于政府“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認識,社會科學領域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North)曾這樣描述國家的兩難處境:“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這一悖論使國家成為經濟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關于長期變遷的分析中,國家模型都將占據重要的一席。”在《新制度經濟學前沿》一書中,諾斯也提到:“事實上,人們對國家無能為力,但與此同時,沒有國家,人們將一事無成。”[5]這就是著名的“諾斯悖論”。“諾斯悖論”提出國家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但國家又會導致很多麻煩。然而,我國卻通過獨特的政策,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身份參與到國民經濟中,通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兩種矛盾對立的體制有機地揉合在一起,更為重要的是,這種 “不協調”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其實,諾斯悖論顯然包含了經濟發展需要國家的基本命題,但它同時反映了政治與經濟的對立,諾斯悖論的預設前提是國家理論,諾斯的國家模型所考察的國家具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國家為獲取收入,以一組服務——諾斯稱之為保護和公正——與 “選民”作“交換”;第二,國家像一個帶有歧視性的壟斷者那樣活動,為使國家收入最大化,它將選民分為各個集團,并為每個集團設計產權;第三,由于同時存在著能提供同樣服務的潛在競爭對手,國家受制于其選民的機會成本。可以看出諾斯所考察的國家是一個統治者,稅收好像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國家沒有什么制度措施來制約政府對收入的過度追求。另外,如何看待國家與政府,經濟學家諾斯的思路是聯系產權來分析國家的。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界定和行使產權最終需要在強制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在經濟學家諾斯的眼中,國家就是“在強制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組織”,它因此處于界定和行使產權的地位。既然國家可視為一種組織,而經濟學家假定人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經濟人”,所以,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不相信國家。
我們看到,諾斯悖論在理論前提中存在缺陷。它的理論基礎是對于國家、政府角色定位和國家所有權的理解,但對上述理解的偏差導致了該理論的不完備。其實,政府投資等一系列政府經濟行為都只是政權的實踐,是國家所有權的行使。其中,政權的性質決定了具體投資行為的實施主旨。國家所有權、全民所有權與各主體所有權的權屬差異,決定了其使用效益的公共化要求與社會價值目標的抉擇,而且上述理念完全可以在立法技術上有所體現。我國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政府的相對獨立經濟行為并不是西方政治學、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制度體現,而是新中國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邏輯的結果。針對諾斯悖論,我們的答案是政府投資或以其他方式參與經濟生活并不是本質上是有限理性的,對它的認知可以因“國”制宜。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投資不能因為資金的所有權不同而令投入到同一市場中的資金附帶不同的權力色彩,即無論各投資主體擔負何種責任或社會期待:引導、救濟、純獲利等,政府投資應作為一個經濟實體,與其他主體一樣參與同一個市場,與其他實體遵循相同的游戲規則。所有權色彩的優勢地位應該被抹殺。所以,在政府投資法的價值取向視角我們要對政府投資進行矯正。即使本著公共利益的宏觀價值取向所從事的政府投資行為,也必須在市場面前褪去所有權色彩的外衣,即褪去所有權背后的權力附帶(包括壟斷地位、信息優勢等),真正做到“權力隔斷”。根據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滿足完全競爭的條件以及一些其他條件的市場能夠導致社會稀缺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針對有政府參與的投資行為,政府資金的多與少、進與退并不直接構成競爭市場的阻礙,而權力配置的平等才是競爭市場的核心。總之,面對不完全競爭、非均衡市場、市場缺位、不希望的市場結果等,政府也不能被期待成為救世主,政府只能是一種選擇,不僅是主體選擇更應是一種制度選擇。
其中,法律制度在對政府投資的社會認知中如何構建,價值取向起著核心作用。法可以有不同的價值目標,這些價值目標不是平行的,需要對這些目標做出選擇,即誰為最高價值,誰為次價值,應當首先選擇誰,當它們相互沖突的時候應使誰服從誰。法律應當實現確定側重于保護和增加哪些價值。[6]前文通過社會系統的視角得出公共整體利益的價值視角,但公共利益作為不確定法律概念本身是非常抽象的、富于彈性和變動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唯有在具體化了的時空中探究具體化了的公共利益的內容才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7]
四、政府投資法價值標準的可量化構建
霍布斯(Hobbes)在《利維坦》(Leviathan,[1651])中表示:“將貨幣輸送給公眾使用的渠道和道路有兩種,一種是送交國庫,另一種是從國庫中重新發放出來作公共支付之用”;“自然人的脈管從身體的各部分接受血液送到心臟,在這里充實生機以后再由心臟經動脈管送出,使各部分充滿活力并能動”;“貨幣在國內人民之間周流傳用,并在傳渡過程中營養各部分。其情況很像國家的血液流通:因為天然的血液也同樣是由土地的產物構成的, 而且在流通過程中一路營養人體的各部分。”[8](p105)至此霍布斯引用威廉·哈維血液循環之原理,將國家比喻為一個“虛構之人”(Artificial Man)。說明國家收入解繳于國庫,已由國庫外放,經過大動脈,使全身各部分活躍, 其功效與血液之循環于人體相似。[9](p225)借用霍布斯的“虛構之人”概念,我們也可得出現代政府投資行為恰恰起著國家心臟的作用,在整個社會系統中猶如“經濟泵”;基于資源有限的社會背景,政府投資是本著一定價值標準的“資源重新分配泵”。法律首先要明確的是開啟這個“泵”時價值目標選擇的傾向性。
從宏觀視角來看,政府投資的法價值取向決定了對社會中存在政府投資與非政府投資的沖突和矛盾如何進行價值判斷。但過于模糊且概括性很強的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能否成為可操作性的價值判斷標準呢?其中,公共是全社會的公共利益還是區域性、地方性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如何客觀體現,具體投資實踐中對什么領域應投入、對什么領域應禁止?面對政府投資,它的實務需求對傳統的價值取向范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不能再囿于務虛的價值取向,可計量、可操作、可借鑒的價值評判標準是政府投資法律制度所急需的。公共利益價值取向此時急需“可操作性概念”,以此來決定政府投資結構的構成。因此,該評判標準不僅指導著政府投資立法而且可以約束政府投資的具體行為決策。在政府投資的啟動環節至退出環節,都應一以貫之并彰顯出其社會現實效益和社會前瞻性。
首先,我們對政府投資行為做一個抽象描述:

其中,A為政府投資;B為市場內的非政府投資人,在不同的市場里它的組成各不相同;C為整個市場的收益,作為宏觀經濟的研究對象,這個收益的含義不同于簡單投資回報,它是表征該市場的發展規模和健康的一個綜合指標;D為社會效益。由公式①可以看出,投資是這樣一個過程:各種投資主體(A和B)參與其中,通過經營活動產生市場效益和社會效益。一般來說,社會效益是一個很難量化的東西。過去的政策制定往往對這種難以量化的指標做了忽略。因此,該方程表現為:

現在看來,這種處理是不合理的。針對各種市場情況,公式應變形為:
⒈只有政府投資參與的市場:

⒉政府投資和非政府投資共同參與的市場:

⒊只有非政府投資人參與的市場:

政府投資所要研究的市場為1類和2類市場。所涉及到的市場形態可以用公式③④來表述。目前,在大部分市場內,這是投資人和市場參與者所看到的或者所理解的二元結構。在二元市場結構中,每一元的經營行為必然與另一元的經營行為有相關性。我們要討論的是如何保證③④的市場形態是健康、良性的。這其中有A參與的市場形態中,A的公共利益價值取向起決定性作用,而且要在社會實現過程中保障公平與效率。其實,所謂公平和效益的矛盾是一種人為的劃分。在這里,筆者首先強調公平,因為如果真正是不公平的立法肯定不會是效用最大化的立法。[10](p103)那么,就政府投資而言,公平既表現為過程的公平 (或者說市場內公平)也表現為結果的公平。過程的公平表現為公式④中A與B之間的公平問題;結果的公平則更多地以社會效益D來評估。也就是說,在公共利益價值目標指引下的政府投資行為,應該既能保障市場內的A與B的市場權力配置公平,又應保障實現社會產出中的社會公平效益。而在“具體化了的時空”中,社會效益的內容包括就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生態環境、國家安全等諸多等待考量的因素。所以,每一項政府投資行為都應該在實現市場效益C的同時,用衡量社會效益產出D來具體體現政府投資的價值目標。這其中社會效益D的目標選擇是關鍵問題。
例如:面對金融危機的大背景,我國政府提出的“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但因經濟增長并不必然帶來就業的同步擴大,甚至可能產生增長與就業目標的矛盾,所以,導致目前中國經濟存在 “無就業復蘇”的危險。針對此問題,2009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提出三個模擬方案,用投入產出的方法來模擬投資與就業的關系。第一種方案,按照過去的投資方法,重視對固定資產的投資從而進行產業投資分配。“4萬億”投資完成以后,可拉動非農產業就業4482萬人,相當于2008年全部非農就業的9.6%。第二種方案,計劃分配的方案。按照現在我國發展改革委員會公布的對不同行業的投資結構安排,可拉動非農產業就業5135萬人,相當于2008年全部非農就業的11.0%。第三種方案,本著就業優先原則。充分考慮到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產業拉動就業的效果之間的差別,再進行投資分配。其中,給予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服務業最高的就業拉動系數,其他產業按照就業拉動系數從大到小排列。可以創造就業7236萬人,相當于2008年全部非農就業的15.5%。[11]由模擬分析可知,這三種分配方案拉動GDP的增長沒有太大的差別。所以,目標的選擇在投資的社會效益中起重要作用。政府投資可以在價值取向的指引下直接宣示某個目標的實現作為具體的社會效益產出期待狀態;或者某個目標優先作為具體社會效益產出狀態。
由此看來,政府投資的行業范圍與政府投資的公共利益價值目標矛盾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因為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與目前政府涉足競爭性或壟斷性行業并不天然矛盾,⑥按照陳敬武教授的總結:從國有經濟的分布領域和所處的地位來看,大體上可分為三種類型:⑴基礎設施、社會公用事業分布型:國有經濟主要集中在土地、資源、基礎設施、社會公用事業等領域。屬于這種類型的國家主要有日本、美國、德國和韓國等;⑵廣泛分布型:國有經濟除分布在基礎設施、社會公用事業等領域外,還廣泛分布于競爭性領域。這類國家有西歐、新加坡、泰國、印度等;⑶主導支配分布型:國有經濟不僅在基礎設施、社會公用事業領域居壟斷地位,而且在競爭性領域的所有部門(行業)也居于支配地位。如社會主義各國,特別是我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陳敬武.國有經濟的功能定位[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1,(5):54.競爭性行業中的政府投資也可以是在本著公共利益價值取向,且在具體社會效益目標追求下的拉動、引領、救濟等投資行為。所以,政府作為“經濟泵”沒有天然缺陷,關鍵是如何解決A與B之間過程的公正(或者說市場內公正)及社會產出中的市場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結果公正問題。這其中,價值取向指導下的社會效益目標選擇是關鍵問題。
[1] 傅云威.應對金融危機, 中國贏得敬意[EB/OL].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9/13/content_12045423.htm, 2009-11-30.
[2]蘇力.“什么是你的貢獻?”——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3](美)米歇爾·沃爾德羅普.復雜——誕生于秩序與混沌邊緣的科學的新描述[M].陳玲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4]劉溶滄,趙志耘,夏杰長.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財政政策選擇[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
[5]岳彩申.“需要國家干預說”的科學方法論解釋——證偽范式的認知[EB/OL].http://www.lichangqi.net/wz/wz.aspid,2009-09-08.
[6]侯懷霞,李虎.論經濟法的價值取向[J].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54.
[7]陳莉.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判斷標準簡論[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4):18.
[8](英)杰克·霍布斯著.利維坦[M].趙雪綱譯.華夏出版社,2008.
[9]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 [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10]蘇力.“市場經濟對立法的啟示”,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11]蔡昉.調整“4萬億”投資方向,避免無就業復蘇[EB/OL].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34114, 2009-09-13.
(責任編輯:高 靜)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Expenditure La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nancial Crisis
Sun Fang
Government investment is based on the China's social reality.The article analysis,and dialysis combing historical origins of complex adaptive social system,deducing that the o public investment expenditure in China is not only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but "induced water"role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thinking on the value-orientation of law in the context of the pluralism government role and social investment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multi-level expectations and to propose the public interest under the guidance of quantifiable values.
government investment expenditure;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legal supervision;value orientation
F810.424
A
1007-8207(2010)03-0036-05
2009-12-04
孫放 (1980—),女,黑龍江佳木斯人,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專業博士生,上海政法學院經濟法系講師,研究方向為經濟法、金融法。
本文系上海市法學會一般課題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 2009滬法課字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