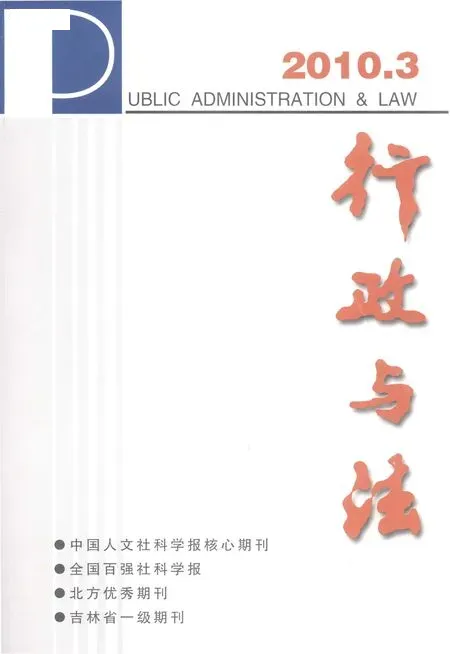行政裁量權的訴權分析
□吳蘭
(長春市委,吉林 長春 130012)
行政裁量權的訴權分析
□吳蘭
(長春市委,吉林 長春 130012)
規范行政裁量權需要通過訴權對行政裁量的內容進行控制。本文認為,通過訴權對行政裁量的控制,具有理論的基礎與實踐的優越性。但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審查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能對行政權過分干涉。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法官應該對行政裁量的合理性進行審查。
行政合理性;行政裁量;司法審查;訴權
20世紀以來,行政權極大擴展,立法不得不授予行政機關大量的、寬泛的行政裁量權,司法對裁量權在審查上又面臨技術上的障礙。為了防止行政失范和權力濫用給行政相對人造成損害,從而背離法治理念,需要通過訴權內容對行政權力進行控制。
一、行政裁量權能否作為司法規制的對象
行政裁量權能否成為司法規制的對象,歷來就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行政行為的裁量一般不違法,不能作為行政訴訟的原由。有學者認為,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裁量權具有首次性與原始性,而行政法院適用法律具有“反應性”和審查性。一般而言,對行政裁量權行使的不當問題,理論上多稱之為“適當性”或“合理性”問題,濫用自由裁量權行為在形式上有著“合法”的外在形式和表現。所以,行政主體作出該選擇本身不存在是否違法的問題,行政裁量權的行使一般不能成為訴訟法的對象。[1](p124)另一種觀點認為,行政裁量權應該成為訴訟法的對象。行政機構需要處理的事件大部分都是通過裁量來實現的。因此,裁量一詞是作為限定行政機關權力發揮以及描述司法審查對行政行為審查的本質的主要術語。所以,對法院而言,知道行政裁量是衡量行政行為以及明確法院所具有功能的必備保障。[2]也有學者認為,對行政裁量權的司法審查并不會損害政府的行為。行政人員在執法過程中,需要嚴格遵循法定的授權范圍。[3]
筆者認為,行政裁量權能否進行司法審查,首先需要討論的是對立法權與行政權性質的認識。就二者各自的范圍而言,二者具有緊密聯系性,“前一領域所包括的按其內容來說是完全普遍的,亦即法律的規定;而后一領域所包括的則是特殊的東西和執行的方法。”[4](p316)但這不能說行政權與司法權是對立的。基于共識,完全不受限制的行政權會導致行政權的濫斷,而防止這種濫斷的關鍵,理論上的路徑具有兩種:一是以權力制約權力;二是以權利制約權力。后者本質是規定公民的權利,從而限制行政權行使的界限。前者是依賴于國家的公權力達到制約行政權的濫用,從而實現權力的平衡,這主要表現為立法權對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制約。在立法允許行政裁量權存在的情形之下,司法權對其行使也就是題中之義。此外,行政權的本性決定了僅僅依靠權利來制約行政權是不可靠的,這就需要另外一種公權力來對此進行保障,而作為“法治的最終屏障”的司法權乃是對行政權制約的必然與最佳選擇。于此,我們可以說,為了防止這種權力的濫用,司法權對此進行制約乃是最好的途徑。對行政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具有以下優點:
第一,保障行政裁量權的合理運用。行政裁量權是行政機關在具體行政行為時行使的權力。行政裁量權的本質是行政機關在執法領域內,在從事具體行政行為時而予以運用的權力,這種權力具有濫用的可能。依據司法權的公正性對行政裁量的內容進行審查,從而能夠保障行政裁量權的合理利用。
第二,對行政裁量權進行審查符合行政裁量的本質特定。行政裁量權的本質是在追求實質正義中做出的在法律范圍內相適應的行為權力。“行政行為中的裁量,是指法院在審查行政行為時,能夠在何種程度上進行審查的問題,即法院在何種程度上必須以作出行政行為的行政廳的判斷為前提來審理的問題。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話,就是是否存在法律作為行政權的判斷專屬事項委任的領域乃至其范圍的問題,裁量實際上成為問題的,是以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審查范圍的形式出現的。”[5](p90)行政裁量是政府為了有效地運用它所擁有的手段或資源,實現政府所管理目的的需要。但需要強調的是,在法治政府框架之下,公民及其財產并不是政府行政的對象,也不是政府為了實現其目的而應加以運用的手段。因此,有學者認為,“行政機構在法治下行事,也常常不得不行使自由裁量權,正如法官在解釋法律時要行使自由裁量權一般。然而,這是一種能夠且必須受到控制的自由裁量權,而控制方式便是由一個獨立的法院對行政機構經由這種自由裁量權而形成的決定的實質內容進行審查。”[6](p270-271)
第三,行政裁量權的司法審查能夠保障裁量目的的真正實現。行政裁量權的行使本身是追求實質正義的行為,如果不對此加以司法審查,該實質正義有可能變成裁量權行使者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因為,“裁量雖是在追求個案實質正義,但如遇相同或相似個案,如做出差異性過大的裁量決定,不僅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亦與個案實質正義所追求的內容不相符合,因此行政機關為避免此不當情況出現,基本上會經由行政內部制定具體行政規則性質之裁量基準來作為所屬公務員與下級機關為裁量權行使的標準。”[7](p461)所以,行政裁量權的司法審查也就是確保行政裁量權的目的得以真正實現的一個必要的機制。
第四,行政裁量權的司法審查是保障受害人利益的需要。在實際生活中,行政裁量權的行使有可能對公民的利益造成損害,而對受害人的救濟只能通過司法救濟的途徑才能得以實現。
二、司法權對行政裁量權審查的限度
學者認為,在對行政裁量權進行控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系統工程中,司法審查是對行政裁量進行控制的“綱”。[8](p5)盡管這種說法筆者不敢茍同,但這的確指出了司法審查對行政裁量權的控制作用。但是,司法審查對行政裁量的控制應該是謹慎的。亞里士多德就認為,對行政裁量權的控制,應“盡可能地少留未決問題讓法官去解決”。[9](p208)英國著名行政法學者科奇也認為,“法律對行政執法人員而不是法律賦予了裁量的權力,該種權力具有首次的司法決定的性質。……而且,任何裁量都賦予了行政執法人員具有犯一定錯誤的自由。事實上,裁量本身具有一定范圍內從事行為的自由,這就使得執法人員的裁量有別于具有相關特定知識與經驗的專家對此所作出的行為。作為結果,當法院對裁量進行司法審查時,應該保持一定有時是極度的克制。”[10]學者認同司法審查對行政裁量的克制,這主要是因為司法審查將會損害行政裁量權的行使。因為:
第一,嚴格的司法審查制度將會導致行政效率低下。在嚴格司法審查的情況下,行政機關的行為動輒得咎,不利于行政機關靈活管理事務。如果行政機關的行為動輒得咎,則不利于行政目標的實現,也不利于行政機關開展行政活動對社會進行管理,最終會損害行政權的行使。對此,威利斯(John Willis)認為,對行政裁量的司法審查損害了行政行為的創造性,損害了行政自治的內容,如果行政人員嚴格遵循法律的剛性規則,行政人員在司法審查面前動輒得咎,就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府。[11]
第二,嚴格的司法審查將導致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分權受到損害。在民主與法治國家,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分離是保障人權、保障社會公正所必不可少的。如果司法機關對此進行審查,那么就會使行政權受到司法權的侵害。凱爾森因此擔心:“倘因現行法之適用,在其正審理之案件不能獲致合乎該法院之道德觀或政治觀的結果,便容許法院依自己之裁判,那就顯然賦予法院以太廣泛的權限。假若讓法院之道德觀或政治觀代替立法者之道德觀或政治觀,那便無異于要立法者將其職位讓給法官”。[12](p86)“不管是在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還是在中國,法院永遠不可能、也沒有能力像立法機關那樣制定廣泛的實體法規則,否則,就會違反憲政結構之下法院的角色,變為代替立法機關為行政機關選擇行為的規則。適度的角色錯位可以容忍,但過分的角色錯位是絕對不允許的。”[13]在該種分權機制下,司法對行政裁量權的審查需要保持克制。
第三,嚴格的司法審查制度將導致行政裁量權難以正確行使。行政裁量權的存在是行政權力行使的必然結果,所以,行政裁量權是不同行使方式中選擇出能夠實現個案正義的行使方式。行政機關對此的選擇就需要保持一定的裁量權,這樣才能實現法定的目的,通過對法定目的的解讀來實現個案正義。但是,如果對行政裁量權進行嚴格的司法審查,將會導致行政裁量的動輒得咎,不便于行政裁量權的行使。
基于以上理由,筆者認為,嚴格的司法審查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應該對之進行限制。這就需要司法在對行政裁量權的審查過程中保持一個限度或者堅持一個標準。
第一,在司法審查中,不能對行政裁量權行使的構成要件進行審查。司法如果對行政裁量權的構成要件進行審查,將會阻礙行政機關對裁量行為的判斷。因為,“理論成立的前提應是承認法構成要件為司法審查之必然對象,但為尊重行政機關之專業判斷,特別是近來科技立法之規定,在法構成要件上形成一行政自我領域,在此領域中行政機關所為之決定,法院僅能審查行政機關是否有逾越此領域范圍,其余在此領域中所為之行政決定,法院必須尊重,不得為審查之。”[14](p459-460)
第二,對不確定概念的運用司法審查需要保持克制。不確定概念本身就是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行使相關的職權而在立法中作出的規定。不過,這不等于不確定概念不能受到司法審查。因為不確定概念的存在,將會導致行政裁量權力的濫用,為了保障這種權力的行使符合權力的目的,應該對行政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但是,該種審查需要保持一定限制,也就是說,行政機關在行使不確定概念行政權的所有場合都要受到審查。但如果不確定概念的運用是在行政機關處理特殊事務或者既定情形時不能允許司法審查。
第三,對個人基本權利的侵害,要受到全面的審查。基本權利是由憲法所確定的一種綜合性的權利體系。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幾乎用相同的文字規定了人的基本權利:生命權,免受酷刑或殘忍的、不人道的、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權,任何人不得使為努力,不應被強迫奴役,人生自由與安全權等等。這些權利是憲法保障公民生存與發展所必要的內容,這種權利的侵害將會導致法律的基本違反。所以,在人的基本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行政法院原則上應從法律和事實兩個方面對行政決定進行不受限制的審查……只有在有關事務極為復雜和特別靈活,以至理解具體行政決定如此困難,司法審查可能破壞職能界限的情況下,才能考慮行政機關享有‘有限的決定自由空間’。”[15](p90)
第四,超越權力與濫用權力要進行司法審查。各國法院對行政裁量的審查做法有明顯差異,共同之處集中在兩個方面:超越裁量權與濫用權力。前者主要是指該裁量超越授權范圍而行使權限致處分成為違法,后者是指表面上行政機關雖在授權范圍內行使權限,但超越了法律授權的內在限度。[16]如我國臺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201條規定:“行政機關依裁量權作為之行政處分,以其作為或不作為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者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銷”。
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①該條內容為“人民法院經過審理,根據不同情況,分別作出以下判決:(一)具體行政行為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的,判決維持。(二)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并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⒈主要證據不足的;⒉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⒊違反法定程序的;⒋超越職權的;⒌濫用職權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責的,判決其在一定期限內履行。(四)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可以判決變更。”我國的司法機關主要是對行政行為不合法、濫用職權以及程序違法進行審查。[17](p15)從比較法的視角來看,我國《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體現了現代國家行政權和司法權合理配置的要求。此種規定表明,立法者在規定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時,遵守了司法權有限的基本規律。
三、法官如何對行政合理性進行審查
根據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法院只能就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只有在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時,才可以對其合理性進行有限度的審查,并作出變更的判決。因為,“從價值判斷的角度講,合理性原則追求的是一種至善的境界,而且法律也提倡行政機關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將合理性三原則發揮到極致,但若法院嚴格地以合理性原則的要求去判斷自由裁量行政行為的效力,則行政效能將陷入癱疾是顯而易見的,而政府所承載的一系列重大社會目標也就無從談起了。”[18]《行政訴訟法》第5條也對此進行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而《行政復議法》第1條所規定的任務,不僅在于糾正“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而且同時要糾正“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由此可以推知,司法機關的行政審理行為僅適用合法性原則。司法機關是不是可以對行政合理性進行審查呢?也就是說,行政相對人是否可以以行政合理性的內容進行訴訟呢?筆者認為,司法機關應該對行政裁量的合理性進行審查,這是因為:
第一,對行政裁量合理性進行審查,可以限制行政裁量權的濫用,這是督促行政機關積極高效行使行政權力的需要。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膨脹是現代行政的一個突出特點,如果不加以限制,它將會變成一種專斷權。對于行政自由裁量權,成文法的規制在技術上無法實現。為此,在適度范圍內授予法官根據正義或理性來判斷行政行為是否合理的權力,確立行政合理性司法審查制度,以合理性司法審查來對抗行政自由裁量權,這也是控制自由裁量權的重要途徑。[19]
第二,對行政裁量合理性進行審查,能夠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利益,促進行政裁量保障目的的實現。在我國,盡管行政相對人對于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可以申請復議,然而,由于行政機關自身的性質,行政復議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并不能有效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利益。如果不允許司法對行政的合理性進行審查,就剝奪了行政相對人的司法救濟權。
第三,將行政合理性列入司法審查能夠保障法治的統一。法律的統一不僅僅包括法律規則的一致、法律內容的明確,而且也包括法律精神的統一。由法院作為法律解釋和適用的最后一道關口,可以確保法律的統一適用和解決法律之間的沖突。與行政機關相比,法院在對法律的統一性、協調性具有更為高度的認識,因此,正如學者指出的那樣,司法審查是維護法治統一的重要屏障。[20](p556-557)
第四,對行政裁量合理性進行審查也是世界其他國家的經驗所在。盡管世界各國限制行政裁量的方法不同,但在審查行政合理性方面,一般需要對以下問題進行分析:⑴行政裁量是否具有不正當的目的;⑵行政裁量是不是不考慮法律規定應當考慮的因素,或者考慮法律規定不應當考慮的因素;⑶行政行為反復無常,相同情況不同對待,不同情況相同對待;⑷行政裁量顯失公平;⑸行政裁量不合理遲延或不合法拒絕。[21]如德國對行政裁量的合理性進行審查主要表現在:⑴審查行政機關是否錯誤理解法律概念和法律規定中的判斷余地。在進行這種審查時,法院需要審查行政機關對法律概念的抽象解釋是否妥當,而不審查不確定法律概念的特征在行政機關對具體案件的判斷中是否得到了正確的應用;⑵審查行政機關是否沒有意識到具體案件中存在判斷余地;⑶審查行政機關是否故意曲解其活動的法律界限,如未注意通常的判斷標準或客觀性要求,是否存在偏見、造成侵權損害等;⑷審查行政機關是否存在判斷瑕疵,如果存在,法院可以責令行政機關重新作出行政行為。[22](p358-360)所以,我國應該吸收世界各國的先進經驗,對行政行為的合理性進行審查。目前,在我國,應根據以下內容對行政行為的合理性進行審查:
其一、根據法律的目的進行審查。行政裁量是否構成濫用,看是否符合法律目的,“如行政機關之裁量權行使不以裁量權授予法條或法律規定目的為基準,此時就出現裁量權的濫用。”[23](p462)特別是當存在著幾種選擇的可能性時,行政機關對于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解釋選擇是否合理,人民法院有權審查,認為合理的予以認可,認為不合理的則不予認可。
其二,依據比例原則進行審查。訴訟中,法院依據法律的原則對行政機關的行為進行審查。在法治國家,政府的任務不再限于消極保障人權、保障公民的自由,國家機關應遵守法律約束,在法定范圍內行使權力,如果這種權力違反法律、超越職權則應對公民進行國家賠償。在比例原則中,強調手段的適當,不可過分侵及義務人權利,這是與法治國家原則相契合的。比例原則以人權保障為最高價值追求,強調在達成目的的手段的副作用過大時可放棄目的的追求,講求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平衡,其實質是在國家與公民之間講求一種公平、和諧,這同樣是法治國家原則所能涵蓋的。[24](p96)法官在審理案件的時候,需要結合比例原則所包含的內容(即適當性原則、均衡性原則的內容)進行審查。
從比較法視角而言,對于合理性司法審查的操作標準,在各國實踐標準不盡一致。美國法院對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準主要有六個:⑴是否違法,其中“違法”包括實質的違法與程序的違法;⑵是否侵犯憲法的權利、權力、特權或特免,其中憲法規定的權利包括公民的選舉權、人身自由權、言論自由權、正當程序權等;⑶是否超越法定的管轄權、權力或限制,或者沒有法定權利;⑷是否專橫、任性、濫用自由裁量權。根據司法實踐,濫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又包括目的不當、專斷與反復無常、考慮了不相關的因素和未考慮相關的因素、不作為和遲延等;⑸是否沒有事實根據;⑹是否沒有“實質性證據”,其中“目的不當、專斷與反復無常、考慮了不相關的因素和未考慮相關的因素、不作為和遲延”亦屬判定行政行為是否合理的具體操作標準。[25](p556-557)英國法院對于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主要從以下十個方面進行:⑴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作出行政決定時,將不相關之因素納入考慮;⑵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作出行政決定時,未將相關因素納入考慮;⑶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以非法律所授予之目的或不正當之動機作出行政決定;⑷行政機關以惡意或不誠實行使裁量權;⑸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忽視公共政策;⑹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 其行使 “不公正”、“不完善”、“恣意”、“不公平”、“過分”、“剛愎”、“反復”; ⑺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忽視市民法律上合法之期待;⑻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法律解釋不適當;⑼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違反禁反言原則(例如違背契約或承諾);⑽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其行使是如此之不合理(或荒謬、暴虐、錯誤),以至于任何具有理性之人均不可能如此行使。[26](p56-57)德國司法審查的標準主要包括六個:⑴無權限;⑵超越管轄權,包括超越地域管轄權與超越實體管轄權;⑶實體瑕疵,包括法律瑕疵、事實瑕疵、違背善良道德、不清楚、錯誤方法等;⑷違反程序與形式;⑸超越自由裁量權,包括超越自由裁量權范圍和不行使自由裁量權;⑹濫用自由裁量權。其中“違反合理性原則、不正確的目的、不相關的因素、違反客觀性、違反平等對待”都屬合理性司法審查的具體操作標準。[27]
因為這些判斷仍然屬于一種主觀判斷標準,操作性不強。對此,我國學者提出了多種操作標準。有學者認為,合理性原則應該包括:一是正當性標準。即行政行為的作出應出于正當的動機、目的,應考慮正當性因素;二是情理性標準。行政行為應符合法律價值,符合公認的道德觀念,符合生活常理。[28](p237)也有學者認為,符合下述標準之一者就屬于行為不當:不正當的目的、不善良的動機、不相關的考慮、不應有的疏忽、不正確的認定、不適當的遲延、不尋常的背離、不一致的解釋、不合理的決定、不得體的方式。[29](p270-276)也有學者認為,不合理行政行為應包括:目的不當、錯誤的事實認定、不適當的考慮、法律適用不當、不作為和程序不當的行政行為。[30]也有學者認為,存在以下情形或條件時,一般情況下均可判斷為 “不合理”,認定為濫用職權:[31](p59-60)⑴如果行政主體或行為人在行為當時,明顯存在惡意、不誠實的情況。比如存在報復性處罰時,就可以認定為“不合理”。例如工商局人員為了對其在市場租用攤位的熟人換個好位置,要求攤位較好的張某經營的百貨店串動攤位,被張某拒絕后,工商局將張某百貨店予以查封;⑵明顯故意或非故意(因認識的原因)嚴重曲解法律或其他依據;⑶明顯應當考慮的因素沒有被考慮。比如婚姻登記機關認定某對公民離婚證無效時,沒有充分考慮法定的必要因素——沒有查明所謂的相對人“騙取離婚證”之證據;⑷當行政主體或行政行為人在行為當時,顯屬不應當考慮的因素卻被考慮了,可以高度懷疑。比如英國1926年著名的“紅發案件”中,校長因教師頭發為紅色而將其免職。此處分已考慮了不相干因素,違反合理原則而無效;⑸行政行為如果與多數有理性的人的觀點嚴重相違背,可以高度懷疑。這就是法官格林(Greene)所謂“如此荒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能想象行政機關在正當地行使權力時能有這種標準”;⑹行政方法上(手段、措施、種類)強人所難,要求苛刻,明顯使相對人利益受不必要侵害,或者增加相對人不必要的負擔;⑺同一行政主體對同類事件實施處理卻變化無常,違反同一性和平等性的。比較以上各種觀點,筆者更贊同孫笑俠教授總結的行政合理性不當的這幾種情形。因為這些標準更具有操作性,更符合行政合理性規范的目的與比例原則。不過,需要明確的是,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合理性審查范圍并不需要進入行政權。合理性審查的目的是制約行政權,而不是削弱行政權,更不是代替行政權。合理性審查之所以必要,主要是督促行政人員謹慎行使權力,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利益。
綜上所述,對行政裁量的訴訟,不僅包括“違法性”問題,還包括“合理性”問題、“合目的性”問題,這些都屬于司法審查所要解決的問題。正如學者所說,把司法審查的標的局限性地稱為“合法性審查”是一種過時的錯誤觀念,相關的立法應該予以改正。[32]值得指出的是,司法審查在具體的行政裁量行為中,對結果的確認,要么給予維持原行政裁量行為,要么對之予以撤銷,一般不直接改變行政行為的實質內容。如果司法審查能夠直接改變行政行為的內容,無疑會導致司法權對行政權的不當介入。
[1](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行政法學總論[M].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0.
[2]C.KOCH,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ACTICE§9.7,at106-07(1985).
[3]Genevieve Cartier,ADMINISTRATIVE LAW TODAY:Culture,Ideas,Institutions,Processes,55 Univ.of Toronto L.J.631.
[4](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1.
[5][15](日)鹽野宏.行政法[M].楊建順譯.法律出版社,1999.
[6][9](英)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鄧正來譯.三聯書店,1997.
[7][14][23]陳慈陽.行政裁量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以兩者概念內容之差異與區分必要性問題為研究對象[J].載臺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C].臺灣五南出版社,2001.
[8][17]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論[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
[10]Charles H.Koch,“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in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May,1986,p.470.
[11]John Willis,Canadian Administrative Law in Retrospect'(1974)24 U.T.L.J.225 at 2367.
[12]Kelsen,aaO.S.253.轉引自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13]余凌云.法院如何發展行政法[J].中國社會科學,2008,(1):98.
[16][21][32]解志勇.行政裁量與行政判斷余地及其對行政訴訟的影響[J].法治論叢,2005,(5):68-70.
[18][30]王振宇,鄭成良.自由裁量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原則和標準[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0,(3):12-13.
[19][27]馮志勤,王聽煜.行政合理性司法審查探究[J].法治論叢,2006,(5):41-43.
[20][25]王名揚.美國行政法(下)[M].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
[22](德)漢斯·J·沃爾夫,奧托·巴霍夫,羅爾夫·施托貝爾.行政法[M].高家偉譯.商務印書館,2002.
[24]羅豪才.行政法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26]羅明通,林惠瑜.英國行政法上合理原則應用與裁量之控制[M].臺灣臺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1995.46-50;孫笑俠.論司法對行政的合理性審查[J].公法研究[C].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
[28]張正釗,李元起.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9]江必新.行政訴訟問題研究[M].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
[31]孫笑俠.論司法對行政的合理性審查[J].公法研究[C].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王秀艷)
Analysis of the executive discretion of the right to appeal
Wu Lan
Standardize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ary right of appeal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through the contents of control.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ight of appeal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y the control of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dvantages.But the judicial power of the executive power should be reviewed to maintain a certain limit excessive executive power can not interfere.Therefore,in judicial practice,the judge should be the reasonableness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ary review.
administrative rationality;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judicial review;litigation
D922.1
A
1007-8207(2010)03-0086-05
2009-12-20
吳蘭 (1967—),女,吉林松原人,長春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研究方向為法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