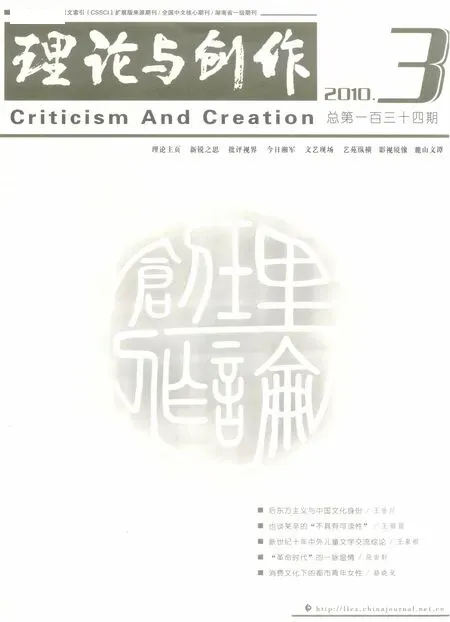為誰寫作:論西部作家的底層意識
■ 王貴祿
一個作家在何種價值立場上看待底層,以何種情感和眼光評價底層人物的生存方式、命運遭際、精神狀況等,這往往形成其底層意識。作家的底層意識,實際上是一種高度的文學自覺。這種“自覺”表現在,作家已了然這是為誰而進行的創作,其作品隱含著何類讀者,這樣的創作到底在呼喚和催生什么樣的社會生態。換句話說,富于底層意識的作家,其創作之根已深植于現實生活中,深植于底層民眾中,而在精神層面又超越了底層。在這個意義上,直面底層、再現底層生活,這是作家底層意識的基本狀態,而最為關鍵也最為動人之處,則在于作家以主體身份介入到底層的矛盾張力中,為底層遭遇的苦難真誠地呼吁,而同時卻能夠真實傳達底層的利益訴求、人生期待和政治愿望;則在于密切關注底層的文明進程,以提升底層的精神境界為己任。底層表述的生命力和感染力也正源于此。
一、革命話語主導下的底層表述:作為美學主體的底層
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是圍繞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論證與新的國家精神的確立而展開的,以革命歷史圖景的展示和民族國家的再想象為其特征,表現出鮮明的革命指向。也是在這種革命話語主導的語境中,西部作家的第一代(如柳青、杜鵬程、王汶石等)開創了西部敘事的先河。他們是在陜甘寧解放區成長起來的作家,就其生活經驗、作品取材的區域而言都與東南沿海地區的作家不同,文學地理上的這一轉變,“表現了文學觀念的從比較重視學識、才情、文人傳統,到重視政治意識、社會政治生活經驗的傾斜,從較多注意市民、知識分子到重視農民生活的表現的變化。”①他們從創作的早期,就將眼光投向底層,以底層表述而登上文壇,底層關注甚至成了他們一生的選擇。他們眼中的底層卻遠不是怨天憂人、自暴自棄及精神迷惘的底層,而是具有階級主體性和歷史能動性的底層,是處于急劇上升時期的底層。也就是說,他們是將底層作為美學主體進行表述的。這種底層表述,“會提供關注現代文學中被忽略的領域,創造新的審美情調的可能性。”②
早期的啟蒙知識分子常常將底層編碼為愚昧、麻木、冷漠的群體,如魯迅筆下的鄉村文化形態。啟蒙話語與真實的底層人生其實是相當隔膜的,啟蒙者的底層想象過于悲觀和單一,導致了底層對啟蒙話語的排拒。盡管啟蒙話語對底層并沒有也不可能造成實質性的影響,但作為一種表述底層的方式,卻在知識階層普遍流行,致使底層的本真面目越來越模糊。啟蒙話語之后,三十年代革命話語背景下的底層仍然失語和緘默,這種狀況直到四十年代的解放區文學才有了好轉。由于其時《講話》精神的廣泛傳播,加之解放區政府利用了行政調動力,底層方有可能以其原生形態進入到作家的視野,周立波、丁玲、李季等的創作顯示出了嶄新的底層氣象,他們的創作也為柳青等西部作家的底層敘事做了必要的鋪墊和準備。
柳青的《創業史》不像《紅旗譜》、《青春之歌》等“成長小說”,沒有過多地敘述主人公梁生寶的成長經歷,而是將主要精力放在了再現這個底層人物的階級主體性和歷史能動性方面,以凸顯“新底層”的本質為旨歸。但如何凸顯?我們知道,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無法擺脫倫理道德的束縛,而將梁三老漢設置為梁生寶的繼父,顯然切斷了梁生寶這個新底層身上的宗法遺留,為其投向心儀的“父親”——黨的懷抱預設了令人信服的邏輯前提。然而,關于梁生寶形象的真實性,即使在《創業史》(第1部)發表的初期就遭遇質疑。質疑者并不是直接向梁生寶這個人物發難,而是反復言說梁三老漢形象的真實性,這的確是一種富有深意的解構策略:如果梁三老漢形象的真實性能夠成立,那么,梁生寶形象的真實性自然就失去了依據。但梁三老漢卻是一個徹底的舊式農民,他的身體充分顯示了其底層性和被規訓性:滿面很深的皺紋,稀疏的八字胡子,憂愁了一輩子的眼神,脖頸上一大塊死肉疙瘩。他活像一個五十年代的閏土,眼神中亦不乏祥林嫂的遺留。是的,梁三老漢是夠“真實”,倘若將其生活的時代后退到二十年代;但在一個改天換地的年代,其所作所為所想卻暴露出荒誕性和令人憎惡的保守性,他斷然不可能昭彰底層的未來和希望。
如果是這樣,質疑者為什么還要窮追不舍?反復抬高梁三老漢這一類底層人物的終極目的又是為何?不難看出,質疑者仍然在沿襲著二十年代的啟蒙話語,他們認定底層只能像梁三老漢一樣狹隘、自私、勤勞、純樸和容易滿足,其人生夢想無非是“做三合頭瓦房院的長者”,怎么可能是思想先進、無私慷慨和有能力組織窮哥們奔赴共同致富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帶頭人呢?正如底層不能理解文化精英夸夸其談的啟蒙話語或現代性話語,高高在上的文化精英也同樣不能想象底層會爆發出如此強大的自省力量和改變自身命運的智慧。某種程度上說,《創業史》的出現打破了文化精英的慣性思維,梁生寶的形象也沖決了文化精英關于底層的知識邊界,這使他們不能容忍,不能再保持沉默。實際上,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新世紀初,文化精英或隱或顯地否定《創業史》和梁生寶這一底層人物的聲音從來都不曾停歇,這反而給人們一種提示:支撐柳青創作的不是精英意識,而恰恰是底層意識。
柳青等西部作家是《講話》后在陜甘寧解放區逐漸成長起來的,這個成長經歷奠定了他們健朗的底層意識。在《講話》中,毛澤東以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倡導知識分子到底層去鍛煉和接受改造,他認為底層盡管“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③。現在看來,毛澤東所器重的是淡化了精英意識而以底層審美為志趣的作家,其底層觀深度影響了解放區作家的創作。柳青就是一個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堅決的追隨者和實踐者。與《講話》提出的知識分子改造相一致,柳青在建國前后多次深入到底層,在艱苦的工作崗位自覺地磨練自己,苦行僧似地進行知識分子改造,最終淡化了精英意識。這是柳青區別于來自國統區作家的一個重要特征,其早期的敘事如《種谷記》和《銅墻鐵壁》,就是根據底層工作的觀察和體驗完成的。正因為這種對底層群體堅決的情感皈依,他的筆觸也就能夠沉潛到草根深處,在時代的大變動中自如地再現其心靈運行的軌跡。
不僅柳青,而且王汶石、杜鵬程等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西部作家都是將底層作為美學主體進行表述的。王汶石不同于柳青的苦心建構史詩般的巨制,他往往從底層人生中截取一個個片段,憑借對底層新生活的熱情和社會新事物的敏感,及時發現處于上升時期的底層身上的亮點,并通過鋪陳這亮點的時代生活動因,以形成自己的底層表述。杜鵬程的短篇主要涉及和平年代的底層建設者形象,他善于通過底層平常生活的展開來折射人物的心靈之美,從而凸顯底層的美學主體性。從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上看,柳青等第一代西部作家的底層表述已作為一種資源而存在,對后輩西部作家的影響極其深遠。
二、底層是天使,抑或是庸眾:當文化精英遭遇底層體驗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反右”,在大陸知識界產生了一批“右派”。幾乎是一夜之間,他們從受人尊敬和待遇優厚的知識分子,被下放到貧瘠的鄉村或偏遠地區接受“改造”,從此像沉默的底層一樣失去了話語權。這種社會地位的巨大反差,使他們真正體驗了、經歷了底層生活,一定程度上說,在這樣的非常時期他們也是底層的構成部分。“文革”結束后,當他們重新擁有失去的社會地位而告別底層時,他們會以何種情感和眼光審視曾經與他們相濡以沫的底層?他們會以何種話語方式表述底層?重估新時期初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思潮,我們卻驚奇地發現,再次踏上“紅地毯”的知識分子所描述的則主要是知識分子的受難史與精神史,而那些為人稱贊的文本又多是知識分子的自我塑造、自我辯解和自我洗刷。“右派”作家的底層表述不僅與真實的底層令人遺憾地相隔膜,而且顯示了其有意疏離底層的傾向,底層在他們的筆下往往是缺乏美學主體性和歷史理性的一群。“右派”作家與底層人生的這種貌合神離,既說明了其精英意識的頑固性,也預示著其底層表述的暫時性。然而,作為一種難以釋懷的文化記憶,底層體驗卻在“右派”作家剛剛踏上“紅地毯”的那個歷史時刻難免要左右他們的創作,盡管底層在這里僅僅是作為“陪襯”而出現的。
張賢亮和王蒙都是從“反右”斗爭中始遭遇底層體驗的西部作家,近20年的底層體驗不可能不在他們的創作中留下痕跡,事實上,他們新時期初的創作多涉及底層。雖然他們與其他“右派”作家一樣,并沒有形成和柳青們相似的與底層同呼吸、共命運的審美情感,但畢竟他們筆下的底層面目尚不猙獰,甚至在某些文本中,底層還變身為“天使”——心地純良、善解人意、可以無怨無悔地為“落難”的知識分子獻身。但是,隨著這些作家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底層便走向了可憐、可惡或可憎,越來越不討人喜歡,如張賢亮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的創作;或底層從記憶中徹底消失,不再被關注,如王蒙進入九十年代以后的創作。底層形象從“天使”到“庸眾”的滑落,無疑是由于張賢亮們的底層意識的更替使然。我們不妨重讀張賢亮新時期問世的文本,以觀察其底層意識的演變軌跡。
張賢亮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以引人注目的《邢老漢和狗的故事》、《靈與肉》等作品而重返文壇。此時的作者仍身處社會的底層,盡管其時的小說不無悲憤慷慨的情緒,但鋒芒內斂、哀而不傷,行文之中流溢出的是對底層人物的欣賞、同情和贊美之情。可以說,此階段張賢亮的底層意識不僅健朗,而且就他而言也是最接近底層真實的時期。
在《靈與肉》發表四、五年之后,張賢亮又陸續推出引起更大爭議的《綠化樹》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短短的幾年時間,張賢亮進入了權力層,其人生境遇得到極大改善,已完全擺脫了底層的困苦與艱辛。伴隨著他精英意識逐漸增強的是,其底層意識也在不知不覺之間發生了變化。癥候之一便是,底層人物由前期的主人公身份退居為陪襯性人物,他們的一切活動似乎只是為了突出落難知識分子的存在。如《綠化樹》中安排馬纓花、海喜喜這些底層人物的活動,都無非是為了完成某種使命——使精神人格遭遇閹割的知識分子章永麟恢復做人的自信。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皆為落難知識分子,他們孤獨、脆弱而且敏感,故事的演進也主要是根據主人公的情緒變化,在他們豐富而復雜的心理流動中映像底層人物,故底層人物無一幸免都被做了主觀化和平面化的處理,呈現為靜止的“失語”狀態。
因為底層真實的存在被作者有意無意地遮蔽,于是作品的幻想性質便凸顯出來。以底層女性與落難知識分子的糾結而論,敘述的重點已不是知識分子被教育、改造和受感化的種種心情,而是著意渲染底層女性對落難知識分子的憐憫、恩賜和愛撫。受難者身邊的此類底層女性,往往可以為心目中的“好男人”犧牲自己的一切而在所不惜。那么,吸引底層女性的到底是什么?倘若從正常的標準衡量的話,落難知識分子既無政治地位,勞動能力又低下,且其囊中也羞澀,這樣的人怎么能讓終日奔波在生存線上的底層女性動心呢?為了給讀者一個理由,作者便不惜虛構一個個“紅袖添香夜讀書”的場景,并借底層女性喬安萍之口做了簡單的交代,“右派都是好人”,“我挺喜歡有文化的人”(《土牢情話》)。“好人”或“有文化的人”——這樣的理由就能使底層女性為之傾情、為之赴湯蹈火?顯然,諸如此類的交代于情于理都很勉強,不過是作者對愛情生活充滿羅曼蒂克的幻想而已。
如果作者對底層人物的精神活動的遮蔽僅僅以羅曼蒂克的形式出現也就罷了,問題是作者在神化底層的同時,又時常對底層流露出不屑一顧的神情。映照出來的是張賢亮底層意識的復雜性與矛盾性。從根系上看,張賢亮始終以“知識分子”這一社會身份自居,即使身處災難的深淵,即使為兩個稗子面饃饃也不惜露出卑賤相,那黑色囚衣包裹下的仍是死而不僵的精英意識,仍是一種優越感。曠日持久的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改變的只是他的身體,并沒有有效觸及他的靈魂,也沒有使他能夠更好、更深刻地理解與認同底層的苦難、歡樂和希望。在他落難的時候,是底層不止一次地將他救贖,這其實僅僅使他對底層產生了一種感激之情,因此,在某種情況下他也還能夠寫活底層形象。但他真正感興趣的并不是底層表述,而是借底層經驗以傳達其精英意識。這樣,在張賢亮進入權力階層后,便時時有底層意識與精英意識的沖撞、消長與更替,這便是導致底層形象在“天使”與“庸眾”之間徘徊,直至完全滑向“庸眾”的緣由。當他徹底告別底層經驗而全面書寫其精英意識時,又在多大程度上可能給讀者帶來驚喜?像《習慣死亡》和《我的菩提樹》,充斥于字里行間的無非是知識分子自作多情的痛苦、孤寂和無望,是猶豫彷徨而又自怨自艾的情緒,是知識分子一次次的云雨之歡和心如死灰,曾經的章永麟們極力張揚個人價值的勃勃雄心已消失殆盡、無影無蹤。
張賢亮是幸運的,因為他有著豐厚的底層體驗,這使他在八九十年代之際成為領潮的作家,他以現代的方式注解了文學“窮而后工”的道理。張賢亮又是不幸的,因為精英意識的執拗與作祟,他最終還是沒有將文學之根深植于底層厚土之中,故進入九十年代后其創作便泄露出強弩之末的尷尬,盡管張賢亮從不缺少才情與靈氣,盡管他一直很勤奮。
三、底層并不等于苦難:現代性話語裹挾下底層表述的多向度拓展
在張賢亮、王蒙這些“右派”作家黯然撫慰靈魂創傷的同時,一批更年輕的西部作家開始崛起,如路遙、張承志、賈平凹、扎西達娃。他們大多來自社會的底層,從小體驗的底層磨礪和苦難經歷,不是讓他們逃離與背叛,而是將他們的哀樂牢牢地粘附于底層,以至于在他們成名之后多年,雖然有的已進入了權力層,底層仍是他們夢魂牽繞的所在。這代西部作家與柳青一代有很大的相似性,他們亦將底層關注當作他們一生的選擇,即使在新時期以來多種思潮的頻繁更替中,也不曾動搖他們的底層意識。但新時期文學又是以現代性話語為主流的,呈現為多元話語共存的格局,這不能不影響他們的價值取向。“人”的覺醒與發現、文化尋根與反思、底層神話的崩塌與重構等題旨,都是這代西部作家的底層意識的構成中不同于前輩的地方。他們的底層表述正是在現代性話語的裹挾下所進行的多向度拓展,其努力大大豐富了西部小說底層表述的可能性,具有獨特的文學史意義。
T1時刻:根據風力、光伏的實際出力情況、負荷需求、儲存電量水平等,進行生產調度調整,如指定電源出力、管理負荷、控制交換功率等。
路遙從八十年代初發表中篇《驚心動魄的一幕》步入文壇,到九十年代初完成長篇《平凡的世界》后突然謝世,十年時間里奉獻了數量驚人的底層文本。他的文本是巨變時代底層人生的忠實記錄,其最動人之處在于深度描述了底層青年改變命運的激情,及其由此而來的不得不時時直面的挫折、抑郁和焦慮。這也是路遙不同于柳青的地方,在柳青那里,上升時期的底層青年雖然也有碰撞,有不如意,但底層在政治上的優勢卻足以緩解乃至于化解一切挫敗,而路遙時代的底層顯然已經復歸于草根狀態,底層青年向前跨出的每一步都意味著沉重與艱難,都意味著孤軍奮戰的血的代價。但路遙并不憂傷,也從不悲觀,他以極其細膩的筆法記敘了底層青年遭遇不幸后,其父輩們以黃土地一樣的寬容和誠摯來接納他們,安慰他們,使他們重建生活的信心。路遙的底層敘事因此便具有了不可替代性——以底層青年改變命運的歷史動機為中心,盡可能全景式地映像底層社會的方方面面,并將眼光輻射于非底層人群。面對孤立無助而又不甘心重蹈先輩命運的底層人,他的筆端常常流溢出不可遏止的溫情與同情,他太理解這些底層人了,對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感同身受,因之他的底層表述也就能夠抵達同類題材難以企及的真實性與豐厚度,特別是那些對底層人悲劇般的尊嚴、絕望般的希望和西西弗斯般的奮斗歷程的描述更是具有跨越歷史時空的沖擊力,感動了幾代的底層人。列寧曾言,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們。它必須在群眾中喚起藝術家,并使他們得到發展。”④路遙的文學人生無疑對之做出了形象化的詮釋。路遙底層意識的突出表征,還在于將底層人物置于中國現代性進程的大背景中,但始終能夠站在底層的價值立場上,探察底層群體的人生出路與未來前景,再現底層的疾苦和歡樂,反饋他們的愿望與心聲,路遙已完全把自己預設為一個“底層作家”。陳忠實曾這樣評價路遙的意義,“路遙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勞動者構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最能深刻理解這個平凡世界里的人們對中國意味著什么”,⑤并非無的放矢。
如果說路遙以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全景式地再現了特定歷史時空中的底層人生,那么,張承志則以浪漫主義的創作姿態,著力表現了底層在苦難和不幸面前召喚出的堅強、韌性與豁達,以蒼健而悲涼的筆調歌頌著底層。正本清源地看,奠基張承志敘事底色的不是精英意識,而是底層意識,這與其成長經歷有關。他曾在偏遠的內蒙古烏珠穆沁草原插隊四年,是底層給這個異鄉來的已進入青春期的少年以無私的關愛和奉獻,這使他深深地為底層的淳厚、素樸和誠摯所感動,他躁動而漂泊的心從底層那里獲得了少有的慰藉和安寧,底層于是成了他永遠的精神故鄉。這個經歷幾乎決定了他闖入文壇的那一時刻的基本選擇,他曾真誠地說:“我非但不后悔,而且將永遠恪守我從第一次拿起筆來時就信奉的‘為人民’的原則。”⑥那么,張承志又將如何實踐“為人民”的創作理性?他走的顯然不是柳青、路遙的現實主義路子,也與張賢亮的底層表述形成了反方向運作。他更關注的是底層的心靈世界的變遷與展示,挖掘底層在各種非常態的情境中何以爆發出驚人的耐力與韌性,從其成名作《旗手為什么歌唱母親》到廣受爭議的《心靈史》,他從兩個端點上對謳歌底層進行了鏈接。但由于張承志深受精英文化的熏陶與濡染,其思維方式和表述方式與底層讀者的期待卻是判若云泥,這也就不難理解,他的作品為什么不可能在底層產生多大影響了。
張承志的種種書寫,如對底層人生的頌揚、對權力社會的否定、對自然美景的留戀和對宗教文化的皈依,極易使人產生誤讀,似乎張承志敘事文本的精神訴求極不穩定,并造成這樣的錯覺:神圣的姿態與虛無的內核。⑦但如果聯系中國社會八十年代以來的實際狀況,就不難洞悉,張承志其實一直在為底層的前途命運而擔憂,他在冥冥之中預感到現代性進程也許將會使底層變得更加一無所有,曾經擁有的一切美好記憶亦將蕩然無存,這種底層焦慮是如此的深刻,竟使他有時不得不以一種過激的方式加以表現。要正確認識張承志的底層表述,后現代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話也許最具啟示性:“從理論角度看,浪漫主義之新純屬無意:它確實如同肌體躲避打擊一樣,可以視為一整代人試圖保護自己的方式,以此回避世界的總體性的空前的大轉變,即世界從此進入中產階級資本主義貧瘠的物質主義的環境。因此,一切封建世態和政治白日夢,一切宗教事物和中世紀事物的氛圍,對舊式等級社會或原始社會的復歸,旨在還原舊貌的復歸,都應該首先理解成防御機制。”⑧如果我們從“試圖保護自己的方式”來理解的話,張承志敘事文本的內核其實很具體:捍衛底層的尊嚴。
在路遙和張承志之外,扎西達娃等作家八九十年代的底層表述同樣可圈可點,他們都把各自熟悉的底層生活作為主要創作資源來展開,形成了西部小說底層表述的多元格局。就扎西達娃的底層表述而論,既不同于路遙的現實主義,也不同于張承志的浪漫主義,他懷著強烈的啟蒙沖動,通過營造那些如真似幻的宗教文化背景,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方式來映像底層人生的悲劇性與荒誕性,故扎西達娃的底層表述顯得空靈、縹緲而意味深長。
從扎西達娃的后期創作來看,其精英意識與底層意識始終纏繞在一起。他筆下的人物大多是等待拯救的底層,他們愚頑地重復著某種宿命,不注意時代的變化,也不相信自己改變命運的可能性。在這些時候,扎西達娃表現更多的是精英意識,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觀照,這樣,我們能看到的也只是扎西達娃啟蒙話語中的底層,底層本真的生存狀態與心理流程在此被過濾掉,或被高度抽象化和寓言化。扎西達娃的這種敘事策略的實施,可能在尋求某種更高意義上的“哲學的真實”或“文化的真實”,但畢竟在相當程度上遮蔽了底層,因此也限制了其底層表述的再拓展空間。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讀出扎西達娃深沉的底層意識,彌散于他后期文本中的情感主要是一種“現代性焦慮”,是渴望底層踏上自由之路的緊張,是因為底層的行動滯緩而生發的絕望過后的悲哀。扎西達娃一直在試圖“拯救”底層,預設著憑借其啟蒙話語將他們從宗教的沉溺拉回現實中來,并創造和享受現世的幸福。因是之故,我們從他的文本中根本就讀不出辛辣,而是對底層愛極生恨的焦慮、緊張與悲哀。
四、走向“底層文學”:消費時代的底層表述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伴隨著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規模轉型,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度的裂變,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地域差距、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的無限蔓延趨勢。在這樣一個由消費文化、強權和資本合謀的語境中,社會底層被持續再生產,于是,沉寂已久的革命話語在不知不覺之間復興起來,其重要表征是“底層文學”的橫空出世。底層文學雖然以革命話語為其主要的話語形式,但顯然與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主流話語有著內在的差異,底層文學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并不主張通過階級對抗和政治革命的激進方式來改變底層的生存境遇,而是直面客觀存在的兩極分化和階層分化,強調復歸“革命文學”的人民性傳統,呼吁權力社會關注底層的艱難民生,關注底層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呼吁通過建構一種平等、和諧的社會秩序,使底層的存在狀況得到根本的改善,使他們重獲失去的政治地位。我們可以將底層文學的話語方式看作是“后革命話語”,或“新左翼話語”。
西部小說從其發端就是以底層表述為其標識的,我們在此論及西部小說之走向“底層文學”,無非是說,在中國社會已進入市場意識形態為主導、消費文化為主流的語境,西部小說與方興未艾的文學思潮形成遇合與對接是水到渠成的必然。在這一過程,受強勢文學思潮和地域性文學傳統的合力影響,此階段西部作家的底層意識同樣會呈現出某些特別的時代烙印。賈平凹、雪漠、石舒清、王新軍等作家的創作是這種時代印痕的極好體現。
八十年代初期的賈平凹為社會變革帶來的底層富裕氣象而欣喜不已,其時的底層表述師法沈從文、廢名等京派名家的鄉土神韻,表現出底層人生的詩化傾向,風格明朗而清新,《商州初錄》等文本把底層面對觸手可及的幸福時的情態已和盤托出。八十年代中期創作的眾多中篇,如《天狗》、《山城》、《遠山野情》,賈平凹表現出欣喜過后的一絲隱憂,歷史是進步了,底層是衣食不愁了,但人們的道德水準卻在下降,浮虛之風正在生長,這是底層的幸還是不幸?長篇《浮躁》將其喜憂參半的情感推向了高潮,而其風格漸趨沉郁。進入九十年代,賈平凹似乎離開了底層言說,連續創作了《廢都》、《白夜》和《土門》等涉及都市上流社會的長篇,而這些敘事中卻出現了一個悖逆的現象,即權力人物一個個處于醉生夢死的狀態,不難讀出作者對上流社會的厭棄之情,其實也是他底層意識的別一向度的表述。如果說《廢都》和《白夜》的表述風格以沉郁較著,則《土門》一變而為凝重。在《土門》中,作者的底層意識中攜帶著沉重的憂患,農民告別了土地將何去何從?并沒有人給那些即將失去土地的農民安排一個更好的出路,他們想象中的幸福卻越來越模糊,他們已被城市文明拋向了不可知的窘境。從底層表述的意義上看,《土門》是一個標識,它是賈平凹轉向底層文學的契機,其所昭示的悲劇性意蘊將在賈平凹新世紀的創作中得以延續和深化。
賈平凹于新世紀初推出《秦腔》,這個長篇可以看作是《土門》的邏輯延伸。《高興》給我們展現了鄉下人進城后的悲慘境遇。在更高的意義上,又不能不使我們產生這樣的疑惑:現代性的終極意義何在?這不僅是我們的追問,其實也是賈平凹的追問,他在《高興·后記》中寫道:“我為這些離開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貧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種種歧視而痛心著哀嘆著……想為什么中國會出現打工的這么一個階層呢,這是國家在改革過程中的無奈之舉,權宜之計還是長遠的戰略政策,這個階層誰來組織誰來管理,他們能被城市接納融合嗎?進城打工真的就能使農民富裕嗎?沒有了勞動力的農村又如何建設呢?城市與鄉村是逐漸一體化呢,還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貧富差距?”⑨
在西部作家中,賈平凹的底層意識是獨特的。盡管與柳青相比,他缺乏的是柳青那樣的大度與融洽;與路遙相比,他缺乏的是路遙那樣的真誠與謙卑;與張承志相比,他缺乏的是張承志那樣的慷慨與熱烈;甚至與張賢亮相比,他缺乏的是張賢亮那樣的袒露與感激,與扎西達娃相比,也缺乏扎西達娃那樣的焦灼與悲情。但賈平凹卻自有一種執著、一種從容和一種深度,這又使他形成了一種格局。他能始終保持一種獨立的姿態,但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精英意識,而是與底層同患難、共富貴之外的遠景凝視:底層將如何發展?現代性進程給底層帶來了什么?底層的最終歸宿又在何處?因為被這些問題所困擾,賈平凹的底層表述便有了長久的驅動力,這使他無法停止,無法不時時思考底層的命運流變,無法不以自己的筆來言說底層,他三十多年來的創作實踐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一個為奧凱西畫像的威爾士藝術家曾給奧凱西寫信,質疑他為什么把自己的創作和一個“階級”捆綁在了一起,并勸他作為一個詩人和藝術家不應該屬于任何階級。《西恩·奧凱西傳》的作者大衛·克勞斯,替奧凱西做了這樣的回應:“對于某些為藝術而藝術的,且有獨立經濟來源的美學家文學家來說,這樣一種超然的藝術觀或許是很不錯的;但對于奧凱西來說,倘若他不是一個富于正義感的人,憑借自己的經歷和信念使自己始終與工人階級休戚與共的話,他就根本不會成為一位藝術家了。對他來說,不隸屬任何階級的藝術家或不隸屬任何階級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在他看來,藝術家對他的同胞所肩負的責任應當更大于普通人,而這種責任又與他對藝術肩負的責任密切相關,無法仳離。”⑩
我們在此引用這個故事,是因為大衛·克勞斯的回答也許對說明西部作家的創作與“底層”這個階層的關聯是再恰當不過的了。自柳青以來,底層意識就一直左右著西部作家的創作,他們以富于正義感的聲音為改善底層的境遇而呼吁。他們不可能去創作某種“純藝術”的東西,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所書寫的每一個文字都擔負著底層的希望與訴求。他們是作家,是因為他們曾經替底層言說,或正在替底層言說。舍棄了底層,他們將寧愿沉默。
注 釋
①②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
③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6頁。
④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研究室:《列寧論文學與藝術》,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2-913頁。
⑤陳忠實:《悼路遙》,《小說評論》1993年第1期。
⑥張承志:《老橋·后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
⑦涂險峰:《神圣的姿態與虛無的內核——關于張承志、北村、史鐵生、圣·伊曼紐和堂吉訶德》,《文學評論》2004年第1期。
⑧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李自修譯:《馬克思主義與形式》,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頁。
⑨賈平凹:《高興·后記》,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⑩大衛·克勞斯:《西恩·奧凱西傳》,中國戲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