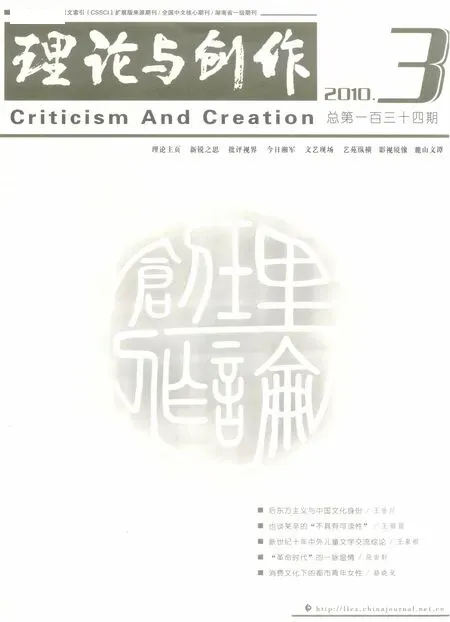安徒生童話與中國文學童話的本體論研究
■王蕾
文學童話的本體論研究就是研究什么是文學童話,文學童話的根本屬性是什么。“本體”源自哲學術語,指終極的存在,關于本體的思考就是本體論,“是在最抽象的層次上思考存在是什么、存在與思維的關系,把握人與世界的本質聯系,揭示世界的原初本質。”將哲學本體論研究運用于文學研究中,就是研究什么是文學的本體。中國早期兒童文學理論建設者圍繞兒童文學基本概念的理論辨析形成了對中國兒童文學本體的探究,并從此思路深入,探尋兒童文學的文體之一文學童話的本質、特點等,成就了一系列有關文學童話本體論的研究成果,而這些研究成果的出爐幾乎都離不開對世界文學童話的經典之作安徒生童話的解讀與言說。
五四時期,中國文壇曾出現過“童話大討論”。1924年,趙景深將這場討論中的30篇重要論文編輯成《童話評論》一書,由上海新文化書社出版。這場討論涉及了童話研究的許多領域,有從人類學與民俗學角度研究民間童話,有從教育學、兒童學角度探討教育童話,還有從文學本體的角度探討文學童話。趙景深與周作人之間展開的童話討論便涉及文學童話本體論的研究。
從1922年1月至4月,趙景深與周作人以9次通信全面展開了對童話的本體探討,這些信先后發表在1922年1月至4月的《晨報副鐫》上,并收入進1924年出版的《童話評論》一書。
1922年2月5日周作人去信給趙景深,這是他們童話討論中的第4次通信,在去信中周作人重述了自己有關民間童話與文學童話的兩大童話分類說,認為安徒生童話都是文學的童話,他認為“安徒生早年作的童話稱作eventyr(意同marchen),后來自己改稱 historier(意同stories),但這只是他個人的意見,其實他的著作都是文學的童話,雖然有許多比較的接近現實,卻也是童話中所有的分子,未必便可以歸到傳說范圍里去”。①
在1922年3月25日第7次通信中,周作人提出中國傳統故事《促織》可以作為文學的童話,指出:“《促織》可以當作‘文學的童話’,不過講給小孩子聽,興味的中心卻在那個病孩的變為蟋蟀,他父親的怎樣被杖倒反落在不重要的位子了。文學的童話的本意多是寄托,教訓或諷刺,但在兒童方面看來,他的價值卻不在此,往往被買櫝而還珠:這可以說是文學的童話的共通的運命。我想中國許多的所謂札記小說很值得一番整理研究,其中可以采用的童話材料就可以提出應用。這個辦法比較采集現代流行的童話,雖然似乎容易一點,但是文章都須重新做過,也很有為難的地方,這就是來信末節所說的問題了。”
緊接著,趙景深在1922年4月3日的復信中接著周作人所拋出的“文學的童話”的探討,以安徒生童話與王爾德童話作對比,給文學童話的特點予以概括與歸納。首先趙景深認為,要對作家創作的文學童話歸納其藝術特點只能按照其大部分的作品呈現出的特點予以歸納,因為一個人的思想或藝術,決不能說是一生沒有變遷的。這體現出趙景深理論分析的發展眼光,不用一成不變的理論分析動態發展的文學現象。隨即,趙景深對安徒生文學童話的綜合特色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安徒生童話的語言大部分是小兒說話一樣的特點,“和兒童的心相近”,但是也有一些語句太美,不像兒童的語言,比如,“《雪中王》和《白鴿》兩篇,美妙的藝術表現的尤美,小孩似乎說不出那樣美的話;即使兒童偶爾有極美妙的詩句,但最多不過四五句,大約沒有那樣多的。”②所以他認為安徒生的童話只是大部分的“小兒說話一樣的文體”。與安徒生童話的語言相比,趙景深認為,王爾德的童話“雖是內中很多深奧的語句,不是小兒說話一樣的文體,似乎是文學家的話,但是他的《幸福王子》,《利己的巨人》和《星孩兒》三篇中”,卻是“很有許多話是天真可愛的”。不過從王爾德的大部分作品來看,語言還是“非小兒一樣的文體”,常把不可捉摸的“智慧”“愛情”等等抽象的名詞插在童話里。③
在童話的思想表現手法上,趙景深認為安徒生的文學童話雖然有些地方“太玄美,兒童多不能領略”,但是大多地方還是“顧及兒童方面,用事實去推闡的多。他只將事實寫得極真切,并不用任何深奧的話”。而王爾德表現他的思想方法卻不同,是將“事實和深奧的話并用”。因此,從兩人表現思想手法的不同來看,“安徒生還要比王爾德比較的近兒童”④。
安徒生的文學童話與王爾德的文學童話從藝術表現手法、語言等方面都不盡相同,這是文學童話的本質所決定的,因為文學童話本是由不同的創作者創作而成,因此不同的創作者皆有自己不同的審美意識,所呈現出的審美創造的最終結果當然會有所不同。趙景深從安、王兩人文學童話對比出發揭示出文學童話所呈現的作家的審美個性,這是從根本上將其與民間童話相區別,因為后者由集體創作而成,大都具有語言、藝術表現手法上的套路化與模式化。因此,通過對安、王的對比研究,文學童話具有審美個性這一特點得到了很好的闡述。
此外,趙景深在對安、王童話進行對比時還指出,文學童話與民間童話相比,“若要童話最合兒童的心理”,文學童話總及不上民間童話。因為,“文學童話的本意,多是寄托教訓或是諷刺”,差不多成了“很多作者自己發表哲學的東西”。但是,“兒童聽或看童話多愛事實,事實以外的理,多不大注意的,所以童話中說理愈多,愈不能近兒童”。
趙景深所總結出的文學童話具有寓意,這與周作人此前信中所說的“文學童話的本意,多是寄托教訓或是諷刺”的觀點類似,都是從文學童話的現實性寓意角度考察文學童話的特點。文學童話由于是作家個人獨創,雖然其中包含有多種“超自然的空想分子”,卻又在其中隱藏著某種生活的影子,蘊含豐富的人生哲理,是現今生活的一種折射,融合著作家個人的愿望、理想以及獨特的主觀感受和想象,文學童話作為作家創造的精神產品,必定寄寓著作家個人的生活感受與人生思考。趙景深在探討安徒生與王爾德童話不同的審美個性之后,又對從安、王童話的共通之處總結出文學童話的兩大特點:
其一就是都是文學的童話,有所寓意;并且不是平鋪直敘,都有文學的結構。其二就是都是美的童話,他們里面的主人翁,大半都是花鳥蟲魚,用到猛獸劣樹的時候很少;并且所敘的事實,亦都趨向于美的方面。雖是有時都免不了對于社會發生哀憐,但從哀憐中卻生出樂觀來;他們那種高尚的情緒,同等的使我發生愉快。⑤
趙景深這段話中關于文學童話并非平鋪直敘的文學結構這個觀點是對文學童話敘事結構的理論認識。文學童話在敘事結構上因其不同的創作者有不同的結構特點,一般有三段式、夢幻式、歷險式、奇遇式、尋寶式、漫游式、循環式、連續式、串連式、反復式、歸繆式等⑥。但無論創作者選用何種敘事結構,其共通點便是,敘事結構力求吸引讀者的閱讀,不能平鋪直敘,如安徒生在《丑小鴨》中敘事結構主線清晰明了,沖突與高潮安排得恰當適切,將丑小鴨的成長成才過程表現得淋漓盡致,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此外,趙景深在此處用簡單的一句話“雖是有時都免不了對于社會發生哀憐,但從哀憐中卻生出樂觀來”表述了對文學童話“快樂性”這一審美追求的認識。其實在與周作人童話討論的這10封信寫作之前的一個月,趙景深曾寫過一篇《安徒生評論》(后來亦收錄進《童話評論》中),在那篇文章中他借安徒生童話的解讀,更為詳細地表述了文學童話的快樂性美學追求。他指出,安徒生的童話,“大半含有極豐富的詩歌意。我以為兒童好似初開放的花,正是蓬蓬勃勃,大有朝氣的時候,應該讓他快樂,不應將煩悶的事接觸他。而心靈上的愉快,又須自然顯示給他。所以我愛他的童話,第二是因為他以自然的現象,增加兒童心理上的快感”。⑦
趙景深對安、王的童話進行比較研究之后,又將西方文學童話在當時的演變發展予以介紹,他寫道:
安徒生以后有王爾德,王爾德以后又有愛羅先珂,就文學的眼光看來,藝術是漸漸的進步。思想也漸漸進步了!但就兒童的眼光去看,總要覺得一個不如一個。或者以這樣的步趨——安王愛——供給漸長的兒童——自童年至少壯年——倒還容易引起他們愛好一些。⑧
周作人針對趙景深上述這些有關文學童話的理論闡述,在4月6日的回信中,提出文學童話中的“成人世界”、“兒童的世界”與“第三的世界”三個概念界說。周作人認為,王爾德的文學童話里創造出來的世界是“在現實上復了一層極薄的幕,幾乎是透明的”⑨,讀起來總覺得很漂亮、輕松,而且機警,也很愉快,但是有苦的回味,這便是“成人的世界”。安徒生的一部分作品“因了他異常的天性”,能夠復造出“兒童的世界”,但大部分作品所創造的世界是“超過成人與兒童的世界,也可以說是融和成人與兒童的世界”⑩,這就是文學童話的“第三的世界”。周作人還認為“第三的世界”是最理想的境地,因此“文學童話到了安徒生而達到理想的境地,此外的人所作的都是童話或一種諷刺或教訓罷了”?。
周作人此處所提出的三個世界的概念實際上已觸及到有關童話創作中的審美意識理論,只是他用“世界”這一術語來表述罷了。我們知道,審美意識是指存在于社會群體的比較穩定的審美觀念,是審美主體對審美客體存在的美丑屬性的反映。童話作為兒童文學文體之一,也由成年人創作出來以供兒童閱讀,因此創作者與接受者具有從客觀上便存在差異的兩種審美意識,即成年人審美意識與兒童審美意識。當成年人是按照成年人的意識進行創作,那么創造出的童話世界便仍然是“成人的世界”;如果成年人完全按照兒童的審美意識創作,那么創造出的將是“兒童的世界”;只有當成年人理解、把握和提升兒童的審美意識,也就是如周作人所說的“超過成人與兒童的世界,也可以說是融和成人與兒童的世界”,才能創造出真正的“第三的世界”,這“第三的世界”是文學童話的最高境界。正如茅盾所說“兒童文學最難寫。試看自古至今,全世界有名的作家有多少,其中兒童文學作家卻只廖廖可數的幾個”?。兒童文學難寫的關鍵便在于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在審美意識上存在的客觀差異。周作人從安、王的具體作品特點中看到了這種差異,并將其上升為三個世界的理論界說,這對中國現代童話的理論發展具有深化的作用。
趙景深與周作人在以安徒生童話為主的外國童話的解讀與分析中,重點對文學童話的本質、美學追求、審美意識等一系列蘊含深厚學術價值的問題予以關注與闡述,對于文學童話理論的深入系統研究起到了積極與巨大的作用。
注 釋
①②③④⑤⑧⑨⑩?周作人,趙景深:《童話的討論》,王泉根編:《周作人與兒童文學》,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頁、第96頁、第97頁、第97頁、第97頁、第97頁、第98頁、第98頁、第98頁。
⑥蔣風:《兒童文學原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頁。
⑦趙景深:《安徒生評傳》,《童話評論》,上海新文化書社1924年版。
?茅盾:《60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上海文學》196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