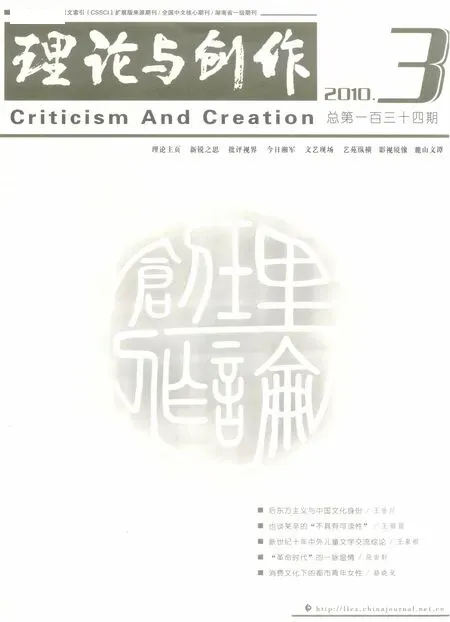重訪愛麗絲的奇境世界:兒童文學經典的啟示?
■舒偉
一、說不盡的奇境
2010年3月,由蒂姆·伯頓執導的IMAX 3D電影大片《愛麗絲夢游仙境》與公眾見面,再次引發了人們對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兩部“愛麗絲”小說的關注。作為英國兒童文學黃金時代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愛麗絲”故事不僅在紙質媒介和印刷文化的時代(人類文學創作的高峰階段)引領風騷,而且在21世紀的數字化傳媒時代(圖像、影視、網絡及數字化新媒介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仍然具有激進的潛能,原因何在?這無疑是當今兒童文學研究領域應當大力探究的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的問題。首先讓我們簡略回顧一下一個多世紀以來人們通過不斷的闡釋和重新述說而表現出來的對于“愛麗絲”的關注。一方面是批評家和學者們進行的理論闡釋和發現,另一方面是作家、藝術家們以模仿、改寫、續寫、重寫等形式進行的文字闡釋以及以影像藝術形式出現的影視敘事。在19世紀后期,兩部“愛麗絲”小說的發表對許多與劉易斯·卡羅爾同時代的,以及后來的作家產生了很大影響,出現了競相效仿的熱潮:吉恩·英格羅(Jean Ingelow)創作了《仙女摩普莎》(M opsa the Fairy,1869)講述男孩杰克在一個樹洞里發現了一群仙女,結果他騎在一只信天翁的背上,跟隨她們去往魔法仙境,經歷了一場奇遇;克里斯蒂娜·羅塞蒂(Christina Rossetti,1830-1894)不僅自己創作了童話敘事詩《妖精集市》(Goblin Market),而且寫了《異口同聲》(Speaking Likeness,1874),講述少女弗洛娜參加一個波瀾橫生的生日舞會,她奪路而逃,卻跑進了一個幻想世界,在那里她發現那些自私孩子的所有令人厭惡的特點都以“異口同聲”的方式被人格化了;莫爾斯沃思夫人(M rs M olesworth)的《布谷鳥之鐘》(The Cuckoo Clock,1877)講述孤獨的女孩格瑞澤爾達遇到一只會說話的布谷鳥,結果在它的帶領下進行了幾次歷險;G·E·法羅(G.E.Farrow)的《沃利帕布的奇異王國》(W allypub ofW hy,1895)講述女孩格莉被她的布娃娃帶走了,帶到一個叫做“為什么”的地方,那里發生的事情是奇異而顛倒的。沃利帕布本是那里的國王,但他卻被自己的臣民所管轄,還要稱呼他們為“陛下”。艾麗斯·科克倫(Alice Corkran)的《雪域之梯》(Down the Snow Stairs,1887)講述自私的女孩基蒂被一個雪人帶到魔法世界,在那里她的不良行為得到矯正。她重返現實世界后決心痛改前非,善待自己家中瘸腿的兄弟;此外還有E·F·本森(E.F.Benson)的《戴維·布萊茲和藍色之門》以及查爾斯·E·卡瑞爾 (Charles E.Carryl)、艾麗斯·科克倫(Alice Corkran)、愛德華·阿博特·帕里(Adward Abbott Parry)等人的作品。漢弗萊·卡彭特等在《牛津兒童文學指南》中指出,這些仿效之作都沒有達到《愛麗絲奇境漫游記》的藝術高度,后者顯示的是幻想文學的“無限的可能性”,是難以仿效企及的。在20世紀出現的仿寫、改編和續寫以及影像表現包括中國作家沈從文的《阿麗思中國游記》(1928);中國作家陳伯吹的《阿麗思小姐》(1933);美國真人實景影片《愛麗絲奇境漫游記》(1933);迪斯尼動畫片《愛麗絲奇境漫游記》(1951);英、法、美合拍的真人實景與木偶混合版影片《愛麗絲奇境漫游記》(1951);英國電視片《愛麗絲奇境漫游記》(1960,1966);美國電視片《愛麗絲鏡中世界奇遇記》(該片將兩部“愛麗絲”小說的情節與《奧茲國的魔法師》的情節糅合起來,1960);英國影片《愛麗絲奇境漫游記》(1972);美國電視片《愛麗絲奇境漫游記》(1985);蘇珊·桑塔格的舞臺劇劇本《床上的愛麗絲》(1993);麥琪·泰勒的新數碼插圖版《愛麗絲奇境漫游記》(2008);蒂姆·波頓執導的3D版真人實景與木偶混合影片《愛麗絲夢游仙境》(2010)……
人們為什么會對“愛麗絲”故事表現出如此持久的興趣和關注呢?它能夠為我們的兒童文學研究者提供什么啟示呢?
二、“愛麗絲”走進奇境世界
在成為《愛麗絲奇境漫游記》的作者之前,人們所認識的劉易斯·卡羅爾(Lew isCarroll)名叫查爾斯·路特威奇·道奇森(Charles Lutw idge Dodgson,1832-1898),是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的數學教師。查爾斯·道奇森于1832年出生于英國柴郡達爾斯伯里的一個牧師家庭。在小查爾斯11歲那年,全家搬到位于約克郡的克羅夫特居住。查爾斯自幼聰慧,興趣廣泛,而且多才多藝,尤其在文字寫作方面表現出特別的興趣和愛好。從1846年至1850年,查爾斯在約克郡的拉格比公學(Rugby)讀書,隨后考入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讀書。在大學念書期間,他以全班數學第一的成績畢業,并由此獲得一份獎學金,成為數學專業的研究生和助教,并最終留校任教。道奇森從1855年就開始向《喜劇時代》雜志(the Com ic Times)投稿,該雜志后來改名為《列車》(the Train)。1856年,道奇森創作的一首名為《孤寂》(Solitude)的詩作刊登在《列車》雜志上,署名為“劉易斯·卡羅爾”(Lew isCarroll),這是編輯從他本人提供的幾個筆名中敲定的,是從他的本名Charles Lutw idge Dodgson演繹而來。關于“愛麗絲漫游奇境”的創作緣由及過程是英國文學史上具有浪漫色彩的傳說之一。1862年7月4日,一個金色的午后,卡羅爾和他的朋友,牛津大學的研究生羅賓遜·達克沃斯(他后來成為西敏寺大教堂的教士)一同帶著基督堂學院院長利德爾膝下的三姐妹泛舟美麗的泰晤士河上,進行了一次慣常的漫游。那一年卡羅爾三十歲,風華正茂;愛麗絲小姐十歲,天真可愛。根據兩部“愛麗絲”小說的注釋作者馬丁·加德納(M artin Gardner)對此次郊游所做的詳細注解,①卡羅爾一行乘坐的小舟從牛津附近的弗里橋出發,抵達一個叫戈德斯通的鄉村,行程大約是三英里;然后五人上岸歇息、喝茶。這次泛舟之旅之所以意義重大,是因為三個小姑娘不僅像往常一樣,要求卡羅爾給她們講故事,而且在旅游結束后,二小姐愛麗絲突然提出要求,請卡羅爾先生為她把講述的故事寫下來。據卡羅爾當天日記所載,他們晚上8點1刻返回基督堂學院,還一同在卡羅爾的房間里觀看了他的縮微放大照片集,然后三姐妹被送回家中——正是在互道晚安時,愛麗絲向卡羅爾提出將講述的故事寫出來的請求。多年后,卡羅爾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形以及故事手稿的誕生,他說那是“無法抗拒的命運的呼喚”。在那些令人愉快的郊游中,卡羅爾為利德爾姐妹講了許許多多的故事,“它們就像夏天的小昆蟲一樣,喧鬧一場,又悄然消亡。這一個又一個故事陪伴著一個又一個金色的午后,直到有一天,我的一個小聽眾請求我把故事給她寫下來。”卡羅爾回顧道:“多少次我們一同在靜靜的河水中劃船游玩——三個小姑娘和我——我為她們即興講述了多少個童話故事……頭上是湛藍的晴空,船下是明鏡般的河水,小舟輕輕地蕩漾在水中,翻動的劃槳上閃動著晶瑩剔透的水珠,三個小女孩急迫的眼神,渴望那來自童話奇境的故事。”為了讓自己熱愛的孩子們得到快樂,卡羅爾費盡心機,信口講述:他把女主人公送進了兔子洞——這就是故事的開端——至于后面將發生什么事情他還沒有想好;好在卡羅爾深諳童心,才思泉涌,雖即興發揮,故事卻從心到口,源源不斷地流淌而出。卡羅爾不僅讓愛麗絲成為故事的主人公,而且將當時船上的幾個人也都編進了故事當中。利德爾姐妹中的大姐洛瑞娜(lorina)變成了小鸚鵡(Lory),小妹伊迪絲變成了小鷹(Fagiet),羅賓遜·達克沃斯(Duckworth)變成了母鴨(Duck),當然他本人則變成了一只渡渡鳥(Dodo)。而在此后兩年間,為了讓他所熱愛的孩子得到快樂,他把故事寫了下來,打印成手稿,還配上自己畫的插圖,取名為《愛麗絲地下游記》,在1864年將它作為圣誕節禮物送給愛麗絲(后來卡羅爾又從愛麗絲那里借用了這部手稿,使之在1885年以影印本的形式出版)。卡羅爾告訴人們,在記述故事的過程中,他增加了許多新的構思,“它們似乎從頭腦中涌現出來,涌進原來的故事當中”。在完成手稿《愛麗絲地下游記》以后,也許是對自己的杰作不無得意之處,他在將手稿本贈送給愛麗絲之前借給幾位朋友傳閱。在作家喬治·麥克唐納家中,麥克唐納太太為孩子們朗讀了這部手稿的故事,很受歡迎。所以麥克唐納力勸卡羅爾將書稿充實一下,送交出版社出版。于是卡羅爾對手稿又進行了擴充(增加了“小豬與胡椒”一章中關于公爵夫人廚房的場景,以及“癲狂的茶會”一章中的瘋帽匠的癲狂茶會)、修訂和潤色。《愛麗絲漫游奇境記》終于在1865年正式出版。七年以后,《愛麗絲鏡中世界奇遇記》(Through the Looking-Glass,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出版。從整個創作過程來看,“愛麗絲”故事一方面體現了口傳童話故事的民間文化因素(現場性,親密性,互動性),另一方面體現了作者文字加工后的藝術升華,這兩者的結合體現的是歷久彌新的童話本體精神與現代小說藝術相結合的產物。隨著時光的流逝,這兩部“愛麗絲”小說以豐富的內涵征服了越來越多的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領域的學者,同時以獨特的藝術魅力征服了不同時代,不同年齡的讀者。
三、心靈的激情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在特定意義上進入了一個“進步”(工業革命,物質進步與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與“退縮”(退回內心,懷念童年)齊頭并進的時代。在包括工業革命的社會影響與重返童年的懷舊思潮等多種時代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這一時期的諸多英國一流作家開始有意識地關注兒童和童年,乃至于為兒童和童年而寫作。②童年的重要性在維多利亞時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顯。書寫童年,反思童年,或者以童年為媒介而進行創作成為一種潮流。羅伯特·波爾赫默斯(RobertM Polhemus)在論述“劉易斯·卡羅爾與維多利亞小說中的兒童”時將夢幻敘事及幻想文學與童年聯系起來,闡述了卡羅爾創作的小女孩愛麗絲作為維多利亞時代小說中的兒童主人公的意義,表明兒童成為小說作品之主人公的重要性,而且闡述了卡羅爾筆下的小女孩主人公是如何與其他重要的小說大家所創作的兒童和童年相關聯的。當然,卡羅爾之所以書寫童年是與小女孩愛麗絲息息相關的。如果說貝特麗絲是激發但丁創作激情的女神繆斯,是《神曲》中引導作者進入天堂的集真善美于一身的指引者,那么人們可以把愛麗絲看做激發卡羅爾創作靈感和激情的貝特麗絲,在特定意義上正是她引導卡羅爾進入了地下奇境和鏡中世界,使他以自己的才情去探幽訪勝,神游萬仞。
現實中的小女孩愛麗絲是激發卡羅爾心靈激情的女神繆斯,這是毋庸置疑的。但這樣的解釋顯得簡單化了。卡羅爾對于天真爛漫的小女孩的熱愛在愛麗絲身上得到聚焦,隨后通過“愛麗絲”小說的創作得到釋放和升華;我們可以借用著名紅學專家周汝昌先生對《紅樓夢》藝術的研究成果來審視卡羅爾創作后面的深層因素。簡言之,周汝昌先生認為《紅樓夢》藝術貫穿了獨特的玉、紅、情“三綱”文化因素。“玉”乃萬匯群品,獨具靈性的玉石;“紅”乃作為七彩之首的紅色,代表鮮花和少女;情乃為“普天下女子”的不幸而痛哭流淚的深邃博大的深情。用周汝昌先生的話說,曹雪芹要犧牲一切而決心傳寫他所親見親聞的、不忍使之泯滅的女中俊彥——秦可卿所說的“脂粉隊里的英雄”。正是這樣博大深邃的情懷使曹雪芹寫出了中國最偉大的文化小說。《紅樓夢》作者的心靈激情是一種為眾多花季少女的不幸命運而痛哭的悲情。在《紅樓夢》第五回中,賈寶玉隨賈母一行到寧府花園去賞花游玩,一時感到疲憊思睡,于是賈母令人帶寶玉去歇息一回。結果寶玉去了賈蓉之妻秦氏(秦可卿)的房里歇息,一覺睡去,進入夢鄉,在警幻仙姑的引導下游歷了一番太虛幻境。在夢游中他預覽了幾位女主角(寶釵、黛玉、湘云、妙玉)的結局以及其他女子的最終命運。其間小丫鬟捧上的清香之茶“千紅一窟”和甘冽之酒“萬艷同杯”是具有象征意義的,被認為揭示了整部《紅樓夢》的主題意旨:“千紅一窟”即“千紅一哭”的諧音,“萬艷同杯”乃“萬艷同悲”的諧音。劉鶚(1857-1909)在《老殘游記》的“自敘”中說“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他認為《離騷》是屈原的哭泣,《莊子》是莊生的哭泣,《史記》是司馬遷的哭泣,《草堂詩集》是杜甫的哭泣。……王實甫寄哭泣于《西廂記》,曹雪芹寄哭泣于《紅樓夢》。……曹雪芹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萬艷同杯”者,千芳一哭,萬艷同悲也。劉鶚的見解有獨到之處,人類與動物的區別在于前者擁有靈性所滋生的深邃情感。那些千古杰作乃是長歌當哭的藝術結晶。以此而論,卡羅爾之所以寫出兩部英國最杰出的,難以被超越的童話小說,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作者的創作動機發自內心肺腑的深情,或曰心靈的激情。雖然“愛麗絲”故事以荒誕奇趣而著稱,卡羅爾也被稱作講荒誕故事的癡呆的數學家,但人們卻解出了其中意,認識到了愛麗絲故事的奧妙和旨趣,認識到了作者精神層面的“洛麗塔”情結。卡羅爾對于兒童,尤其是小女孩懷有特殊的情懷,與她們的交往和友誼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正如他本人所說,她們是“我生命中的四分之三”。而在維多利亞時代,文學作品反映出作家們將小女孩的美貌和童貞理想化的一種傾向。卡羅爾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對于小女孩的熱愛在愛麗絲身上得到最集中的體現,這種熱愛是對于許許多多天真爛漫的小女孩的純真玉容的珍視,而她們對卡羅爾故事天才的崇拜也使他得到人生最大的寬慰與滿足。童年是美好的又是流逝的,對逝水流年的惋惜轉化為內心的激情,卡羅爾與小女孩的對話是安徒生式的成人意識與童心的交流,是人生最美好的回憶——如何才能留住童年,留住美好回憶呢?回答就是用愛麗絲漫游奇境世界和鏡中世界的故事將所有的遺憾和感傷化為一曲詠嘆“夏天”的絕唱。這就是莎士比亞那首著名的十四行詩(第十八首)抒發的情懷,其精湛的詩藝表達了詩人無限的深情,可用以題解卡羅爾心靈的激情:
我能把你比作夏天嗎?/你比夏天還要溫柔可愛:/五月的狂風摧折了嬌艷的花蕾,/夏天的逗留實在是太短太短:/蒼天的驕陽有時酷熱難當,/那金色的面容時常云遮霧擋:/世間的美艷終將凋謝零落/或受制于機緣或屈從于時輪運轉。/但你永恒的夏天卻不會消逝,/你的玉容倩影將永留人間;/死神也難夸口說你在他的陰影中闖蕩,/只因為你的生命流淌在我不朽的詩行。/天地間只要有人呼吸,有眼能看,/這詩就流傳,就讓你永恒。
譯詩中的“夏天的逗留實在是太短太短”得之于周煦良先生的譯句,這是出現在高爾斯華綏著《福爾賽世家》第一部《有產業的人》的尾聲“殘夏夕照”中的莎士比亞詩句。這個尾聲描寫的是福爾賽家族中正直倔犟的老喬里恩在生命盡頭的一個美麗抒情,令人感傷的人生插曲。夏天是英國最美好的季節,正是在這樣的季節里,老喬里恩邂逅了前來憑吊亡人的少婦艾琳。老人在生命暮年的愛美之心和惜香憐玉之情使他與艾琳成為忘年之交。面對一個外貌美,心靈也美的年輕異性,真可謂“觀其容可以忘饑,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而談宴時而出游,“色授神與”,大慰平生;但也恰恰是這段交往為老喬里恩的生命提前畫上了最后的句號。這個“愛美之心”的插曲是小說中最抒情,最感人的描寫。當年30歲的卡羅爾與當年10歲的愛麗絲亦是忘年之交,他把自己融進了愛麗絲故事,把這段友情化作了永恒的夏天。在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中,詩人先將友人比作夏天,轉而敘述夏天比不上友人,因為自然界的夏天有諸多不如意之處。物換星移,生命變老本是自然規律,但詩人的情感和文筆卻能產生奇跡,因為友人的生命流淌在詩人不朽的詩句之中,化作永恒的夏天。對卡羅爾亦是如此,兩部“愛麗絲”小說將流逝的童年和難忘的友情化作永恒的奇境漫游,成為英國兒童文學永恒的夏天。
四、開拓幻想文學的新疆界
羅伯特·波爾赫默斯在《劉易斯·卡羅爾與維多利亞小說中的兒童》一文中指出,卡羅爾為藝術,小說和推測性思想拓展了可能性。卡羅爾的開拓性創作不僅體現在兒童文學領域,而且深刻地影響了成人文學。正如波爾赫默斯所說,通過創造“愛麗絲”文本,卡羅爾成為一個人們可以稱為無意識流動的大師。他指明了通往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道路。④波爾赫默斯這樣論述道:“從卡羅爾的兔子洞和鏡中世界跑出來的不僅有喬伊斯、弗洛伊德、奧斯卡·王爾德、亨利·詹姆斯、弗吉里亞·吳爾夫、卡夫卡、普魯斯特、安東尼·阿爾托、納博科夫、貝克特、伊夫林·沃、拉康、博爾赫斯、巴赫金、加西亞·馬爾克斯,而且還有20世紀流行文化的許多人物和氛圍”。從兒童文學的視野看,“跳進了兔子洞”意味著進入了幻想文學的奇境,由此形成了兒童幻想文學從現實世界進入幻想世界的一個重要模式(從《納尼亞傳奇》的魔櫥到《哈利·波特》的神秘的火車站莫不如此)。同樣書寫童年,同樣將19世紀的兒童作為小說創作中的主角,卡羅爾的貢獻是革命性的,無以替代的。他不僅用幻想文學的藝術形式來書寫童年,拓展了兒童文學的新疆界,而且通過描寫主人公的意識和無意識活動,通過愛麗絲的反思和憤慨來顛覆說教文學,顛覆成年人讓她遵從的教訓和常規。如果把同時代的文學大師狄更斯的書寫童年的小說與卡羅爾的“愛麗絲”小說比較一下,人們就能夠更清楚地認識卡羅爾的特殊貢獻。關于狄更斯,波爾赫默斯指出:“正是查爾斯·狄更斯,而不是任何其他作家,使兒童成為信念、性愛和道德關注的重要主題;作為一個小說家,狄更斯所做的貢獻沒有什么比他對于兒童的描寫更具影響力的。……通過他自身童年受到傷害的經歷,狄更斯將兒童的浪漫的形象銘刻在無數人的想象之中,促使人們去感受和認同于遭受傷害和壓榨的孩子們,認同于人生早期歲月的心理狀況。”如果說狄更斯再現的是真實的童年經歷的記憶,那么卡羅爾則以幻想文學的藝術形式超越了這些記憶。波爾赫默斯認為,狄更斯等作家在追溯童年時試圖回答兩個問題:1.我是怎樣成為現在的我?2.我的童年是什么樣的童年?而卡羅爾探尋的是如何才能消解自我,消解成年,如何才能回歸童年,甚至重新成為一個小女孩?卡羅爾的回答是,富有想象力地走進小女孩愛麗絲的世界。具體而言,卡羅爾采用夢幻敘事的方式讓愛麗絲引領我們走進夢幻般的奇境世界,隨著愛麗絲的“意識流”來重返童年。在心理分析學家看來,童年的精神特征體現為自我中心,無法區分自我和他者,萬物有靈,等等,所以在愛麗絲的世界里所有動物、植物、撲克牌和象棋子等等都是有生命的,能說會道,活靈活現。這里發生的一切事情,出現的一切物體都像是夢中的境遇,都是漫游者(做夢人)的組成部分。夢幻敘事可以將人類普遍的主觀思緒和情感轉化為可視的意象。而那些想象出來的,陌生化的奇境、夢境和困境等在人們的腦海中喚起了“似曾相識,依稀能辨,甚至非常熟悉的”感覺,所以從心理分析的視角看,它們就代表著人生的境遇、沖突、恐懼、困惑、欲望、挫折、自我寬慰等等現實中存在的現象,因而具有一種絕妙的心理真實性。一方面,愛麗絲是一個普通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小女孩,她代表常識和理性的視野;另一方面她又是一個不乏主見的,具有批判精神和反抗精神的顛覆者,所以她敢于頂撞那個專斷暴虐,動不動就下令“砍掉”別人腦袋的王后。通過愛麗絲的視野,卡羅爾戲仿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生活邏輯(茶會、宴會、槌球賽,國際象棋賽,等等),以荒誕藝術的形式表達了作者對兒童權利的捍衛和對成人威權的反抗。“愛麗絲”小說的“顛覆性因素”還表現在以夢幻(噩夢)的境遇或者帶有后現代主義色彩的錯位來顛覆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對于理性、道德或者現實秩序的自信,以及對于敘述、時間、或者語言等方面的自信。在語言實驗方面,兩部“愛麗絲”小說中出現了許多作者自撰的詞語及語言游戲。例如在《愛麗絲鏡中世界奇遇記》的第一章,愛麗絲在進入鏡中屋后看到的那首反寫的怪詩“杰布沃克”(Jabberwocky)必須通過鏡子才能閱讀。至于書中眾多的“提包詞”(混成詞)更是一大特色。
重返童年而又超越童年,兩部“愛麗絲”小說體現了童話小說的雙重性,從而使之具有強大的潛能,正如19世紀末麥克唐納在《奇異的想象力》(The Fantastic Imagination,1893)一文中對童話藝術特征的描述:“一旦從它的自然和物理法則的聯系中解放出來,它潛在的各種意義將超越字面故事的單一性:童話奇境將成為一個隱喻性,多義性的國度,在這個奇妙的國度,‘藝術越真實,它所意味的東西就越多’”。③“愛麗絲”小說是兒童本位的(為兒童創作講述,創作動機就是為了取悅于特定的聽故事的兒童),是作者與童心和童年對話的結果;但它們又是博大深邃的,能滿足成人的審美需求和心智需求。
作為英國童話小說的經典之作,兩部“愛麗絲”小說不僅具有奇趣,而且富于象征性、哲理性、荒誕性和審美性,是開放性和對話性的文本。這是一個難以說盡的奇境世界,但有一個啟示是清楚的,那就是批評家C·N·曼洛夫(C.Manlove)所說的最優秀兒童文學作品的特征:
那些為兒童創作的最優秀作品是由那些似乎忘記了自己究竟為誰而寫的作者創作出來的,因為話語的成人世界與兒童世界如此完美地融合起來:霍林戴爾稱之為“童心童趣”;當劉易斯·卡羅爾在創作愛麗絲故事之前和之后,用一種成人的聲音談論童年的奇事異趣,當他將《西爾維亞與布魯諾》呈獻為對一個早慧嬰孩的頌揚之作時,他是笨拙的,窘迫的;而當他馳騁想象,全神貫注于愛麗絲故事時,多少年的歲月流逝都不會使他的光芒暗淡下去。
這無疑是“愛麗絲”小說給我們提供的最重要的啟示之一。
注 釋
①加德納在他的注釋里引用了卡羅爾當天的日記及二十五年后的回憶;愛麗絲本人的兩次講述;愛麗絲的兒子有關他母親回憶情形的文章;以及當天同行的羅賓遜·達克沃斯的回憶文章;加德納還記述了他于1950年在倫敦氣象局查詢有關1862年7月4日天氣記載的詳情及相關說明。見Martin Gardner The Annotated Alice: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by Lew is Carroll.The Definitive Edition,New York:W.W.Norton&Company inc.,2000.pp.7-9.
②有關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作家的懷舊思緒,參見舒偉:《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童話小說崛起的時代語境》,《外國文學評論》2009年4期。
③轉引自Mendelson,M ichael.The Fairy TalesofGeorge MacDonald and the Evolution of a genre in M cGillis,Roderick editor.For the childlike:George MacDonald's fantasies for children.London: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Metuchen,N.J.:Scarecrow Press,1992,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