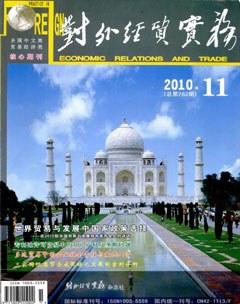中國企業海外鐵礦資本大布局
畢 夫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天河學院
中國企業海外鐵礦資本大布局
畢 夫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天河學院
伴隨著國際市場鐵礦石價格一輪又一輪的飚升,中國鋼鐵企業正在不斷承受著成本劇增和利潤擠壓的殘酷煎熬,特別是在國內鐵礦石供給短缺且增量有限的市場環境中,無數中國企業正陷入為國外鐵礦石供應商兇殘綁架并可能窒息而死的窘境。因此,為了擺脫這種受人操控與宰割的痛苦生存狀態,已經覺醒的中國企業開始走上了在全球搜尋和圍獵鐵礦石資源的投資之路。
倒逼出來的無奈選擇
自從2005年作為一個重要的買方談判代表坐到國際鐵礦石價格的談判桌上以來,中國鋼鐵企業除了忍受著巨大的心理考驗和壓力之外,還客觀上承受了連續5次談判失敗和為人殘酷宰割的痛苦與煎熬。資料顯示,從2005-2009年的短短5年間,中國鋼鐵企業無奈接受國際鐵礦石生產商的漲幅要價累計達200%,而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指出,由于談判失敗,中國企業過去5年的損失高達7000億元人民幣。
2010年的鐵礦石談判以中國企業再次敗北而劃上了句號。中國鋼企不僅接受了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等三大鐵礦石供應商(以下簡稱“三大鐵礦”)100%的漲幅要價,而且被中國企業看好的價格長協機制也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季度合約定價機制。這就意味著,中國企業不僅要接受更痛苦的盤剝,而且還要經受鐵礦石價格劇烈波動的考驗。
消費者就是上帝。作為全球鐵礦石消費量和進口量最大的國家,中國理應在全球鐵礦石價格的定奪上具有話語權,但實際并非如此。資料顯示,近年來,中國每年鐵礦石進口都在5億噸左右,占到全世界 70%左右。特別是2009年,中國進口鐵礦石達6.28億噸,創造了歷史上增加數量和增長幅度的最大記錄。而正是由于巨大的鐵礦石需求量,中國企業才自暴談判短板,同時使國際鐵礦石生產商獲得了穩定的要價籌碼。
構成中國鐵礦石需求的巨大力量來源于國內鋼鐵業的重復性膨脹。數據顯示,2004年中國粗鋼產量2.82億噸,而2009年粗鋼產量則達5.68億噸,增長2.01倍。作為鋼鐵業中鐵礦石的消耗大戶,中國粗鋼生產中約62%至69%的鐵礦石需求主要來自進口,這也就是說,中國鐵礦石對外依存度達62%至69%。中國鋼產量的快速增長和鐵礦石進口量的激增,帶動國際鐵礦石價格坐上了云霄飛車。
許多人天真地認為中國企業應該通過更多地使用國內鐵礦石以形成對進口鐵礦的替代,但只要將目光轉移到國產鐵礦石的身上,這種觀點就會不攻自破。的確,中國國內的鐵礦石儲量并不算貧瘠,其中2009年的產量就達8.8億噸,相比于2004年增長了2.8倍。但是,中國鐵礦資源的80%都屬于貧礦類別。以我國探明的單礦床規模最大的鐵礦資源產地之一鞍山礦區為例,除極少富礦外,該礦區約占儲量的98%為貧礦,含鐵量20%-40%,平均30%左右。至于全國鐵礦礦石的平均品位目前更是低至 17%-18%。而作為同樣的指標,澳大利亞、巴西等地的鐵礦石品位則達到了60%以上。大量的貧礦生產過程不僅對鋼鐵的生產設備有影響,還會影響鋼鐵企業的生產效率,這讓許多鋼鐵企業寧愿走出國門,花高價購買國外的優質鐵礦石。
但是,受制于人的日子不僅現狀悲愴,而且未來也不會出現意外的好結果。在與國際鐵礦石生產商過招的過程中,中國企業突然發現,同為鐵礦石資源貧乏并且主要依賴進口的日本鋼鐵企業不僅在談判過程中游刃有余,而且對屢次近乎被剝奪式的談判結果處之泰然。答案自然非常地簡單,即日本的鋼鐵企業從上個世紀 60年代開始就參股到國外鐵礦石上游企業。根據國際金屬和礦產工業的權威機構AME提供的資料,在澳大利亞24個主要的鐵礦中,8個有日本公司直接參股,其余的16個鐵礦日本的企業也間接參股;在巴西的22個鐵礦中,日本公司同樣有參股。這種穩態性的資源互補機制不僅使日本獲得了可靠的海外原料供應基地,而且在鐵礦石價格近乎瘋漲的情況下,最大程度從外部轉移和稀釋了日本鋼鐵企業的成本壓力。
師夷長技。作為鋼鐵強國日本的境外權益鐵礦石目前已占到了其進口比例的60%以上,相比而言,中國企業在海外的鐵礦石權益量只有微不足道的 4000萬噸,且不足進口量的10%。因此,在國內鐵礦石資源的質量瓶頸約束之下,面對著國外鐵礦石巨頭們的瘋狂而殘酷的擄掠,中國企業唯有走上海外尋礦之路才能實現自救與自強。
瘋狂搶食的國際巨頭
印度東部的奧里薩邦和卡納塔克邦在進入 2101年以來顯得特別的惹人眼球。這里不僅招徠了韓國浦項制鐵的安營扎寨,而且世界最大鋼鐵集團安賽樂米塔爾公司也在此安家落戶。據悉,浦項制鐵準備斥資190億美元在奧里薩邦和卡納塔克邦各建一家鋼鐵工廠,安賽樂米塔爾將出資264億美在同樣的地塊上開發三個新建鋼鐵項目。實際上,鋼鐵巨頭準備的好戲不止在印度上演。浦項制鐵在印尼的 60億美元的鋼鐵廠項目將進入施工階段,印度埃薩鋼公司在卡塔爾興建的一個年產鋼材150萬噸的鋼鐵廠業已動工,淡水河谷在巴西投資 30億美元興建一家年產能為 500萬噸鋼板的鋼廠也將于2011年開工……。
針對以上現象,專家認為,伴隨著世界經濟復蘇腳步的愈來愈清晰以及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的到來,全球鋼鐵產能將進入快速擴充的通道,由此帶動鐵礦石的需求口徑的增大和伸展,鐵礦石價格未來還有相當可觀的升漲空間。正是如此,本已不平靜的國際鐵礦石市場如今更是波瀾四起——以世界著名鋼鐵企業為主要陣容的制造業巨頭在全球范圍內展開了對鐵礦石資源的密集搜羅和版圖再瓜分。
作為獲取海外鐵礦資源的能手,日本鋼鐵企業圈田占地的手法顯得格外地老練,不僅抱團出擊成為了他們不二的法門,而且將目光緊緊盯在了鐵礦資源豐富的巴西。早在3年前,日本日新制鐵、住友金屬、神戶制鋼、JFE以及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已商討決定成立一財團,合資購買國外鐵礦,當時的日本政府也出面相助,承諾提供909億美金的低息貸款支持這一計劃。如今這一計劃已經結出豐收的果粒:新日鐵等日本4大鋼廠出資約31.2億美元從巴西國家鋼鐵公司手中拿下了Namisa鐵礦40%的股份,開工不到一年,該礦的鐵礦石產量已從1800萬噸提高到3800萬噸,而待2013年該礦擴建全部完成后,新日鐵的鐵礦石自給率將超過40%。無獨有偶,三井物產在巴西也旗開得勝。今年年初,三井物產憑借其對Caemi股份的優先選購權并聯合淡水河谷,對Caemi實施了聯合收購,由于Caemi擁有MBR公司85%的股份,而MBR公司的鐵礦石產量在巴西國內排名第二,因此,日本政府估算,僅此收購就可以增加日本海外權益礦比例的2%。
試圖從中國手中奪回亞洲鋼鐵企業霸主地位的韓國浦項鋼鐵在過去半年多的時間中所展開的海外收購活動可謂有風生水起:斥資 780萬澳元收購澳大利亞Jupiter礦業公司16%股份,以共同開發西澳CentralYilgarn地區的鐵礦石;收購印度尼西亞PTMotta資源公司65%股份;與烏克蘭Metinvest集團簽訂諒解備忘錄,尋求在烏克蘭礦業和鋼鐵產業獲得新的發展。也就在日前,浦項收購了西澳大利亞的 RoyHill鐵礦公司3.75%股份,并有望進一步增持股份至15%。按照規劃,該礦山2014年開始投產,最初年產能5500億噸,屆時浦項每年可從其獲得1000萬噸鐵礦石。不僅如此,浦項正與澳大利亞、巴西或新興資源國家等中小型礦山合資開發礦產資源進行會談,如果一切進展順利,到2012年,浦項鋼鐵的鐵礦石自給率可以提高到30%。
與亞洲鋼鐵企業相比,歐洲最大的鋼鐵企業也是全球老大的安賽樂米塔爾獵取海外鐵礦石資源的力度當然毫不遜色。雖然目前安賽樂在巴西、利比里亞和塞內加爾、哈薩克斯坦、墨西哥和美國等國家已經擁有多座礦山,但其胃口并沒有得到滿足。該公司的目標是到2014年,鐵礦石年產量從目前的5500萬噸提高到1.1億噸,鐵礦石自給率從目前約50%提高到75%-85%。為此,安賽樂米塔爾今年將加快利比里亞鐵礦石項目的開發和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并爭取今年全面投產。與此同時,安賽樂正在尋求與必和必拓合資經營幾內亞的鐵礦山以及共同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業內人士預計,安賽樂可能未來將收購行動指向更加廣泛的非洲大地。
中國企業海外新陣容
鋼鐵企業無疑成為了中國企業出擊海外鐵礦石的強大排頭兵。其中,去年一年就已經鎖定30億噸海外鐵礦石資源量的武漢鋼鐵集團在進入2010年后的“跑馬圈地”步伐更加的快捷與迅敏:出資約4億美金認購了巴西MMX公司約21.52%的股份,成為其第二大股東,并獲得約6億噸資源權益;斥資6846萬美元從中非發展基金手中收購了利比里亞一處鐵礦石項目60%的股權,同時獲得該項目 25年的開發權。與武鋼相同時,鞍山鋼鐵集團從澳大利亞金必達礦業公司手中拿到了Karara磁鐵礦的終生開采權,據悉,該鐵礦預計在未來30年內年產量為3000萬噸。無獨有偶,山東鋼鐵集團也在前不久與香港洪橋集團合作獲得了巴西Salinas鐵礦項目的開發權。而根據Salinas披露的信息,該項目預計儲量62億噸。好事不斷。經過近一年的商討,重慶鋼鐵集團收購亞洲鋼鐵控股有限公司60%股權終于也在日前交割完成,雙方將聯手開發西澳大利亞資源總量達17.8億噸的伊斯坦鑫山磁鐵礦項目。幾乎同時,澳大利亞鐵礦石生產商布羅克曼資源公司宣布,與中國中鋼集團旗下的中鋼澳大利亞有限公司簽署諒解備忘錄,協議內容包括,中鋼將在布羅克曼馬里納鐵礦項目投產后的5年內,每年收購約1000萬噸的鐵礦石。
國內礦冶集團集群式參與國外鐵礦石的購買和開發成為2010年中國企業出海尋礦的一道亮麗風景線。其中,中國鐵路物資總公司以1.526億英鎊收購非洲礦業公司12.5%的股權,從而獲得了該公司在Tonkolili項目中鐵礦石至少 20年的開采機會。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出資2億美元入股澳大利亞礦業公司 Resourcehouse Ltd.并獲得該公司在西澳大利亞的一處鐵礦石項目。華東有色以12.2億美元收購伯邁資產管理公司旗下Jupiter項目100%的產權,并在今年年底完成全部收購。數據顯示,Jupiter項目鐵礦石探明儲量及控制儲量約5億噸,遠景儲量約為13.9億噸,而且該項目經簡單采選后的鐵礦均可達到65%的精礦標準。當然,在國內礦冶公司投資海外鐵礦石的案例中,中國鋁業與力拓公司的合作事件最具轟動力。前不久,雙方同時發布公告,準備成立一家合資公司,共同開發力拓在幾內亞的世界級鐵礦西芒杜項目,以中鋁在該項目的股權比例來測算,其將擁有3000多萬噸的鐵礦石權益。
令人興奮地是,在中國國有企業揚帆出海網絡鐵礦資源的同時,國內民營企業也擺開了挺進海外鐵礦石礦山的架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遼寧西洋集團出資33億元收購了俄羅斯一10億噸露天大鐵礦的全資開發權,據悉,該鐵礦將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產,如果加上西洋集團同時在當地新建的400萬噸鋼鐵廠,該項目當為目前中國在俄羅斯最大的投資項目。
按照中國鋼鐵企業協會的預測,由于中國企業積極參與海外鐵礦石資源的開發,2010年中國海外權益礦將從 2009年的 8000萬提高到1億噸以上,而且這一目標正在各路力量的推擁中變得越來越清晰:武鋼與加拿大CLM公司合作開發的總量達23億噸的鐵礦石資源從今年第一季度開始已向國內起運;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參與開發的加蓬貝林加鐵礦項目預計第二季可以向國內發貨;鞍山鋼鐵集團從澳大利亞金必達礦業公司手中拿到的Karara磁鐵礦項目也將在今年實現裝船……。
他鄉之路的暗礁與風險
物以稀為貴。在鐵礦石已經成為稀缺上游資源的生態背景中,在全球鋼鐵企業不約而同地參與到鐵礦石競爭的市場環境里,中國企業出海投資和開發鐵礦石除了可能遭遇激烈的火拼之外,還會面臨著政策法律、地域文化以及資源質量等一系列風險的考驗。
風險之一:棒打鴛鴦——資源國保護主義的干擾和阻撓。由于目前全球已進入資源高價周期,加之鐵礦資源供小于求的市場特征,鐵礦石資源國往往會借維護本國資源主權等名義或者變相提高合作開發門檻而對外國開采者或收購者進行干預和阻撓。以中國鋁業收購力拓礦權為例,雙方本已按照澳大利亞的相關法律簽署了合作條款,而且中鋁已投入128.5億美元,但是,在經過了時長4個月的審查后,澳大利亞外商投資審核委員會最終還是以不符合澳大利亞相關政策為名作出了否決中鋁收購力拓的決定。而力拓只在支付1.95億美元違約金的情況下轉身投入到了必和必拓的懷抱。同樣的故事發生在武鋼與澳礦商WPG的交易身上。按照計劃,武鋼已經與WPG簽署好了出資 4500萬澳元成立合資公司共同開發澳洲中部鐵礦資源的協議,而且武鋼還是通過參與WPG定向增發的形式獲得合資企業股權的,但這項交易卻遭到了澳大利亞國防部的否決,理由是,雙方合作開采的項目位處南澳軍事禁區Woomera之內。
風險之二:橫刀奪愛——三大鐵礦刻意干擾和攪局。排除極少數與三大鐵礦直接合資、合作之外的項目外,中國企業在海外更多地是參與其他礦山的合資開發,由此勢必會動搖三大鐵礦的壟斷地位,相應地稀釋和分解他們的談判要價能力,特別是對于中國買家收拾“臥榻之畔”的資源,三大鐵礦更會格外地警覺。也正是出于這種擔憂和考慮,鐵礦石巨頭在除了加緊合并和聯合之外,也會采用各種手段對中國企業的海外收購和入股行動進行蓄意破壞和干擾。以去年下半年中鐵物資購買澳大利亞UnitedMinerals公司股份為例,雙方已經進入談判的尾聲,但關鍵時候必和必拓半路殺出,拿出了比中方高出一倍的價錢,從而使中鐵物資與 UnitedMinerals的合作胎死腹中。從理論上推斷,無論是淡水河谷,還是澳大利亞的“兩拓”,今后可能會更加看緊自家的資源,中國企業的收購和參股行動可能會變得更加艱難。
風險之三:饑不擇食——中國企業遭遇“廢礦”和“死礦”之痛。一般而言,海外投資鐵礦石既要充分考慮鐵資源儲量、礦石品位,也要考慮物流、鐵路、港口、水電等基礎設施,每一個項目牽涉的環節十分復雜,任何一個部分的判斷失誤都會使投資方蒙受損失甚至血本無歸。從目前來看,由于不少中國鋼鐵企業片面追求資源自給率,而忽視了投資對象信息采選、財務分析和技術調查等重要的基礎性工作,致使后期的投資陷入到了入不敷出和顆粒無收的被動境地。以首鋼收購西澳馬科納鐵礦項目為例,由于缺乏論證,倉促上陣,結果得到的不僅是連國內不如的貧磁鐵礦,而且由于當地物流和基建設施的匱乏,即使少得可憐的精礦資源至今也無法運出。
風險之四:禍起蕭墻——出海企業的無序和暗斗。某種程度而言,由于目前海外投資鐵礦石成為了國內鋼鐵企業間的攀比手段,彼此之間自然就形成了明顯的競爭和壓力。而且由于國家相關部門缺乏一套有效的集中統一管理體制,境外開礦的國內企業基本上是各自為戰,缺少一個領唱者,甚至出現當一些富礦項目被中國多家企業相中后而互抬價格的現象。但反觀日本,海外資源收購多由三井物產、三菱商事這樣的商社型組織出面運作,而新日鐵等鋼鐵企業則隱居其后。
謀取鐵礦的智與能
掃描全球,盡管鐵礦石目前仍處于供給短缺狀態,但這并不否認世界范圍內鐵礦石的既有豐富藏量和可取量。如在目前以三大鐵礦已落實投資的2.7億噸項目之外,澳大利亞還有超過2.31億噸、總投資約150億美元的鐵礦項目由于勘探、資金及市場等種種原因,大多數還未進入開發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只要中國企業選擇恰當的策略和戰術,其海外鐵礦石的資本布局空間勢必得到擴張和放大。
——遴選好進入國,優化資源來源結構。
原則之一:避開資源集中型和投資回報慢的國家,如澳大利亞。由于澳大利亞鐵礦資源90%以上為“兩拓”所控制,而且其與政府的關系十分緊密,中國企業的大規模進入必然引來這些利益集團的聯合抵制。另外,雖然澳大利亞鐵礦石開采容易,但其投資到回報需要約5—10年,投資企業面臨的未來市場風險較大。
原則之二:選擇資金短缺且需求性強烈的國家和地區,如非洲、拉美。目前,非洲地區的鐵礦石資源主要分布在茂密的赤道森林和偏遠的荒漠地帶,開發難度較大,因此,非洲不少國家制定了許多引進外資開發鐵礦石的優惠政策,由此也吸引了三大鐵礦的密集關注。但是,非洲國家一直對中國企業保持著非常良好的印象,中國企業若將其選為投資對象,完全能夠受到非洲國家的歡迎。同樣,南美國家巴西由于遭受金融危機影響,許多采礦企業資金緊張,不得不作出轉讓或合資的決定,而且巴西的許多礦山項目是家族遺傳,繼承者由于不善經營、無意于礦業開發等多種原因,也擬將礦山轉讓或合資經營。
原則之三:選擇與中國關系友好的國家和周邊國家,如俄羅斯、蒙古。由于中國和蒙古的地緣關系,與印度、澳大利亞或巴西相比,蒙古鐵礦的運輸成本要低得多,而且蒙古至少還有其他20處尚未開發的鐵礦資源,政府希望在未來5年內帶來250億美元的外國投資。另外,俄羅斯作為中國的貿易伙伴國,其國內的許多鐵礦石生產商目前都想利用這一特殊的經濟貿易關系尋求與中國企業的合作,以與三大鐵礦競爭并占領中國市場。
——遴選好目標企業,提高投資的成功性。
目標之一:產能擴張的礦山。產能擴張的公司需要大量資本,在自身無法解決的前提下,就會尋找外部資金。如像巴西國家黑色冶金公司就是一例。根據該公司的擴張計劃,到2011年鐵礦石產量將達到6400萬噸,包括港口的擴建,另外還將建兩家球團礦生產廠,但其自有資金非常有限,需要外部資本共同開發。
目標之二:可以深度合作的公司。即與國外礦山合作不能僅滿足于資源的間接性共同開發,而應當獲得參與管理的權利。以中鋁公司與力拓在非洲的西芒杜項目為例,中鋁不僅向合資公司董事會委派了3名董事直接參與管理,而且獲得了合資礦山44.65%的權益。這樣中鋁既直接參與開發或勘探資源,而且可以獲得海外管理的經驗,同時能有效保證鐵礦石資源的穩定供應。
目標之三:權益有爭議的礦山。最近幾年,三大鐵礦在全球購買了很多礦山,但一直沒有開發,引起了一些國家的不滿,不少國家要求更改原始協議或者重新選擇其他投資者,雙方矛盾激化。以力拓在幾內亞的西芒杜鐵礦為例,雖然力拓擁有該礦100%的權益,但幾內亞國家礦業部對力拓的開發速度非常不滿意,并準備推翻與力拓的協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鋁業看準機會提出與力拓共同開發西芒杜鐵礦,并很快得到了力拓公司的積極回應。之所以如此,力拓主要是看重了中鋁背后的中國政府在非洲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希望借助中鋁來打開與幾內亞政府之間的僵局。
——構建戰略聯盟,延伸投資產業鏈。
戰略聯盟作為一種組織創新、更作為一種獨特的資源配置渠道,為企業實現內外資源的共享與優勢相長提供了框架。因此,國內同行在進行對外投資鐵礦石資源時應當加強聯系、溝通與協調,這樣一方面可以通過共享市場信息、技術信息,在獲得原料成本價格優勢的基礎上,提升企業的綜合競爭力,另一方面在謀求與國外礦商合作基礎之上鞏固自己的市場戰略地位。另外,由于鐵礦石礦山的投資與開發涉及到鐵路運輸、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要相關投資巨大,因此戰略聯盟可以發揮資金集中和強大的優勢,使中國企業的投資不僅僅著眼于對礦山本身的投資,還兼顧到與其相關的全產業鏈的資源合作,從而建立起與資源國利益共贏的長效機制。
——發揮政府和行業協會的作用,為企業海外尋礦創造條件。
由于鋼鐵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重要戰略地位,可以說海外尋找鐵礦的成敗,已經不僅僅關系到鋼鐵行業的整體運行,甚至會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以及國家的資源安全。從這一層面來講,現階段海外尋找鐵礦已經不是某個行業之事,更不是某幾家企業之事,甚至將其定義為“國家行動”也不為過。為此:國家首先應設立專業部門,加強集中統一領導與協調。其次,政府可考慮設立一個海外礦業風險投資基金,一并承擔海外開發的資金風險,必要時政府可以為出海企業提供財務保證。再次,行業協會在為企業提供信息服務、法律資助的同時,可以考慮與銀行合作建立海外投資專項金融服務部門,運用專業評估機制和金融貸款機制的聯合作用減少企業海外投資的盲目性。最后,國家應當建立鐵礦石的戰略儲備機制。尤其應當利用中國鋼鐵企業“走出去”的這一市場機遇進行戰略儲備,當儲備量達到一定程度時,政府不僅可以平緩礦石價格的波動,還可以增加與國外鐵礦巨頭談判的籌碼,同時達到穩定和調控鋼材價格的目標。
10.3969/j.issn.1003-5559.2010.1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