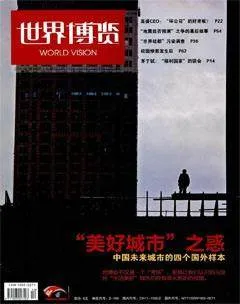在臺北看見大江健三郎
年前的某一次,我在臺北見到了大江健三郎。不止大江,還有奠言、朱天文。
這次大江健三郎的研討會被冠以“國際視野”的帽子,想必這帽子大江很喜歡,他一心反對日本的國家主義,強調“民主價值”。莫言當場說:
“大江是個脫離了狹隘民族主義、追求全人類價值的作家。”這話大江聽來肯定特別入耳。
大江于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曾在1995年買了他的兩本小說:《個人的體驗》和《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之后的新書沒再買過。大江的文字水平遠差于川端康成,雖然他挑戰川端康成的諾貝爾獲獎感言《我在美麗的日本》很成功,當時,他的獲獎演說題為《我在曖昧的日本》。我還認為,大江健三郎的小說也劣于三島由紀夫。大江其實更擅長政論和演說。
那次研討會由大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和臺灣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共同舉辦。大江說,由中國大陸和臺灣、海峽兩岸的專家們來討論一個日本人的文學,這是最榮耀的經驗。我相信這話是真心的。大江心里一定喜歡這樣的安排,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再加上日本,這糾結在一起的歷史沉淀、復雜暗示,正是大江這“東亞代表性作家”所需要的。
莫言說,大江總是說自己老了,寫的是最后一部作品,但其實這不可信。歌德78歲了還愛上了一個侶歲的姑娘。雖然他作為晚輩,不敢建議大江愛上18歲的姑娘,但建議大江安排他正在寫作的小說《死水》中的父親有這種經歷。奠言其實不用舉歌德那么遠的例子,說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就行了。
這一次大江的回應比較睿智,他說19歲時是追上了18歲的姑娘,如今這個姑娘73歲了,弄得他一見18歲姑娘,就會想象對方73歲的樣子。
朱天文和大江大談《死水》中的種種情節、意象,特別注重“天皇”這個象征。其中一種說法我頭一次聽到,說是當初日本戰敗后是聽從了人類學家的建議才保留天皇。我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在那樣一個血腥之后的灰燼時代,誰會理會學者的話。
在為人風格上,莫言、朱天文和大江確實代表了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和日本的作家。我在現場直接采訪交流的對象是奠言。這三個地方的作家待人接物的感覺確實很不同,尤其大陸作家,跟臺灣、日本作家都不同。
關于大江來臺灣的活動,有很多不知真假的幕后消息。一種說法是本來與大江對談的臺灣作家是李昂,因為大陸的壓力換成了朱天文。還有一種說法是本來列名主辦單位的還包括東京大學,也因為同樣的壓力而劃掉,因為這個活動應當是兩岸交流,而不是“國際交流”。對于這些傳言,臺灣的主辦者都明確否認,真相又成了要探究的東西。
在華人圈,“真相”總容易“不明”,再加上個“曖昧的日本”,“真相”就更成問題了。
(亢霖,自由作家,現居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