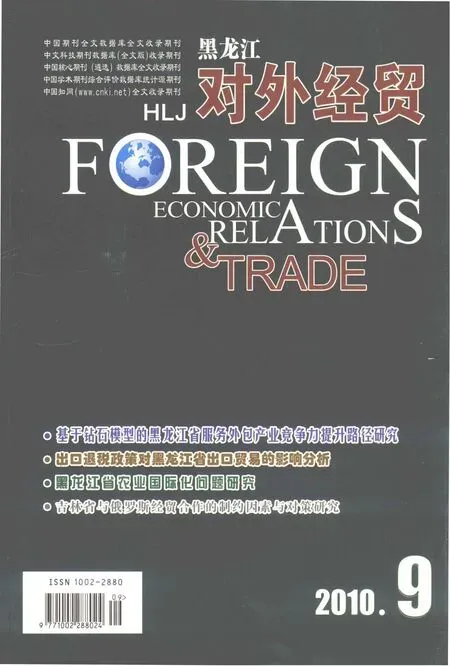基于要素稟賦視角的浙江省傳統產業結構升級
朱 翔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浙江杭州 310018)
[產業經濟 ]
基于要素稟賦視角的浙江省傳統產業結構升級
朱 翔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浙江杭州 310018)
隨著浙江省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原有的依靠初級要素所形成的比較優勢已不再適合傳統產業的發展,甚至產生了制約作用。因此,浙江省傳統產業應加強對高級要素的有效利用和培養,促進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依靠技術創新、品牌建設等方式實現功能升級,提升產品附加值和企業競爭力,進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
浙江省;要素稟賦結構;產業結構升級;高級要素;生產要素配置
改革開放 30多年來,浙江省傳統產業的發展一直處于要素驅動階段。憑借初級生產要素(如自然資源、非熟練工人等)所形成的比較優勢,該地區大力發展缺乏資本和技術要素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了以低價競爭為主的傳統制造業集群,成為了中國乃至世界的制造中心。但傳統產業是以加工組裝和初級產品生產為主,產品檔次低、附加值低,缺乏創新能力、自主品牌和銷售網絡,處于價值鏈的底端,產業發展缺乏主導權。而當今世界經濟正朝著以知識經濟和技術創新為主導的方向發展,生產技術和產品供給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加上要素稟賦結構不斷演化,使得原有的由初級要素所形成的比較優勢已不再適合浙江省傳統產業的發展,甚至制約了浙江省的產業結構升級。因此,浙江省應通過優化要素稟賦配置,發展資本、技術含量更高的產業,通過技術創新和品牌建設等方式實現功能升級,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獲取產業發展的主導權,實現產業結構升級。
一、要素稟賦結構與產業結構關系的機理分析
產業結構問題實質上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實際上就是要素資源在產業間的優化配置,其層次高低,受制于要素稟賦結構。過去浙江省最具競爭力的只能是勞動力要素密集的制造業,這是在特定的要素稟賦結構下所難以逾越的階段。而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的開展、國際要素的流入以及本地經濟水平的提升,浙江省的要素稟賦結構正在發生著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的變化。要素稟賦結構對產業結構的內在作用機制可概括為兩方面:
(一)推動機制,即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將影響不同產業的相對成本變動,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根據要素價格決定理論,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不斷變化,不同要素稟賦的稀缺度產生了較大的差異,從而使得要素的相對價格或相對成本發生較大的變化。隨著經濟的發展,自然資源、廉價勞動力等要素趨于稀缺,使用成本日益增加,而資本等要素的存量及積累能力逐漸提高,使用成本逐漸下降,從而導致資本等要素投入量的逐漸增加,而勞動力等要素較少,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向資本含量高的方向發展。另外,隨著技術、資本 (物質和人力)等要素的不斷積累,地區的創新能力不斷提高,將改變土地、勞動和資本在生產中的相對比例關系,以及它們之間的相對邊際生產率和相對成本,即能夠改變產品的生產函數來創造出更高的生產能力,獲得更多的利潤。從而導致生產要素向高利潤的行業流動,將推動落后產業的淘汰、傳統產業的改造以及新興產業的興起,最終促使產業結構發生變化。
(二)拉動機制,即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將影響需求結構,從而拉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隨著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企業資本、技術等要素的積累、本國比較優勢的變遷,將引致社會需求發生較大的變化。而需求結構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產業結構,因為生產的根本目的和出發點是消費需求,需求是生產的動力,需求結構變動是產業結構升級的終極拉動力量。而社會需求包括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1.消費需求,資本等要素的積累將促進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不僅帶動技術密集型產業保持長期快速增長,更會促進研發、售后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的培育和發展,從而將有力地拉動產業結構升級和高級化進程;2.投資需求,具有最直接的拉動作用,將拉動原材料等配套產業、機械工業等裝備制造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3.出口需求,出口需求對于彌補國內需求不足、國際要素的流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隨著各國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將引致各國比較優勢的變化,進而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動。
二、浙江省要素稟賦結構變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模型分析
本文嘗試通過擴展 Ricardo Hausmann和 Bailey Klinger等人的 HK模型,描述產業結構升級幅度與要素稟賦配置間的關系,來分析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浙江省是否已經優化配置生產要素,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最佳幅度。
假定從現產業階段升級到另一產業階段,其收益為,P(δij)

其中δij表示從產業結構升級階段i到j的升級幅度。如果i=j,δij就為 0,否則就大于 0。而產業結構升級的成本則假定為C(δij),

產業階段i升級到階段j的成本將隨幅度的增加而增加,但隨著要素稟賦配置的不斷優化而下降,用E表示要素稟賦配置的優化程度。
從而,產業升級帶來的最大利潤為:

可見,產業結構升級的幅度是有限的,除了受到要素稟賦配置情況的影響,還受到其歷史條件的制約,以及外部經濟環境、產業政策等因素的影響。但產業結構實質上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其升級實際上就是要素稟賦在產業間的優化配置。因此,針對要素稟賦結構變化而順勢選擇正確的升級方向和幅度才是至關重要的。根據這一理論,政府應充分考慮外部條件的限制,對要素進行合理配置,選擇從現有產業結構向與其處于最佳距離的產業結構的躍升作為升級戰略。
目前,浙江省產業結構中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仍然較高,產業附加值低,競爭優勢不強,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緩慢,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始終偏低。浙江省經濟從 2001年到 2008年增速從全國第 6位跌落到第 22位,工業增速更是自 2004年 6月以來出現了持續 55個月的下滑。到 2009年,浙江省的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僅為6.2%,低于全國的 11%,更遠低于安徽的 22.6%、江西的20.1%、遼寧的 16.8%、吉林的16.8%、黑龍江的 12.1%。這表明浙江省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產業結構升級未達到最佳幅度(如圖 1)。圖中Cij、Pij、∏ij、δij分別代表產業升級的成本、收益、利潤和產業升級的幅度。圖中Ep/c表示浙江省目前的升級幅度,而E*p/c則表示要素稟賦最優配置情況所能達到的升級幅度。可見,浙江省的產業升級幅度未達到要素稟賦最優配置狀態下的升級幅度,出現了“斷檔”現象,產業結構還需要一定程度的調整升級。

圖 1 浙江省產業結構升級中出現的“斷檔”現象
產生比較優勢的斷檔期主要原因是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浙江省原有的比較優勢產業在其他地區的沖擊下,失去了比較優勢,而新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尚未形成、新的比較優勢難以形成的深層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1.人力資本、技術等高級要素積累緩慢。首先,浙江省在人力資本、技術等高級要素的積累方面具有“先天性”的不足,在科研創新、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基礎與其他發達省份差距較大;其次,由于研發能力的薄弱使得高新技術過度依賴跨國公司,而且由于產品生命周期和技術代際差異,難以獲得核心技術;最后,浙江省著名高校和研究院所較少,培養的研發人員和管理人才等人力資本的數量有限,并且政府、企業在職工技能培訓方面的投入不足,培養的熟練勞動力不多。2.要素積累對產業升級的滯后性。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的重要原因還在于難以將科技成果產業化,難以將人力資本有效地轉化為產業升級的推動力。一方面,浙江省的創新體系尚不完善,尚未有效形成能夠整合政府、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市場資源等的“官產學研用”合作體系,難以有效地將人力資本、技術成果轉化為產業升級動力;另一方面,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的激勵和保障機制尚不健全,使得創新主體缺乏將科研成果產業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3.要素之間的匹配程度不高。浙江省目前的勞動力要素稟賦 (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比例)水平不高,很大部分勞動力的技能水平難以滿足高技術含量的產品生產的要求,另外浙江省的中小企業眾多,這些企業要么資本短缺,要么人才、技術短缺,這些要素難以有效地整合發揮作用,難以達到較高的匹配程度,從而制約了技術等高級要素作用的發揮。
三、優化要素稟賦結構,推進浙江省傳統產業升級的對策
從發達國家和地區發展的歷史經驗看,大多經歷了低成本優勢—價格競爭力、制造優勢—產品競爭力和經營優勢—品牌競爭力三個發展階段。浙江省的傳統產業要實現從價格競爭力發展階段向產品競爭力和品牌競爭力發展階段的轉變,必須實現產業發展支撐要素由初級要素向高級要素的轉變,積極培育和大力引進高級要素,實現要素稟賦結構的優化,以強大的技術創新、產品研發能力為依托,以品牌建設為輔助途徑,通過技術創新、品牌建設等方式實現附加值和競爭力的全面提升,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為此,浙江省除了著重培育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和體系建設,利用貿易和投資方式多渠道地引進、消化和吸收世界高技術和先進技術外,還應著重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完善要素市場,優化要素配置效率
產業結構升級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流動方向及使用效率,而這些因素又取決于生產要素的市場配置過程,它客觀上要求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和具有高效調節功能的要素市場,來幫助市場化的企業有效地組合生產要素。要素市場一方面可以節約企業的交易成本,加深企業與其他服務部門之間的聯系,提高企業的資源配置能力和效率;另一方面,則有助于加快知識、技術等高級要素的產權市場化,從而鼓勵技術創新。因此,浙江省應沿著現代市場經濟的路徑,徹底改變政府主導要素市場的局面,從最基本的制度層面做起,為市場主體的成長創建安全、穩定的生存環境,進而通過市場組織的創新,來優化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使其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突破口。
(二)實行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全球要素規劃
在知識經濟時代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浙江省應提出“全球要素規劃戰略”,在開放型經濟體系下,通過借助發達國家的高級要素,努力培育自身高級要素,以滿足產業結構升級所要求的各種要素需求。首先,培育本土跨國企業,幫助其“走出去”,在世界范圍利用全球各種生產要素,提升企業的知識型競爭能力,并通過組合國際生產要素,規劃本土的生產與經營,從而促進浙江省實現從傳統的依靠本土比較優勢競爭轉變為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優勢組合的競爭;其次,注重對外投資,善于利用國外公平競爭的機會向外擴展,從總體上改變浙江省“國內生產,向外出口”的開發方式,轉為發達國家普遍采用的“全球生產,全球經營”的模式;最后,借助外部要素,在其示范、競爭、聚集、鏈接等外溢效應下,創造自身缺乏的知識經濟要素,以形成“動態要素富裕”,改變要素的弱勢地位,從而獲得真正絕對的競爭優勢。
(三)大力發展生產者服務業
生產者服務業通過將高級生產要素“嵌入”到傳統產業,能夠較強地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首先,生產者服務業所體現的各種具有核心競爭能力的隱性知識,通過軟件嵌入硬件,提高了裝備制造業產品的性能,以及用其所制造的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其次,生產者服務業所圍繞的各種產品研究與開發服務,如研發中的設計服務、創意服務、模具服務,生產中的工程技術服務,營銷中的物流服務、網絡品牌服務等,都具有增強產品差別程度和區分競爭對手的作用,從而強化企業的定價能力和控制市場能力;最后,制造企業在生產經營和資本經營中所需的各類生產者服務,如金融服務、企業管理咨詢服務、法律和知識產權服務等,對于提高企業的戰略清晰度、增加市場份額、收購兼并成長等,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浙江省應加強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提高企業的生產運營效率、經營規模和其他投入要素的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產品差異化程度和競爭力,從而有效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1]Gary Gereffi.The Global Apparel Value Chain:What Prospects for Upgrading by Developing Countries?[R].Working Paper forUN IDO,2003.
[2]Ricardo Haus mann and Bailey Klinger.The Structure of the Product Sp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R].C ID Working PaperNo.146,2007.
[3]邁克爾·波特.國際競爭優勢[M].中信出版社,2007.
[4]錢納里.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M].上海三聯書店,1995.
[5]高傳勝,劉志彪.生產者服務與長三角制造業集聚和發展[J].上海經濟研究,2005(8).
[6]張其仔.比較優勢的演化與中國產業升級路徑的選擇[J].中國工業經濟,2008(9).
[7]余劍,谷克鑒.開放條件下的要素供給優勢轉化與產業貿易結構變革[J].國際貿易問題,2005(11).
W ith the change of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in Zhejiang province,the origi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pending on elementary factors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raditional industries.Therefore,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of Zhejiang should strengthen effective utilization and training of senior elements,promote optimum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achieve functional upgrading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rand building,enhance product added value and enterprises‘competitiveness,and then fulfill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Zhejiang province;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senior elements;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F127
A
1002-2880(2010)09-0029-03
(責任編輯:陳鴻鵬)
——張脆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