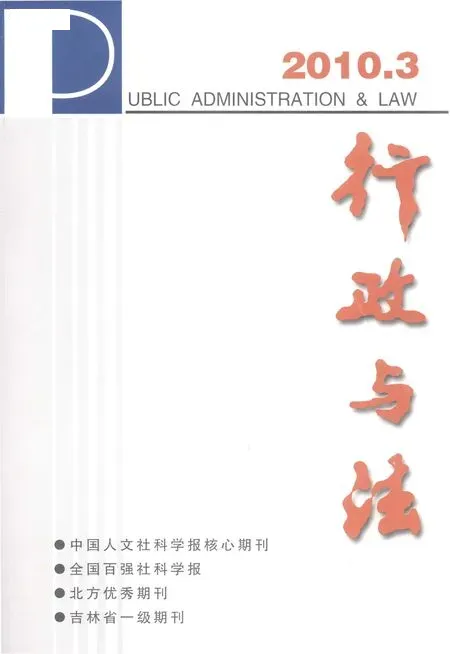反思與重構:我國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之檢視
□胡偉
(復旦大學,上海 200438)
反思與重構:我國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之檢視
□胡偉
(復旦大學,上海 200438)
自我國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設立以來,在實踐中,出資人缺位、錯位、越位的現象層出不窮,當前,有必要對出資人制度進行全面的反思。筆者認為:我國國有資產的真正出資人 (終極所有者)應是全體國民;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應是出資人的代表人而非出資人;出資人的職責僅指按照有關的法律法規行使股東權利;國有資產的三層次運營模式并不能解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兼具的 “老板加婆婆”的雙重角色;未來我國可以遵循兩條路徑對國有資產出資人進行制度的重構。
終極所有者;出資人制度;制度重構
從黨的十六大提出國有資產出資人,到《企業國有資產法》正式確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為出資人以來,在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中,關于出資人制度的主體、功能、職責及運營模式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出資人制度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能否在實踐中發揮《企業國有資產法》所意欲打造的“干凈、純粹”的出資人職責,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尚有繼續研究之必要。本文從應然與實證的視角對我國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進行反思,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關于國有資產監管體系的制度性重構。本文所討論的范圍僅限于經營性國有資產,對于其它類型不作涉及。
一、國有資產終極所有者之界定
終極所有者是指對國有資產具有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能的原始所有人。終極所有者的界定直接關系到出資人及其代表主體的確定,是探討出資人制度的前提和基礎。對我國國有資產終極所有者如何界定,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和立場進行了相應的解釋,主要形成了以下幾種觀點:
⒈國家所有論。該觀點認為,國家是國家所有權的唯一的 、統一的所有者,國家所有權屬于國家,任何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團體或者個人均不能成為國家所有權的主體。在我國,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是國家政權的承擔者,而且是國有財產的所有者。[1](p249)
⒉全民所有論。該觀點認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決定了國家所有權的全民性。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外在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體,更不是凌駕于絕大多數共同體成員之上的異己力量,而是全體社會成員的聯合產物。就全體社會成員自身的聯合體國家所有權而言,國家所有就是全民所有。[2](p21)
⒊政府所有論。該觀點又可分為中央政府所有及中央與地方的二元所有。中央政府所有論認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財產所有權的主體實際上是中央政府。這樣做的目的是給中央政府制定和貫徹經濟發展計劃尋找財產法上的根據,以便中央政府將行政權力和財產權利結合起來制定和貫徹其計劃。[3](p12)二元所有論認為,在我國應當規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級所有權,特別需要在物權法中改變原來的國家所有權規定,重新建立“公共法人所有權”或者“政府法人所有權”制度,明確中央政府所有權與地方政府所有權的區別。[4]
⒋對上述觀點的評析。就國家所有論而言,該觀點看到了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屬性,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但是,從應然的角度分析,國家所有論存在以下理論上的障礙。首先,國家是一個歷史范疇,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隨著私有制的出現而產生的,在國家產生之前,社會上的財產歸屬于哪一主體,雖然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特定主體絕不是國家,因為此時國家尚未誕生。其次,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論述,國家本質上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國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指的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的確定部分,在法律上組織起來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聯合,國家一詞是指持久地占有一處領土和人民,并且由共同的法律和習慣束縛在一起成為一個政治上的實體,通過組織起來的政府為媒介,行使統治領土范圍內所有的任何事物,與地球上的其他社會團體宣戰、締結和加入國際組織的主權。[5](p247-248)國家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在法律層面上,任何民事主體都必須具有一定的權利能力(獨立人格),任何權利的享有者都是一個具體的主體,而由一抽象主體 (國家)來享有民法上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實有悖法理。最后,從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分析,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產生、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市民社會強調個體的“私”的領域,并排斥政治國家的干預;政治國家主要存在于“公”的領域,為市民社會“私”的領域之有效運行提供制度保障。作為社會財富之國家財產,是市民社會健康有序發展的物質基礎,也是市民社會用以對抗政治國家干預的有力武器。因此,國家財產之終極所有者自應是市民社會中的市民而非國家。
就全民所有論而言,從表面上看較為符合我國的實際,我國憲法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民法通則》第73條第1款規定:“國家財產屬于全民所有”。《物權法》第45條規定:“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財產,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企業國有資產法》第3條規定:“國有資產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另外,因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利屬于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維護人民的利益是制定一切國家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故人民理應是我國國有資產的終極所有者。筆者也基本贊同全民所有論,但是,從法律實證主義的角度分析,全民所有論尚存在一些理論上的瑕疵。其一,就人民(全民)所有而論,人民是與敵人相對應的概念,是公法上的稱謂,而作為私法意義上的所有權主體若冠以公法上的概念,則有悖法律的邏輯思維。其二,全民所是指直接的社會所有,所有者雖為全體人民,但在法律上并不是一個所有者。正如捷克民法學家凱納普指出:“全民所有權是一個經濟意義上的所有概念,是在社會意義上所使用的概念,全體人民在法律上并不是一個所有者”。[6](p454)全民是一個高度抽象性的主體,全民所有在法律上只能歸入“共有”,而共有又分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因一國的國民人數每時每刻都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使得其數目具有不確定性,進而造成難以按份享有共有財產;又因“共同共有”雖然在共有期間不能分割共有財產,但在共有終結時,共同共有人可以請求分割共有財產,而這同樣會因人數之不確定難以適用共同共有。[7](p48)其三,從法律規范意義上分析,每一個法律規范都是權利義務的統一,每一項義務必須對應相應的權利,權利可以放棄,義務則必須履行。法律意義上的權利可分為第一性的權利(原權利)和第二性的權利(訴權或請求權),第一性權利以第二性權利為保障。如果沒有訴權(請求權),作為第一性權利之原權利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權利。同理,以全民所有而論,一方面,法律賦予每一個個體(國民)都享有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另一方面,又規定任何人不能行使請求行使分割國有資產的權利。這就使得作為所有者之主體不能行使所有權的占有、使用、處分的權能,故這里所規定的全民所有權不是完整的所有權,甚至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權利。
就政府所有論的主張而言,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證上分析,都值得商榷。政府是一行政機關,行使國家的行政管理權力。在代議制國家,公民選舉自己的代表組成議會或國會,議會或國會經過選舉組成政府,政府對議會或國會負責,并接受其監督。政府的權力來源于人們的賦權,政府應在授權的范圍內行使社會公共管理的職權,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尊嚴等不受侵犯。因此,能夠作為國家財產的終極所有者這一角色的,自然應是全體人民而非政府,政府充當的僅是終極所有者的代表人。這一定位在我國法律中也有明確的規定,《企業國有資產法》第3條規定:“國有資產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的所有權”。
二、出資人制度之檢視
⒈出資人代表主體之反思。《企業國有資產法》第1條第1款規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國務院的規定設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根據本級人民政府的授權,代表本級人民政府對國家出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根據前述分析,我國國有資產的終極所有者應為全體人民,相應地,國有資產的出資人也應是全體人民。《企業國有資產法》頒布后,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國資委應是一個干凈的出資人。這其實是把出資人與出資人代表混為一談,實際上,出資人與出資人代表是有區別的,出資人主要是國家法律的規定,出資人代表則是通過授權行為而認定的。因此,無論是國務院或各級人民政府,還是國資監督管理機構都應是出資人代表,而非出資人。把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定位于出資人也與我國 《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和《企業國有資產法》等有關規定相背離。前者在其第12條規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是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負責監督管理企業國有資產的直屬特設機構。。”后者在其第11條也作了相同的規定。
此外,對政府與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之間的法律關系如何定位也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按照通說,普遍認為二者之間是委托代理的關系,筆者則認為,這一規定主要是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的界定,若從法律的視角重新解讀,二者應是代表關系而非委托代理關系。依據法理,代理是指代理人在法定或約定的權限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為一定的法律行為,而法律行為的后果歸屬于被代理人的行為;代表是指代表人以被代表人的名義為被代表人進行一定的行為。兩者的主要區別是在委托代理中,委托人和代理人是兩個相對對獨立的主體,代理人在委托人授權的范圍內以自己的意思表示為一定的法律行為;而代表人則不是一個獨立的主體,它往往是被代表人的一個組成部分或成員。反觀我國政府與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按照《企業國有資產法》第11條規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國務院的規定設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根據本級人民政府的授權,代表本機構人民政府對國家出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據此分析,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作為國務院的直屬特設機構,在性質上也應是政府部門,是政府機構的組成部分,而在委托代理中,代理人不可能是委托人的一部分,故政府與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之間只能是代表關系。
⒉出資人代表職責之反思。按照黨的十六大和《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的規定,我國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的職能是管理企業的國有資產、管理出資人委派經營企業國有資產的人,管理國有企業的保值增值,即管資產、管人、管事相結合。此外,出資人代表還可以制定國有資產監管的規章、制度。值得肯定的是,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的建立,改變了過去“九龍治水”的混亂局面,朝進一步完善國有資產經營管理體制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上述出資人代表職責的定位,使其一方面作為股東享有出資人職責的“老板”的權力,另一方面又具有制定國資規章制度、安排下崗職工等“婆婆”的權力,成為兼具老板加婆婆、裁判員加運動員的雙重角色。在實踐中,既履行出資人等“私”的職責,又行使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等“公”的職責,成為一個公私兼具的市場主體,出資人代表職責的這一定位一直受到廣泛的質疑。2009年頒行的 《企業國有資產法》在第12條第1、2款規定:“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代表本級人民政府對國家出資企業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出資人權利。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制定或參與制定國家出資企業的章程。”第14條規定:“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以及企業章程履行出資人職責,保障出資人權益,防止國有資產損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應當維護企業作為市場主體依法享有的權利,除依法履行出資人職責外,不得干預企業經營活動。”應該說,《企業國有資產法》對出資人代表職責的進一步明確的定位,為把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打造成“干凈、純粹”出資人指明了方向。它不僅細化了出資人代表的職責,還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同時淡化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的社會公共管理職責。但是,筆者并不就此認同那種認為《企業國有資產法》已經明確界定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作為“干凈、純粹”出資人地位的觀點。[8]我們認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所具有的老板加婆婆的雙重角色,有其深層次的體制、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單單依靠一部《企業國有資產法》就想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改革中所有者缺位、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等頑疾,既不現實,也不可能。實際上《企業國有資產法》本身就是一個各種利益集團相互博弈、妥協的結果,這可以從國有資產立法所經歷十幾年的漫長歷程中得到印證。國企及國資改革中出資人缺位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從黨的十六大提出“出資人”這一稱謂開始,對出資人職責的定位一直在進行不斷的探索,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形成一個清晰、科學的認識。在經過多年摸索之后,現在似乎又回到了邏輯的起點,這固然與我國國體所帶來的本質性的約束,即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不可動搖的社會制度直接決定著我們的選擇空間有關,也與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政府機關和官員家長制的慣性思維方式有密切的聯系。從某種程度上講,后者可能是當下中國亟待解決的問題。其實,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的設置也僅僅意味著出資人機構的到位,并不表明出資人職責的到位,出資人職責的到位遠比出資人機構的到位艱難得多,復雜得多。[9]這也是為什么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設立這么多年來,充當出資人代表的國資委發生錯位、越位的現象層出不窮的原因。
⒊出資人制度下國有資產運營模式之反思。自2003年國資委成立以來,關于國有資產的運營應采取何種模式,理論界有不同的觀點,主要有兩層次運營模式說和三層次運營模式說。兩層次運營模式要求,應由國有資產監管機構作為出資人直接持有國有出資企業中的國有資產,履行出資人的職責;三層次運營模式要求,由國有資產監管機構通過委托代理方式將國有產權委托給國有控股投資公司作為國有資產的出資人,再由國有投資控股公司按照市場化的投資原則,將國有資產投資于下屬企業,形成國資委—國有控股投資公司—國有出資企業三層委托代理運營模式。目前,我國中央實行的是兩層次運營模式,在地方有些實行的是三層次運營模式,有些是兩層次運營模式。在我國理論界,學者們普遍贊同實行三層次運營模式,并認為三層次運營模式是未來我國國資運營的改革方向。正如上文論述,在當前廣泛采用的兩層運營模式下,因作為出資人之國資監管機構本身就是政府部門,難以有效協調市場背景下出資人所享有的“私”權利與政府背景下公共管理者所享有的“公”權力之沖突,必然會造成國有資產監管機構 “錯位”、“越位”、“缺位”現象的發生。相反,在三層次運營模式下,國有資產監管機構通過委托代理將出資人職責委托授權給投資公司,再由投資公司按照市場的要求運營國有資產,可以很好地解決兩層次運營模式下出資人職責模糊不清、所有者缺位等問題,并最終實現政企分離、政資分離。筆者認為,三層次運營模式雖然明確了國有資產運營的產權主體和責任主體,增加了更多的市場運營的環節和因素,但因在三層次運營模式自身所具有的諸多缺陷及大量配套改革措施不到位的情況下,仍然難以解決國資運營中所有者缺位的頑疾。首先,三層次運營模式增加了一層運營主體,大大拉長了委托代理的鏈條,造成過高的委托代理成本,加劇了信息的不對稱性,使得委托人對代理人監管約束的難度加大。在實踐中,基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過度分離,極易出現道德風險和代理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其次,在三層次運營模式下,企業仍難以擺脫政府的行政干預。由于國有資產監管機構作為事實上的政府機構,即使處于第二層的國有控股投資公司按照《公司法》、《證券法》的相關規定,代表國家行使作為出資人的股東權利,但是,因現階段我國尚無成熟的經理人市場和完善的高級管理人員的經營激勵機制,并且國資委牢牢地掌控著國有控股投資公司與國有出資企業的人事任免權,使得處于第二層的運營主體與處于第三層的經營主體缺乏真正的自主權,其董事會往往成為名存實亡的擺設,難以有效行使董事會所應具有的權利。最后,在三層次運營模式下,國有出資企業仍然難以享有充分的法人財產權。依據法理,作為市場主體之法人,必須具有獨立的法人人格(民事權利能力),而獨立的法人人格直接取決于該法人是否享有真實的財產權。后者是前者的獨立的前提和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講,對法人而言,無財產既無人格,無財產也就不能成為市場中商事交易的主體。出資人把自己的財產投入到所投資公司之后,即喪失了對所投資財產的所有權,作為回報,出資人獲取了所投資公司的股權。與此相對應,公司則取得了所有出資人投入財產的所有權,在此基礎上形成公司的法人財產權,公司對此財產享有占有、使用、處分及收益等權能。出資人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能取回自己所投入的財產,通常他們只能行使對所投入公司的股東權利。對國有出資企業而言,既然國有資產投入到國有出資企業之中,就不再享有該國有資產之所有權,該國有資產成為國有出資企業財產權的組成部分,出資人行使的只能是按照《公司法》、《證券法》所享有的股東權利。目前,在三層次運營模式下,國資委基于自己絕對控股地位和對人事的控制權,往往行使了超出股東權范圍之外的權力,造成事實上職權行使的越位和錯位,往往以行政手段強迫國有出資企業承擔其不該承擔或不愿承擔的社會責任,變相剝奪了國有出資企業作為獨立自主、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地位。
三、總結與制度重構
基于我國國體及歷史形成的原因,我國是世界上國有資產最多的國家,目前,我國正處于一個“新興加轉型”的歷史階段,能否在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確保其保值增值,將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穩定和改革開放的大局。因而,這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又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需要我們開動腦筋、解放思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對現有制度進行不斷的反思與重構,進而探索出一套成熟完善、行之有效的國有資產監管運營模式。
根據上述對我國出資人制度的論述與評析,筆者認為,可遵循兩條路徑對現行出資人制度進行制度重構。第一條路徑是依據我國《企業國有資產法》所規定的模式,在現有兩層次運營方式下,對國資委職責進行重新定位,逐步剝離國資委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使之成為一個“干凈、純粹”的出資人。國資委不再是一個政府直屬特設機構,而是一個特殊的“非營利企業法人”。國資委在此基礎上可以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由其主導運營非特大型國有出資企業,負責這些企業的兼并重組,并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真正實現國有資產在非壟斷性領域的退出。此外,國家還要加大對高級管理人員經營激勵制度的改革,發展職業性的經理人市場和資本市場等配套措施。只有在市場背景下實現經理人員的進退自如和資本市場的充分發育,才能真正解決現階段國有資產監管體制下所有者缺位所導致的出了問題無人負責的問題。
第二條路徑是變國有為民有,實現民有民享。對除少數屬于公共物品或自然壟斷產業以外的絕大部分國有出資企業,通過拍賣或股份化等形式變為民有,[10]真正實現國有資產從競爭性領域的完全退出和讓利于民。從根本上解決出資人不到位的問題。在這種方式下,國資委將控制極其少數國有出資企業,由其直接履行出資人職責。當然,這條路徑雖然能夠從源頭上解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中的出資人缺位問題,但會面臨諸多體制與傳統思維方式等因素的制約。這需要在市場化的改革中,以博大的胸襟、世界的視角穩步推進,切記一蹴而就。實際上,如果我們不去糾纏空洞的理論說教,而是實證地論證與分析,著眼于實現社會主義的實質平等、真正的共同富裕,那么第二條路徑未嘗不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模式。
作為世界上擁有最多國有資產的國家,在以市場化、自由化及全球化為導向的競爭格局中,面臨著重大的機遇與挑戰。國有資產如何在我國轉型的歷史過程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造福于國民;如何建立一套真正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出資人制度,防止國有資產的不斷流失,實現其保值增值的目標,是當前我國亟待解決的新課題。30年的改革實踐表明,只有不斷地革故鼎新,敢于突破舊有的思維模式,在反思中吸取經驗,在批判與重構中獲得動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有資產出資人的缺位、錯位、越位等問題。只有通過不斷地放權、還權、賦權與國有出資企業,才能使之成為真正擁有完整法人財產權,能夠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進而實現國有資產從競爭性領域的完全退出。
[1]佟柔.民法學[M].法律出版社,1990.
[2]王利明.國家所有權研究[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3][5]孫憲忠.論物權法[M].法律出版社,2001.
[4]燕春,史安娜.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批判與重構[J].社會科學研究,2008,(2).
[6]王利明.物權法論[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7]徐曉松.國有企業治理的法律問題[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
[8]李曙光.論企業國有資產法中的五人定位[J].政治與法律,2009,(2).
[9]周放生.出資人職責到位需要創新思維[J].上海國資,2004,(12).
[10]張鳳林.尋求治理國資流失的根本途徑[J].經濟學家,1999,(6).
(責任編輯:張雅光)
Rethinking and Reconstruction:The Capital Providers Systems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In China
Hu Wei
Since the capital providers system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has been established,At present,the problems of the omission and dislocation of the capital providers are very serious,So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think the shareholders of state-owned assets.In my opinion,The ultimate shareholders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in china are the entire Chinese population.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shareholders.The only obligation of the capital providers is to perform the shareholders'rights.In future,there are two ways for china to reconstruct the capital providers systems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ltimate shareholders;the system of represent performing as investor;reconstruction of system
D922.291
A
1007-8207(2010)03-0072-04
2009-09-01
胡偉 (1981—),男,河南人,復旦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民商法。
本文受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資助,項目編號:B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