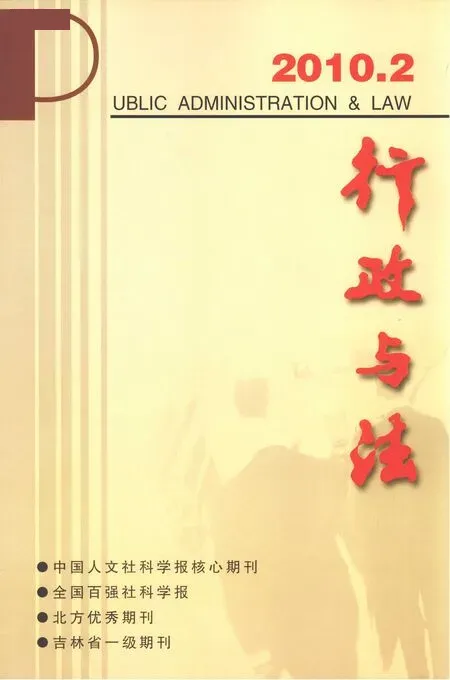整體性治理制度化策略研究
□黃滔
(武漢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2)
整體性治理制度化策略研究
□黃滔
(武漢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2)
整體性治理理論有望成為繼傳統官僚制、新公共管理后的第三代公共行政理論典型范式。本文結合我國實際及OECD國家整體性治理的實踐,從五個維度對構建整體性制度化實施體系進行了探索,認為內部構建大部制,外部倡導理性的公私合作,縱向構建部省合作新型關系,橫向上建設電子化無縫隙政府,動態上從價值與倫理文化角度構建主動性公務員體系是整體性治理制度化的重要途徑。
整體性治理;整體政府;大部制;制度化
一、整體性治理的緣起與地位
整體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的公共行政治理理論研究者最具創新性與前瞻性的理論之一,最早由英國學者佩里·希克斯(Perri 6)于1997年出版的《整體政府》一書提出。該理論深受英國工黨政府認同,并很快被決策層所采納并付諸改革實踐。1997年工黨政府發表極具里程碑意義的政府改革綱領《現代化政府政策白皮書》(The White Paper Modernising Government),即以希克斯的整體性治理理念為指引,提出了聯合性政府 (joined-up government)理念,開啟了全球整體性治理改革的先河。隨后,希克斯和Diana Leat于1999年出版了 《圓桌中的治理——構建整體政府的策略》,并于2002年再次合作出版了《邁向整體性治理》一書。希克斯將整體性治理界定為相關治理機構之間,共同強化服務的意義與目標,并在相互認同的方式中達成彼此同意的結果。[1]這一理論基于對新公共管理運動所導致的政府部門碎片化(functionally fragmented governance)以及政府責任模糊化的反思與回應,以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為政府運作的核心,針對全球化、信息化浪潮對政府的不斷滲入與影響,特別是對諸如傳統體制下對恐怖主義、SARS和H1N1型甲流等大型公共衛生事件、環境保護、低碳經濟、金融危機、就業、教育、搶險救災等跨部門、跨專業、跨功能、跨區域甚至跨國界的重大復雜而棘手的民生問題(wicked problems)反應遲鈍,各自為陣,整體效率低下,公平正義價值喪失的狀況,整體性治理開出了相應的解決藥方。該理論從新涂爾干理論 (the new Durkheimians theory)和組織社會學理論中吸取養分,以公平正義、觀照全體、及時回應服務等為倫理與價值基礎,以預防導向、服務導向、整體導向、合作導向、結果導向為邏輯起點,充分利用信息化技術、網絡化技術、組織一體化技術,以協調和整合(integration)為基本手段,追求在“政策、規章、服務、監督四個方面”進行“治理層級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和公私部門的整合”,[2]以期達到“排除相互破壞與腐蝕的政策情境;更好地使用稀缺資源;促使某一政策領域中不同利益主體團結協作;為公民提供無縫隙而非分離的服務”四個目標,[3]形成一種服務與治理的目標和手段互相增強的新政府治理模式與境界,[4]化解新公共管理模式下的政府管理碎片化和服務裂解性問題。目前,繼英國之后,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芬蘭、荷蘭、英國、美國、新加坡等OECD國家相繼進行了整體性治理的大規模改革實踐與探索。整體性治理在各國、各地區有多種譯法或稱謂,如加拿大稱整體政府(WOG——whole-ofgovernment),英國開始稱聯合政府,我國臺灣地區則譯為全觀型政府或協力型政府。雖然稱謂各不相同,但一個不容爭議的事實是 “整體政府已成為當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新趨向”,[5]“全觀型治理”的理論可望成為21世紀有關政府治理的大型理論(grand theory),值得行政學者廣泛加以研究,“整體政府的理論和機制對我國政府管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6]許多學者認為,整體性治理理論有望替代已被不少學者質疑的新公共服務理論而成為繼傳統官僚制、新公共管理運動后的第三代公共管理理論典型范式。由此可見,整體治理理論已成為國內外行政管理研究領域的熱門與前沿領域,值得我國政府理論的實踐者及時跟進、消化、吸收并結合我國行政改革的實際加以有效運用,不斷進行政府組織與服務模式的改革與創新。
二、整體性治理制度化的必要性
理論的真偽和價值的大小需在實踐中得以檢驗,而科學的理論能否真正指導實踐,取決于是否將該理論制度化。許多理論往往在提出時受到熱捧,最終則因缺乏可操作性和未提出合理的制度化策略而止步于理論界的探討和期望被人遺忘。我國臺灣大學的林水波認為,體制就是 “一種政治制度安排 (a political arragement),它使得公共政府制度中的重要價值能夠被制度化下來,同時,制度亦是一組組織的結構化安排,借此界定和支持此一體制的政治價值”。這一安排的過程,即被稱之為“制度化”。該理論的創始人希克斯十分注重其理論的實踐與運用,他在2002年出版的《邁向整體性治理》最后一章中著重提出了“制度化”問題,以作為構建整體性治理得以實現的策略。但他在這一章中能夠舉出整體性治理成功的例子并不多,他對于各種整體性的討論雖然詳細,但在眾多利弊得失與治理類型的討論中,事實上很難看出,究竟要用何種策略構建,才能使碎片化政府朝整體性治理邁進。[7]“因此整體性治理還是一種成長中的理論,因為整體性治理所需要的制度化正如希克斯自己所說的還沒有完成”。[8]
就整體性治理制度化策略而言,我國內地學者還基本停留在理論引介方面,實踐層面探索不多,相對而言,我國臺灣地區學者研究得相對深入。2005年,臺灣大學政治系彭錦鵬發表的《全觀型治理:理論與制度化策略》、林水波和李長晏出版的《跨域治理》以及臺灣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韓保中2009年發表的 《全觀型治理之研究》一文中都有相關討論。特別是彭錦鵬明確而詳細地提出了要達到整體性治理,必須采取 “線上治理——科技基礎、整合型組織——組織基礎、主動型文官體系——人員基礎”三項制度化途徑對現有政府進行改革。希克斯構想的整體性治理,也就是透過“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途徑來達成全面整和的境界。[9]正所謂理論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策略就成為很難將理論付諸實踐并體現理論的指導意義和價值。整體性治理作為一種全新的治理范式更是需要科學的制度化策略以保證整體性治理理論真正貫穿于政府治理的全過程,建構出整體性的服務型政府模式。因此,加強對整體性治理理論制度化策略的探索顯得十分必要。
三、整體性治理制度化策略探析
應該說,我國臺灣地區學者彭錦鵬提出的制度化策略很具啟發性,為內地學者繼續研究拓寬了視野。但由于臺灣地區的政治、社會及文化背景與大陸有一定的差異,因此,本文主要以地方政府為參照系,從內部、外部、縱向、橫向四個靜態維度及文化價值一個動態維度來探析整體性治理在我地方政府制度化的策略途徑。
第一維度——內部:構建大部門體制
希克斯認為,整體性治理是針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政府改革所強化的碎片化狀況提出的。“整體主義的對立面是破碎化,而不是專業化”,[10]諸如部門間轉嫁問題與責任、項目相互沖突、目標互相沖突、缺乏溝通、服務遺漏等等。產生碎片化的根源有兩類,一類是體制性碎片化,一類是功能性碎片化,兩者均源于公共選擇理論中的組織自利性假設。就我國而言,政府機構部門數量龐大、部門林立、職能交叉、權責不明、職責同構、協調不暢、互相沖突等碎片化現象也十分突出。而整體治理理論認為,整體政府應十分強調整體協調與配合機制的建立,要從體制上予以適當調適與解決。因此,整體性治理的制度化首先應該構建大部門體制。應該說,英美兩國政府是“大部制”實施的典范。我國是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構建 “大部制”的。把一些職能相近或整合性強的職能和機構進行整合,實行綜合管理,使政府部門逐步向“寬職能,少機構”方向發展;同時要求政府從具體的管理事務中逐步抽身,專注于宏觀調控和政策制定職能,使政府向“小政府,大服務”方向發展,力圖通過建立一個決策、執行、監督三者相互協調又相互制約的行政運行機制,有利于政府部門關系、政府職能結構、行政運行機制與政府權責匹配的優化。[11]但許多學者也擔心大部門體制將帶來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集團化,即內部監督問題和職能與機構能否真正同步融合等新問題的出現。因此,在構建大部制的同時,要理性消除對“大部制”的認識誤區。一是大部門不是簡單的機構歸并,其實質是職能整合。二是核心目標是著眼于建立整體性服務型政府而不在于著眼機構的簡單精簡。在具體操作中,首先,應圍繞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四大職能進行科學規劃,搞好頂層設計,穩步推進而不急于“完成任務”,以避免“反復折騰”的錯誤。其次,應因地制宜、因層制宜,在地方一級強調具體性、直接性和執行性,沒必要與中央政府部門嚴格對應。第三,應搞好配套改革與法制建設同步跟進的問題。第四,在大部門內部可強化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的適當分離。如深圳市政府對“行政三分”的探索。
第二維度——外部:加強理性的公私合作
希克斯認為,整體性治理所追求的整合既可以在公共部門內部進行,也可以在政府部門與志愿組織或私人公司之間進行,[12]并且整合的程度越高,凝聚力就越大。他引用費佛、愛默生等人的資源交換和資源依附理論來加以證明,當達到一定強度的資源整合會產生這一狀況:政治樂意交出自主性以換取其它好處。[13]由此可見,公私合作或稱公私伙伴關系(簡稱PPP模式,即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雖然是英國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典型改革模式,但基于對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回顧與反思而提出的整體性治理并不是盲目地排斥公私合作制,相反,它還有機地吸納了公私合作治理。當然,這種吸收是理性的、批判性的、有機的。民營化大師E·S·薩瓦斯把這一模式具體劃分為十類:服務合同、管理合同、租賃合同、特許經營、BOT、BOO、BOOT、反轉BOOT、混合經營、出售,以形成政府部門、企業、非政府組織等主體力量共同提供公共產品的多元化格局。目前,我國在機場建設、城市水務、垃圾處理、公路、學校、醫院等城市基礎設施領域對此也有較多運用,英國、美國在這一方面走得更廣更遠,在監獄、鐵路、國防裝備等敏感領域也在大膽運用。但近幾年,OECD各國都在反思過度民營化、市場化帶來的種種弊端,特別是在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PPP模式的濫用更多地受到人們的責難。其實,從整體性治理看,公私合作本身不是壞東西,相反,它認為公部門業務采取委托、服務外包、民營化、去任務化、行政法人化等做法,運用更多非營利性組織與私人部門接軌,將使公私合作關系產生漸層合作的關系,實現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14]在本文看來,應在整體性治理框架下有益吸收傳統PPP模式的合理內核,實現理性的公私合作,應強調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責任主體不變,完善公共服務與產品監督體系,合理界定合作盈利水平,既強調結果控制又強調過程管理,政府角色由指揮者、控制者向促進者、協調者轉變,使合作過程公開透明,以避免一些公組織和私部門借此產生“尋租”和“公共價值的喪失”,從而影響政府與社會聯動實現整體治理的效果與認同。
第三維度——縱向:構筑部省合作的新型關系
Tom christensent和 Perlegreid通過對 “整體政府”的政治與行政領導的構成性質的研究,總結出“整體政府”治理結構表現為等級式與協商式兩種表現形式,又稱為“聯合岬(Joined-up-ness)”。[15]新西蘭的“整體政府”改革就是一個典型。在那里,“協商”存在于各種相關機構與各層行政組織之間。合作是協商而非等級命令的結果,它可以通過形式松散、結構系統化的協商達成。在區域競爭與合作均十分激烈的今天,為更多更快地獲得中央資源,我國的省、市等地方政府與中央部委各部門間的關系正更多地由等級式向協商式轉變。近年來,各省、市比以前更多地意識到主動加強部省合作構筑新型合作關系的重要性。僅2008年一年,湖北省政府已與交通部、教育部、建設部、育務部、科技部等51個國家部委或央屬企事業單位簽訂了合作協議或備忘錄,高密度的部省合作讓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試驗區建設大大提速,更快、更多地獲得了中央各部門從政策、資金、項目等各方面的特別關注和重點支持。“實踐證明,部省合作的模式積極有效。它已經正在或將會解決城市圈改革發展中依靠自身努力而解決不了的問題”。[16]在其他省份,如福建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湖南與科技部的定期會商合作,幾乎每個省份,都可見“部省合作”的活躍身影。通過這種點對點、相互吸引、形式多樣的部省合作,打破了傳統的“條塊分割”,在中央部委與地方政府之間建立起了新型的伙伴型關系。使雙方的信息交流穩定化、利益訴求一致化、合作形式緊密化、協作平臺具體化。從全國范圍看,這種互動性的競爭與合作使之前比較漠然的層級關系生動化,在傳統的官僚化組織上使縱向的權力線與橫向的行動線交叉與交織,形成柔性而有序的網絡,從而使“協商式”與“等級式”有效疊加,促進了整體性治理的實現。
第四維度——橫向:構建電子化無縫隙政府
從橫向上看就是“大部制”,部門也是有邊界的,部門之間的合作始終是有縫隙的,要消除部門邊界和縫隙則需構建電子化無縫隙政府。“無縫隙的政府”是一種適應顧客社會、信息時代要求的新的政府再造理論。美國哲學博士林登(Russell'Linden)在其所著的《無縫隙政府》中指出,無縫隙政府(Seamless Government)指的是政府整合所有的部門、人員和其它資源,以單一的界面為公眾提供優質高效的信息和服務,這也正是整體性治理所要追求的目標,“整體性運行的目標之一就是設計能對一系列橫向無縫隙結合的問題作出反應的干預或相關的能力”。[17]實現“無縫隙”政府、“電子化政府”(digital government)是與其相輔相承、互為依托的。網絡科技的發展為政府業務毫無限制地連結起來,突破傳統政府層級與部門單位的地理疆界,使政府業務能夠免除以往公文傳遞耗費時日的束縛提供了基礎。實現電子化無縫隙政府,一是要通過服務流程再造實現行政審批無縫隙。以公眾為根本,以服務流程和組織結構進行重組和創新來實現,以公眾滿意為價值導向,對原有流程進行流暢的政府內部銜接和協調。[18]如串聯審批改并聯審批,實行一站式服務、一次性告知服務、延時問責、政務超市等。二是加快政務電子化,實行文件數據化。如青島市2005年開始實施的“統一機構、統一規劃、統一網絡、統一軟件、分級管理”的“四統一分”電子化政務模式,建立起政府各部門共同使用的“政府應用服務提供系統”,運用全市統一的單一政府信箱系統把政府與老百姓生活相關的56個部門以及下屬的12個區和縣的政府統一在一個窗口下,達到政府部門協同辦公的目的。三是要對政府的行政程序立法,建立公開、透明、責任無縫隙的政府。湖南省政府2008年頒布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已開國內先河,值得推廣。四是適時開展點對點上門服務。顧客要求多樣化,整體性政府服務也要適應個性化要求。要在這方面消除服務縫隙,必須適時開展點對點上門服務。如金融危機來臨時,長沙市于2009年及時推出 “兩幫兩促活動”,全市每個黨政部門派出一個三人工作小組,常駐重點企業與相關項目,脫產上門服務一年,實行政務全程代辦,并建立市領導掛點聯系制,后盾單位支撐制、周工作臺賬管理制、季度講評制、要素問題集中交辦制、定向績效考評制,使企業逾越鄉、縣、市、省各部門,只接觸工作組一個“觸點”即可滿足其得到各級政府整體服務的要求。“點式全程代辦”讓其感受了無縫隙的整體性政府服務。
第五維度——動態:建構主動型公務員體系
如果把前四個維度視為靜態維度,那么,公務員的價值與倫理文化則可作為實現整體政府的動態維度。有如愛因斯坦時空系統中的時間維度,是動態的也是最關鍵的。希克斯在有關整體性治理專著中反復討論到整體性責任的重要性,也就是政府組織中每一個人都要為他的公務行為主動負責。[19]但問題是,究竟如何來達成責任的承擔?從公務員的角度加以觀察,顯然必須先有民主政治高度責任感的行政人員,輔以有效合理的文官體系,才能引導建立有為有守的全觀型治理的推動者。[20]Denhardt認為,主動型公務員應該具有以下價值與倫理標準:對組織價值的承諾、服務公眾、授能(empowerment)和分享領導、務實的漸進主義以及奉獻公眾服務。在我國,“為人民服務”一直是政府存在的價值與倫理基礎。要公務員實現其價值標準,需構建科學的體制加以保障。關于如何建立符合整體性治理的主動性文官體系,彭錦鵬在考察了OECD各國公務員體系后提出了三條建議:一是建立多元組織下的公務員“適任性”標準,并用考選和試用的制度加以貫徹。他認為,針對21世紀政府機關的多元化趨勢,應綜合考察組織成員的能力與性格、服務公職意愿和價值觀、未來可能的職業出發潛能等,建立“適任性”標準,并強化客觀的強制性的“試用考評制度”。長沙市政府2009年走進211大學大范圍招聘“政府雇員”,然后從中逐步選拔公務員,就可為“適任性”提供一定保障。二是以成就感為核心,結合年資、績效和待遇平衡成為有效的激勵體系。從激勵理論的平衡(equity theory)角度觀察,發現各種工作條件和資格相似的公務員,影響工作主動性的根源之一是事實上未得到平衡的待遇。主動性公務員體系的核心價值和制度基礎應該建立在公務人員的成就感之上,并配合年資、績效等因素全面規劃,以激發每一個人的潛能而主動作為。三是要建立合理的高級公務員制度,培養主動性公務員體系的領導階層。他考察了法國的國家行政學院行政精英培訓制度(ENA)、美國的高級主管制度(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英國的高級公務員團 (Senior Civil Service)制度,認為精英制輔之以市場性動態管理機制,是OECD各成員國近年來關于主動性高級公務員制度發展的共同趨勢。當然,他的這些觀點都是在西方的政治背景下提出的,不能全部適合我國的社會背景,但合理參考和借鑒西方公務員體系的最新發展經驗,有助于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國國情和面向21世紀任務挑戰的主動作為的公務員體系,進而為構建整體政府助力。
總之,追求整體性治理是當前世界各國面對層出不窮的挑戰而共同追求的新的公共管理理想模式,其制度化策略從理論到實踐均在不斷探索完善中。本文力圖以務實的態度和解析的角度,從內、外、縱、橫四個靜態維度和價值倫理文化維度構建一個動態的體系,以嘗試解析希克斯提出的“整體性治理”制度化策略與途徑,當然更多的只是停留在策略的探討與目標的展望上,具體做法仍需各種政府組織與部門在實踐中以創新和改革的姿態予以不斷探索使之豐富。
[1][7][9][20]彭錦鵬.全觀型治理理論與制度化策略[J].臺灣政治科學論叢,2006,(23).
[2][4][8][13][17][19]竺乾威.從新公共管理到整體性治理[J].中國行政管理,2008,(10).
[3] [15]Christopher Pollit Joined-up Govermment A Survey.Political Studies Review.Jan 2003,vol 1 ssue 1,pp34-49.
[5][14]曾維和.西方“整體政府改革”:理論、實踐與啟示[J].公共管理學報,2008,(04).
[6]周志忍,整體政府與跨部門協同[J].中國行政管理,2008,(09).
[10] [12]Perri6.Dianaleat,Kimberly Seltier and Gerry Stoker.2002.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The New Reforn Agerda.New York:Palagrave.
[11]李和中.中國地方政府規模與結構評價藍皮書(2008年度)[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6]部省合作次第開花[N].湖北日報,2009-07-30.
[18]褚松燕.行政服務機構建設與整體政府的塑造[J].中國行政管理,2006,(07).
(責任編輯:王秀艷)
Study on Strategies of Institutionizing Holistic Governance
Huang Tao
Holistic governance theory is expected to be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typical paradigm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after the traditional bureaucratic theory and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Institutionalization is crucial to the achievement of holistic governance.Based on the practices of holistic governance in OECD countries and the realities of our country,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holistic institutionalization from five large sector institutions,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new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istries and provinces,Seamless Government and Initiative of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holistic governance;holistic government;institutionalization
D630.1
A
1007-8207(2010)02-0001-04
2009-12-23
黃滔 (1974—),男,湖南長沙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長沙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高級經濟師,研究方向為地方政府治理與公共人事行政。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 “基于善治取向的地方政府結構與規模優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7073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