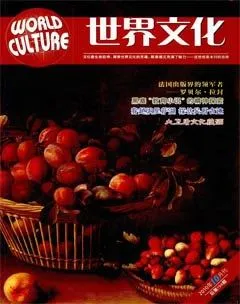黑塞“教育小說”的精神探索
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一位出生于牧師家庭的德國作家,從小受到嚴格的基督教教育;1891年通過“邦試”,他考入毛爾布隆神學校,由于不堪忍受經院教育的摧殘,半年后逃離學校。之后他游歷了許多城市,從事過多種職業,當過書店雇員、機工等。1899年,黑塞遷居瑞士巴塞爾,并于1923年加入瑞士籍。黑塞先后出版了《彼得·卡門青特》《在輪下》《玻璃珠游戲》等以“成長/教育小說”著稱的文學作品,194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2年在瑞士家中去世。
受家庭影響,黑塞自幼博覽群書。廣泛的閱讀,使黑塞對追求知識、智慧、靈性完善的古典人文主義教育充滿憧憬,但坎坷的人生經歷、精神與現實的重重阻隔,又使他常常反思教育自身的諸多缺陷:把“教育”功利化為“進身之階”的途徑自然是黑塞所不能認可的,但一味沉湎于精神領域的古典教育所造成的受教育者與現實世界的疏離,這也是黑塞需要思考的問題。古典人文主義教育使我們向往充實的、富有美感的生活,但由于它的孤芳自賞卻易使人消極地沉溺于精神的享受之中,而難與現實融合;如何處理好教育與精神成長的關系,一直是黑塞“成長/教育小說”所關注的主題。
1904年發表的《彼得·卡門青特》使黑塞一舉成名,這是一部具有濃厚自傳色彩的小說。主人公卡門青特生活在農村,后到城里尋求生活之路,他想成為一位作家,便著意和藝術家、文學編輯以及有文化的人交往,但都市文明的鄙陋使他處于苦悶彷徨之中,鄉間的淳樸一次次牽引他回鄉的目光,但每一次回鄉都使他更加失望,所以他的靈魂無所皈依,在友善的人群中行走,卻不能走進他們的生活,他深深地為之苦惱,后來他遇見殘疾少年波比,在照顧波比的過程中,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最終明白把自己消融在他人的生活里是一種最大的幸福,一切生活的愛和痛苦都可以升華,只要我們并沒有忘記那些生命旅程中已經過去然而并沒有丟失的東西,例如我們曾經想成為一個詩人的夢想,“成長/教育”可以幫助我們發現那個不曾遠離卻被我們忽視的自己。在自然的懷抱中,卡門青特找到親切、溫暖和真實的生活,從而獲得心靈的平靜。
這部作品在創作上的成功,使得年輕的作家同給予他名利的世界達成了暫時的和解——教育似乎有助于人的精神的成長,但隨即黑塞便看到窳敗的現實只是把教育當作社會等級大門的一塊敲門磚,而并不真正關心人的內心成長,在《在輪下》(1906)這部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黑塞對這種“教育”的反思。
漢斯被眾人認為是一個天才,有“一雙嚴肅的眼睛、聰明的前額、優雅的步態”,愛好虛榮的父親和老師們以沉重的學業壓迫他,使他總是帶著“一張睡眠不足的臉,一雙眼圈發黑、疲憊不堪的眼睛,默默地像受人驅趕似的到處走動”。對于拉丁文、希臘文,他是那樣沒有自信,他逼迫自己潛心于那些動詞的變位,然而這其中并沒有多少樂趣;他所做的,無非是害怕成為一個平庸的人的最后掙扎。在邦試結束后,他心懷恐懼地等待著結果——“假如進神學校、進高中和大學都不成功,那會怎樣?他會被送到一家干酪鋪去當學徒,或是到一個寫字間去當辦事員,這樣,他就一輩子做一個他瞧不起的、絕對不愿做的庸庸碌碌的窮人。他那張俊俏聰明的臉扭成一副充滿憤怒和痛苦的怪相。”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他以第二名的身份通過了考試,成為神學校的學生,凱旋之后,追求功名之心抬頭,“而今他自己身上也漸漸滋長了出人頭地、不容他人趕上自己的驕傲情緒”。他埋頭于學業,爭取第一是他唯一的理想,因此,他認為他可以忍受神學校荒寂艱辛的生活。
這是一個被眾人操縱的少年,他不明白自己學習的目的,也沒有懷疑過自己所過的生活,直至他的朋友海爾納出現。海爾納教會他思考,“你本來并不喜歡、也不是自覺自愿地去做這一切功課的呀,而只不過是出于對老師或是對你父親的畏懼。”海爾納是一個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寵兒,生性酷愛自由、感情奔放、性格倔強、充滿幻想,無視一切“神明”,他給一直拘囿在自己狹小天地的漢斯打開了一道通往自己心靈的窗,卻沒有指引發現自己心靈的漢斯如何爭取自己的生活。他忽然消失了一因為出逃而拒絕悔過被學校開除,留下漢斯獨自_人面對他已無力面對的日復一日枯燥的神學校的學業生活。漢斯終于崩潰,拖著病體返回家鄉,等待面對父親的冷眼和老師的失望。
人,一旦看不到生活的目標,就容易陷入絕望——這是庸俗化教育的結果。回鄉之后,“死”成為一個意念,縈繞在漢斯的心頭,在這種憂慮與孤寂之中,它以一個安慰者的面貌接近這位患病的少年,可是關于“死”的幻想和恐懼使漢斯陷入了一種有規律的“悲傷”之中,他知道人不可能去死,“他緩慢地、無法抗拒地陷了進去,就像陷進一塊軟綿綿的爛泥地一樣”。“現在他漫步在秋天的田野上,屈服于季節的影響。已是深秋季節,無聲的落葉,枯黃的草地,清晨的濃霧,植物的成熟、枯萎和死亡,使他像所有的病人一樣感傷不已,惆悵滿懷。他希望自己消失、安眠、死亡,然而他那年輕的生命力違反這種愿望,并堅韌地默默地活著。他感到痛苦萬分。”
他死了,在一個疲憊的午夜。他穿上一件嶄新的藍色鉗工制服踏上學徒的道路,“每當他經過學校、經過校長或數學老師的家、經過弗萊格的作坊或是牧師的家,他心里就很難受。那么多辛勞、努力、汗水;犧牲了那么多小小的歡樂,那么多的自豪和虛榮心以及充滿希望的美夢,一切都白費力氣,這一切只不過為了使他現在,比他所有的同學都更晚些,能進工廠去當一名最小的徒工,受眾人的嘲笑!”荏弱的身體使他無力擔負繁重的體力勞動,頑固的頭痛使他不能專注于任何一門功課,衰弱的神經使他無法面對現實中的一切人和事,在一個醉酒的午夜,他踏上了不歸路。
這是一個沒有出路的人的掙扎,他的所有掙扎只能使他愈來愈深地陷入命定的生活,如果他的心中沒有出人頭地的愿望,也許他會成為一個出色的鉗工;如果他的心中沒有對自然的憧憬,也許他會成為一個本分的牧師:如果海爾納沒有教給他懷疑,也許他會和他的同學們一樣,心甘情愿地馴服于一種制度,成為“教育”的榜樣;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世人把教育當作牟利的手段,而非精神完善的途徑,所以任何有悖于自然的教育都是黑塞所竭力批判的;回歸自然,即使在周圍世界中找不到一席生存之地,也要固守一種純凈的人生——自然是最好的教育,它使我們精神自足。
果然如此嗎?成長中的黑塞不斷回顧這一年輕時關于教育的夢想,越來越感到茫然。他曾說:“一個孩子誕生時處于一種與一切協調一致的狀態。一旦這個孩子受到關于善與惡觀念的教育之后,他就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個性形成過程,這就是絕望和疏離的根源。蓋因他已被人教知法律和道德規條,但卻感到無法遵守由傳統宗教或者道德體系所建立的那種專橫的標準,因為其中排除了看來非常自然的東西。”黑塞漸漸將教育看作人與天然本性疏離的過程,天然本性是在善惡觀之外的理想狀態,黑塞的這一觀念中有一點亞當在伊甸園吃知識樹上的果子的意味,教育就是一種知善惡的過程,人一旦知善惡,人性就被分裂,再回到伊甸園就很難。人性的惡成為了生活中必須面對的問題,怎樣對待人性的分裂,這是黑塞“成長/教育小說”思考的一個關鍵點。黑塞感到困惑的是那種他深深迷戀并為之沉醉的、有助于人類精神成長但又回避人類精神困境的“教育”,精神是一種象征,黑塞對此既信仰又懷疑,這種矛盾幾乎貫穿他所有的“成長/教育小說”,愛痛交織,情感的分裂與生命的融合并存;黑塞晚年創作的《玻璃珠游戲》(1942),則試圖從宗教與哲學的理想教育中挽救一個瀕臨毀滅的精神世界,然而他并不能完全說服自己。
這是一本并不太容易讀的小說,初讀起來特別枯燥,但是,只要你有足夠的耐心,就會發現在他冗長的敘述里有一個你所渴望的世界。
卡斯塔利亞是一處培養精神人才的圣地,這里的學生經過嚴格的挑選,他們是全國的精英,來到這里后必須進行苦行僧式的修行,斷絕與外界的一切往來,完全沉浸于純粹的精神“玻璃珠游戲”之中,鉆研數學、音樂、宗教、哲學等一切人類知識,以獲得精神的最高褒獎——“玻璃珠游戲大師”的稱號。但是無論是受教育者還是教育者,他們都不知道這一行為的目的,除了精神的自救以外,于現實有何補益?小說的整個情節都籠罩在這樣一種充滿懷疑的情緒中。卡斯塔利亞的教育經費由國家專項撥款,這里的人們過著雖然清苦但至少是衣食無虞的生活;但如果失卻國家的投資和支持,它就會瓦解:所以,我們的故事必須發生在一個沒有生存之憂的時代里,這是精神不能自足的缺陷之一。
小說的主人翁克乃西特自12歲就來到這里,他刻苦好學,接受嚴格的教育與訓練,最后集世界文化之大成的玻璃珠游戲藝術于一身,“玩”成游戲大師,并擔任領導者。然而,他的每一次探索,每一次超越,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伴隨著內心深處越來越濃重的痛苦和懷疑。特西格諾利,是卡斯塔利亞的一位旁聽生,他是克乃西特的終生的對手與朋友。特西格諾利與克乃西特是完全相反的人,他代表世俗生活,克乃西特代表精神領域。開始兩個人都不遺余力地為自己生活的世界辯護,特西格諾利稱卡斯塔利亞是“狂妄自大的經院哲學精神”,認為卡斯塔利亞不事生產,脫離現實的精神教育毫無價值可言,而克乃西特則堅決站在卡斯塔利亞一邊,與對手進行激烈的辯論。克乃西特認識到對手的話不是沒有道理,在沒有放棄卡斯塔利亞精神的原則下他承認對方的世界是自然的、原生態的,是永恒的存在。爭論使他們彼此更加堅定自己的選擇:一位堅定地返回塵世,從事實業:一位堅定地留在卡斯塔利亞,進行探索。
事隔多年之后,他們再一次相逢,兩人都在各自選擇的世界里深感疲憊,那一夜,他們艱難地坐在一起交談卻彼此無話可說。克乃西特憂傷地看著年少時的朋友,心想: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痛苦居然把一個天性活潑的青年變得如此壓抑?他揣測那必定是一種自己完全陌生、完全無知的痛苦。這時的克乃西特已成為“玻璃珠游戲”大師,統領一個王國,被命運牽引,顯得那么孤獨而又順從。他為朋友的痛苦而感到痛苦,也為自己不能理解對方的痛苦而痛苦,這不能理解的痛苦構成了他渴望了解世俗人們的誘惑。“我們當時也都懷著善良愿望,而我們卻受善良愿望的驅使把自己折磨得死去活來,甚至無法忍受。”他們都渴望進入對方的世界,他們的友誼并沒有因為分歧而破裂,于是他們又有了后來的交往。
特西格諾利的存在,再次引發克乃西特對“精神”自身可能存在的局限進行思考:生活在卡斯塔利亞的是一些可憐可悲的人,虛偽地停留在永恒的童年之中,天真而幼稚地蟄居于圍著密密的籬笆墻的又整潔又乏味的兒童滑稽戲天地里。……每一種強烈的感情,每一次真誠的熱情沖動,每一場心靈波動都迅速果斷地被扼殺,以致永遠消逝,而外面世界中生活的窮苦人們,這時卻在骯臟的污泥里,生活在真實的生活中,干著真實的工作。——面對特西格諾利的質問,克乃西特的回答是:“你對我們的世界懷有怨恨,同時又滿懷絕望的依戀之情。”每一場游戲,都具有一種激動人心的色彩,表達一種悲劇性的懷疑與放棄,我們撰寫的每一場游戲都竭盡全力從內心尋求解答,再以最高貴的態度放棄這種解答,就像一首首完美的哀歌,悲嘆美好事物的倏忽而逝和一切精神追求的可疑之處。有誰不會為這樣的游戲既感到絕望而又滿懷向往之情?懷疑是為了堅信,但是誰也沒有辦法否認,純粹的精神游戲阻礙了我們體驗真實的生活。
于是,克乃西特想:為什么精神和世俗這兩個世界不能像兄弟般和睦共處呢?為什么人們竟不能夠讓兩者在每個人的心里聯合一致呢?其實,早在克乃西特抵達卡斯塔利亞之初,他就已經目睹許多同學的離開,他們或許因為不能忍受卡斯塔利亞的教育方式,或許是因為看穿卡斯塔利亞人的虛弱無力,或許是因為感到內心的拯救無望,或許是因為無法抗拒外面世界的召喚,總之,他們匆匆來了又匆匆離開,他們決定回到塵世,做一個世俗的人。他們離開時最具說服力的理由就是:留在卡斯塔利亞的人,是逃避生活的人,而他們不愿意做一個逃避生活的人。“這個我們業已離開的遙遠世界發出如此強大的吸引力,也許完全不是針對那些意志薄弱和精神卑劣的人。也許他們那種表面上的跌落(世俗世界)根本不是什么墮落和遭難,而是向前躍進和向上運動。也許我們規規矩矩留在卡斯塔利亞的人才是名符其實的弱者和懦夫。”當人們普遍認為無法承受卡斯塔利亞的嚴峻考驗而退回到世俗世界的學生是精神卑劣或意志薄弱的人的時候,克乃西特卻為他們作了這樣的辯解,他認為留在卡斯塔利亞的人們,由于不敢接觸現實世界而一味沉湎于精神的游戲,這才是真正的弱者和懦夫。克乃西特雖然躲藏在卡斯塔利亞進行精神的游戲,但是,他卻從來沒有放棄對游戲本身的懷疑和對自我選擇的反抗。
所以,克乃西特的內心一直潛伏著返回世俗世界的沖動,最終,他決定離開卡斯塔利亞,到現實生活中去,去做些具體的、有社會意義的教育工作。但是他的嘗試尚未開始,就因為溺水身亡而終結。精神是易碎的,即使沒有現實世界的觸碰,它也會因為自身的纖弱而不堪面對一片湖水,誰能保證它不會自傷其身而化作一粒淚水?更何況一次巨大的塵世冒險?當黑塞向我們宣告精神世界的美妙奇特時,他并沒有因此而隱瞞這個世界先天的孱弱和其中暗藏的欺騙。
值得說明的是,克乃西特的死僅僅是一個傳聞,黑塞讓自己的主人公的生命消失在傳聞中。他沒有回答我們關于“精神”的詢問,是因為他和我們一樣缺少回答的勇氣嗎?不是的,這個故事中克乃西特從2200年的卡斯塔利亞消失之后,又化作三個形象——“呼喚風雨的大師”、“懺悔長老”和“印度王子”,從遠古飄忽而至,娓娓訴說另一個世界的傳奇。“上帝把絕望遣送給我們,并不是想殺死我們;上帝送來絕望是要喚醒我們內心的生命。”
黑塞以一種最感人的方式描寫了人類精神上的自相矛盾,從19世紀末的唯美主義,經過表現主義,而至現代人類的負罪意識,在與現代文學發展平行的文學生涯中,黑塞在他的故事中書寫一個個青年在成長的過程中對于精神追求的那些朦朧渴望,從完美主義者到逃避主義者再到堅定的理想主義者,其間的道路艱難崎嶇。黑塞的每一部小說都假定了一個可能的精神王國,那是他的主角全力以赴的精神目標,不管他最終是否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