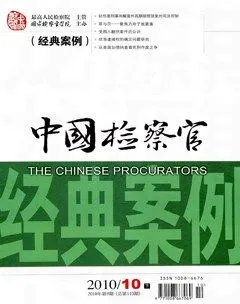有組織犯罪若干問題的實踐性檢討
本文以一起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為切入點,從司法實踐的角度界定有組織犯罪的概念,同時探討實踐中對有組織犯罪實體法的訴求和程序法的期待問題,并提出了相關對策。
[基本案情]被告人高某糾集有前科的社會青年,形成以高某為首,以尹某、汪某(另案處理)、張某(另案處理)為骨干成員的犯罪組織。尹某主要負責管理由丁某等六人組成的打手;張某帶領一幫人插手政府拆遷;蔡某為高某開車,并與宋某、尹某三人充當高某的保鏢。尹某帶領丁某等打手集中住宿,配發砍刀、槍支、通訊工具,不定期發給報酬。對外以“高某公司”為名號(實際上既無實體。也無注冊,僅稱呼而已)。2007年初至2007年10月份以來,到娛樂場所“收保護費”、非法索要債務、拆手政府拆遷、強行向酒店銷售假冒白酒。2007年11月7日,高某帶領手下攜帶刀、槍準備與另一幫派進行毆斗。結果誤將無辜百姓趙某父子打傷,因此而案發。2007年12月25日。公安機關將正在圣誕聚餐的高某等170余人抓獲,后因證據不足,僅逮捕10人。
一、問題的提出
由于理論界對有組織犯罪概念、特征及其與我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之間關系等方面的研究,實踐性探索和規范性思考略顯單薄,故此導致在打擊有組織犯罪時遭遇重重困境。對上文所舉案例,是否可以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爭議很大:一種觀點認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必須有經濟實力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現有證據只有各被告人供述證明收保護費、插手拆遷、推銷白酒,但被害人不愿作證,插手政府拆遷也沒有獲取政府方面證據;如何獲取經濟利益及獲取多少利益均無法確定;非法控制也無法證實,因此不能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另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利益只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犯罪的目的,無需證明具體的經濟實力,根據《刑法》394條的罪狀描述,本案完全符合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特征。該案最終僅以聚眾斗毆罪和非法持有槍支罪進行起訴和判決。這一無奈的處理結果,引發我們對有組織犯罪的有關概念、實體法及程序法等方面的思考。
二、實踐需要什么樣的有組織犯罪概念
前述案例的爭議,表現出學界和實務界對我國刑法中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概念和特征認識上的分歧。法學理論終究是要服務于司法實踐的,對有組織犯罪的界定應當結合本國的刑法規范及司法實踐。對于我國刑法來說。首先需要解決的是有組織犯罪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之間的關系。有人認為國際上通行的有組織犯罪相當于我國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有人認為有組織犯罪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是有組織犯罪的一種形式.除此之外,還包括集團犯罪和組織程度較低的團伙犯罪。其實,只要厘清“黑社會犯罪”與“有組織犯罪”術語的來歷,上述問題便可迎刃而解。黑社會"un-der-word society"起源于西方。最初原文為"svicieter so.ciety",含義為“邪惡的幫會”,西方人簡稱為“黑色幫會”.我國把它譯為“黑社會”。至于其法定名稱,最初有人稱為“enterprise crime”即企業型犯罪,但不久被否定.最終"organized crime"經聯合國刑事司法處認可。由于"organized"是一個被動(過去時)結構,因此直譯應為“已經組織化了的犯罪”,表明是一種有組織體制的犯罪。從有組織犯罪術語的來源、演化可以看出.有組織犯罪即黑社會犯罪,兩者是等同的。刑法學是規范學,刑法學意義上的“有組織犯罪”概念必須是一個規范性的概念(這一點與犯罪學是不同的),結合我國的刑法規范中的“黑社會性質組織”。那么國際上通行的“有組織犯罪”與我國刑法中的黑社bl0TytUcRcZoI2yhowguew==會性質組織犯罪應該是相對應的,可以在同等意義上使用。
對于司法實踐來說.或許對有組織犯罪的定義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這一點正如日本學者長井圓所指出的“不過我們并不總是只需要有組織犯罪的簡單定義。眾多不同的定義取決于各國各地區研究有組織犯罪的目的和產生于受不同國家、地區的不同文化、政治、和社會經濟條件影響的社會現象及其制度結構”。對于司法實踐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學理上能提供有助于認定有組織犯罪的若干特征。對有組織犯罪定義或許是困難的,但是結合我國的實踐和現實,并結合國際最低限度的標準,找出具有共性的特征,應該不是難事。既然有組織犯罪作為國際社會的通病,那么,就一定存在一些共同的“交集部分”。
首先,既然是有組織犯罪,那么作為一種組織化了的犯罪結構,組織結構特征就是必備的。同樣,既然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就必須具有“社會”性的組織結構,就我國刑法規范及司法實踐來說,至少是三人以上組成的,有明確的組織、領導者,成員相對固定和有一定分工。例如前述案例中以高某為首領,以尹某、汪某為骨干成員,打手、拆遷、推銷白酒等分工相對明確。
其次,既然有組織犯罪集團與黑社會(性質)組織具有同等意義,那么,黑社會與正常社會的區別就在于其反社會性。反社會性主要體現在非法控制上,具有長期生存的基礎和防護體系,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領域內,形成非法控制。這里的非法控制,不可能向意大利黑手黨一樣,要求其控制一個政黨或向政治領域滲透,因此,不一定需要政治上的“保護傘”,其所控制的既可以是一條街道、一個區甚至是一個城市:也可以是一個領域,如前述案例中的娛樂行業,也可以是多個行業或領域。
最后,通過實施暴力、威脅或其他非法手段.獲取經濟利益。一般認為暴力性是構成我國刑法黑社會(性質)組織不可缺少的要件,但近年來黑社會犯罪呈現軟暴力化的趨勢,比如在初期靠暴力起家,后來“漂白”成合法公司運作,此時司法機關再獲取其起家時暴力方面的證據,難度很大。事實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下文簡稱《公約》)也沒有要求暴力性,而日本的暴力團經過修改“不限于暴力性犯罪組織,亦不需要行使暴力或者威脅手段。”另外,獲取經濟利益是有組織犯罪的基本追求(或者說是犯罪目的),也是《公約》最低限度的共識。這對我國情況而言,同樣是適用的,但卻并不需要像美國學者所界定的那樣成立企業或公司。我們認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對于經濟利益的追求,在犯罪構成上,只需要作為犯罪目的進行理解。在證據上也只需要達到普通目的犯的證明標準.無需像證明客觀要件那樣必須證明經濟利益的來龍去脈和經濟實力的大小。
三、實踐對有組織犯罪實體法的訴求
法律不僅需要被法學一再解釋,“也必須被‘填補漏洞’,并且要配合情勢的演變”。前述案例最終無法以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起訴和判決,原因之一在于立法上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界定不明,歧義重生,導致司法實踐中各執一詞。從司法實踐對實體立法的訴求來看,最要緊的莫過于對有組織犯罪的罪狀進行明確化修改。
(一)“黑社會性質組織”用語缺乏科學性
我國刑法規定的有關有組織犯罪主要是《刑法》第294條中的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入境發展黑社會組織罪,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如前所述,國際上通行的有組織犯罪與黑社會犯罪具有同等意義,我國刑法沒有必要“別出心裁”地創造出個新的名詞。如果說當時的立法者是考慮到“在我國.明顯的、典型的黑社會犯罪還沒有出現”,那么時至今日,從喬四案、張君案、劉涌案,到最近的重慶萬貫財務公司陳坤志案……雖然比上意大利的黑手黨。但是與我國港、澳、臺的黑幫、美國的摩托車黑幫等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良苦用心”似乎已經不合時宜了。實際上,我國大陸目前黑社會犯罪形勢的嚴峻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既不利于國內有組織犯罪的打擊,也不利于打擊有組織犯罪的國際合作。最典型的缺陷表現在以下三種情況:(1)參加境外的黑社會犯罪行為無法定罪.因為我國刑法規定的是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但由于行為人參加的是境外黑社會而不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因此。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不能以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定罪處罰:(2)境外的黑社會組織在境內從事黑社會犯罪活動的行為無法定罪,因為我國刑法僅規定了境外的黑社會到境內發展成員的,構成入境發展黑社會組織成員罪,對于其從事發展成員以外的犯罪活動,由于刑法缺乏規定而無法定罪;(3)包庇縱容境外的黑社會組織成員的行為無法定罪,因為我國刑法僅規定了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而對于行為人包庇、縱容黑社會(而非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在刑法上也缺乏規定。對此.有人主張增設新罪名。其實產生上述立法漏洞的原因不在于刑法罪名覆蓋面不夠,而是在于使用了“黑社會性質組織”這個不倫不類的術語,而無法與國際對接所導致的。只需將“黑社會性質組織”修改成“黑社會”,上述問題均可迎刃而解。
(二)立法對有組織犯罪構成要件描述缺乏明確性
我國《刑法》第294條以近乎文學化的語言對黑社會性質組織進行了界定,即“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這里的“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均屬非法律用語,歧義重生,含義模糊.在實踐中如何用證據來證明這些帶有強烈主觀色彩和文學色彩的表述?這種不明確的話語,既可能擴大打擊面。也可能縮小打擊面,給司法實踐造成適用上的困難。
在立法上對黑社會組織進行界定,或許短期內達成一致意見還相當困難,但是如前所述,有些特征是共通的。當我們無法界定一個事物是什么的時候,我們可以確實什么是該事物。因此,根據有組織犯罪(黑社會犯罪)共通的特征,立足于我國的打黑現實,并結合《公約》最低限度的要求,進行立法上的界定,應該是基本的努力方向和研究思路。我們冒昧地按照這種方向和思路.結合前文概括的有組織犯罪的三個特征,并結合有關立法解釋和《公約》,提出如下立法建議供批判:由三人以上所組成的骨干成員穩定、為了獲取經濟利益而有組織地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并在一定的區域或行業形成非法控制勢力的組織,是黑社會組織。
四、實踐對有組織犯罪程序法的期待
本文開頭引用的案例,當地群眾都稱“高某公司”是黑社會。甚至坊間傳言:誰家的小孩哭鬧,大人就以“高某來了”來嚇唬小孩不要哭鬧。公安人員在實施抓捕行動時.一舉抓獲高某等正在圣誕節聚餐的170余人.但因取證不到位最終逮捕的只有10人。該案最終只能以普通犯罪起訴和判決,固然與實體立法不明確而導致的分歧有關,但同樣也有程序立法滯后所導致取證不能的原因。有組織犯罪組織化、隱蔽化、智能化的特征,使得取證困難成為我國當前打擊有組織犯罪的瓶頸問題。司法實踐最大的期待之一就是對有組織犯罪在程序立法上規定特別的偵查措施和程序。
(一)成立專門機構
西方一些國家在議會下設打擊有組織犯罪專門機構。負責直接指導、監督和協調全國的打擊有組織犯罪工作。如意大利議會下設反黑手黨委員會;美國除議會的相關委員會以外,在白宮還專設直屬總統領導的有組織犯罪調查委員會。我國目前對黑社會犯罪的偵查仍然依賴于公安機關,盡管公安機關內部設立了“打黑處”.但是畢竟只是公安機關內部設置,力量、技術以及擺脫地方行政干涉的能力都相當有限,更為重要的是在挖出“保護傘”上因無職務犯罪偵查權而只能請求檢察機關協助。但畢竟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屬于不同建制,領導指揮步調不一、溝通協調管道不暢,在所難免,這必然使打擊黑社會犯罪的時機、力度大打折扣。盡管有時各地政法委出面進行協調,或者成立由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參加的專案組,畢竟只是臨時措施,難以形成長效機制。
本文開頭引用的案例,對于高某等插手政府拆遷,相信必定有政府人員陷身其中,之所以取證困難,沒能“拔出蘿卜帶出泥”.揪出“保護傘”.主要癥結在于缺乏專門的機構設置。因此,為適應我國反擊有組織犯罪的實踐訴求,必須建立獨立的反黑機構,可以考慮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下設全國反黑機構,各省、市級人大常委會下設分支機構,為防止來自地方“保護傘”的阻力,區、縣一級不宜設立反黑機構。
(二)秘密偵查法制化
我國目前的秘密偵查在實踐中遭遇兩種尷尬局面:其一是“能作不能說”,秘密偵查的操作只有公安機關的內部規定,不能對外;其二是“作了也白作”,由于秘密偵查沒有得到立法認可,因此秘密偵查獲取的證據不能直接作為證據使用,而必須經過“轉化”才能作為證據使用。這樣的現狀,既妨礙秘密偵查作用的發揮。更容易侵犯人權。
為此,西方很多國家在立法上都確立了對有組織犯罪實行電子監控、臥底行動等秘密偵查措施。《公約》第20條也允許在適當的情況下使用其他特殊偵查手段,如電子或其他形式的監視和特工行動,以有效打擊有組織犯罪。本文開頭引用的案例,公安機關抓獲高某170余人,最終只逮捕10人,其余一一釋放,原因就在于偵查不力.未能在抓捕前通過秘密偵查而摸清該組織的情況,并掌握相關證據。當然秘密偵查措施猶如雙刃劍,有侵犯隱私和觸犯人權之風險。所以,必須建立相應的正當化程序,包括審批程序、秘密偵查的范圍和時間限定、秘密偵查后告知程序等,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審批程序。一般來說,秘密偵查需要由中立的第三方即法官批準以起到監督制約之功效,但就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如逮捕措施一樣,權宜之計應當還是由檢察機關批準。
(三)完善證人保護制度
為分散和瓦解黑社會組織.西方國家的警察部門近年來非常注重對證人的保護工作。美國不惜花費高昂代價建立“證人保護項目”(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由美國法警局審核是否參加證人保護項目,一旦被允許加入。證人及其家庭會被安置在國內危險比較少的地方,并提供新的身份和經濟支持直到證人能找到可靠的工作,盡管花費高昂(2003年美國為執行該項目花費6000萬美元),但是效果很好,在受到保護的證人出庭作證的案件中.定罪率高達89%。
我國證人保護的立法,可謂一片空白。普通犯罪的證人作證尚且有難度,更何況是涉黑犯罪。民眾對黑社會惟恐禍及己身而避之不及,哪里敢出面作證。本文開頭引用的案例.我們在審查起訴過程中也曾試圖說服證人作證,但最終均無功而返,我們切身感受到我國建立證人保護制度的緊迫性。在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空白的情況.權宜之計是先建立反黑社會犯罪的特別證人保護制度,對于涉黑案件中的證人提供其免受威脅的必要保護。另外,也有必要建立類似污點證人制度,對于愿意配合司法機關作證的被告人,可以做相對不起訴或者在審判量刑時予以從輕處罰。
五、余論
我國涉黑犯罪形勢越來越嚴重,司法實踐中遭遇的困境越來越大,司法實踐對有組織犯罪在實體和程序方面的立法,均有諸多緊急而迫切的期待。世界上多數國家為應對有組織犯罪均進行了單獨立法,如美國《反有組織犯罪侵蝕合法組織法》(RICO法案)、日本的《反暴力團法》等。我國臺灣地區的《組織犯罪防治條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有組織犯罪法》也值得借鑒。為了有效應對有組織犯罪,滿足反擊有組織犯罪的司法實踐訴求,有組織犯罪立法建構和完善應當列入關注視野。我們認為,有關實體方面的立法,可以通過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對現有刑法進行完善;而程序方面,鑒于有組織犯罪偵查的特殊性可以考慮單獨制定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