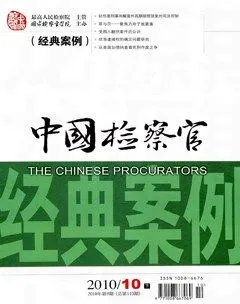偽造動拆遷協議騙取契稅行為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方慶姬、高曉春、姜慧芬、陳秀榮系房產中介人員。其利用本市稅收優惠政策,偽造動拆遷安置協議.由購房者以假冒動拆遷戶的身份向區財政局申請契稅退稅.并從中分得退稅款的55%作為報酬。方慶姬等人采用上述相同手法,在本市虹口、黃浦等地伙同多名非動拆遷的購房者,共辦理契稅退稅12起,騙取國家契稅款人民幣44萬余元。案發后,購房人均已補繳契稅款。
二、分歧意見
對于本案的處理,司法實踐中存在三種分歧意見:第一種觀點認為,本案涉案人員的行為均不構成犯罪。理由是:首先,本案侵犯的主要客體是國家稅收征管秩序,而非公私財產所有權,因此不構成詐騙罪;其次,房產中介與購房者經事先通謀,偽造動拆遷協議,騙取契稅退稅款,侵害了國家的稅收征管制度,符合逃稅罪的構成要件。因購房人在事發后已補繳稅款,并接受行政處罰,根據《刑法修正案(七)》第3條第4款的規定,應不予追究刑事責任。房產中介人員與購房者屬于共同犯罪,且逃稅罪的主體需為納稅人,在購房人不構成犯罪的情況下,房產中介也不應定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本案涉案人員的行為均應構成詐騙罪。理由在于:首先,房產契稅關系中,購房人在繳納稅款后就喪失了納稅人的主體資格,其所實施的騙取契稅退稅款行為侵犯的就不是國家的稅收征管秩序;其次。不管是房產中介人員還是購房人都是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合謀通過虛構動拆遷戶身份的事實騙取國家的房產契稅退稅,侵害了國家的財產所有權,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應以詐騙罪定罪量刑。
第三種觀點認為,房產中介人員的行為應構成詐騙罪,而對購房人應不追究刑事責任。
三、評析意見
筆者認為,對本案中涉及的兩類人員應區別處理,即對房產中介人員應以詐騙罪定罪處罰,而對購房人則不追究其刑事責任:
(一)房產中介人員的行為應認定為詐騙罪
首先,房產中介人員不是納稅人,無法滿足逃稅罪的特殊主體要求。按照刑法理論的通說,逃稅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納稅人和扣繳義務人。然而,也有人認為不管單位還是個人.也不論他們是否從事生產經營都可能是納稅義務人,在逃避繳納稅款的情況下都可能成為逃稅罪主體。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對特殊主體的一種誤解。我國刑法要求特定的身份,是指與一定犯罪行為有關的,行為人在社會關系上的特殊地位或狀態,如特定的職務,特定的法律地位,負有某種特定的法律義務,特定的職業等…。就納稅人而言,其是否產生納稅義務是區分納稅人與否的必要條件。盡管所有單位和個人都有可能成為納稅人.進而成為逃稅罪的主體,但是應該看到,就不同的個體而言,要成為納稅人還需具備一定的必要條件。在本案中.成為契稅納稅人的條件就是購買房屋,從而需要繳納契稅。顯然,若僅僅因為房產中介存在購買房屋從而繳納契稅的可能性,就認為其能成為納稅人的理論是荒謬的。房產中介因為沒有房屋買賣的行為,也就無需繳納契稅。而詐騙罪的主體則是一般主體,只要是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和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成為詐騙罪的主體。因此房產中介人員符合詐騙罪的主體資格要求。
其次,房產中介通過欺騙、隱瞞等犯罪行為騙取契稅退稅,符合詐騙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可以說,欺詐行為就是在具體狀況下,使對方產生錯誤認識,并做出行為人所希望的財產處分。本案中,房產中介與購房人共謀采用偽造動拆遷協議的方法,虛構購房人動拆遷戶的身份,使財政局工作人員陷入認識錯誤,從而給付國家財產,造成國家利益的重大損失,完全符合詐騙罪的客觀構成要件。
再次,房產中介的行為侵犯的是國有財產所有權。如前所述,房產中介不是納稅人,與房產契稅的繳納并無關系。雖然他們與購房人合謀采用偽造的動拆遷協議騙取房產契稅退稅,但是兩者索要的對象性質是有區別的。對購房人來說,其已經繳納過契稅,他通過虛構動拆遷人的身份行騙的目的,是要獲取自己已經交過的契稅中的一部分;而對于房產中介而言,其并沒有繳納過任何與此相關的契稅,他所要騙取的就是國家的公共財產,因此其行為侵犯的客體是國有財產所有權,而非國家的稅收征管秩序,符合詐騙罪的客體要件。
(二)購房人的行為符合逃稅罪的構成要件
首先,購房人的行為符合逃稅罪的客觀構成要件。根據《刑法修正案(七)》的規定,“納稅人采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構成逃稅罪。所謂“欺騙、隱瞞”,就是指用制造假象或者隱瞞事實真相等方法,使稅務機關誤認為行為人具有減免繳納稅款的情形。因此,筆者認為,逃稅行為既可以是在繳納稅款時采取欺騙、隱瞞方式逃避繳納,也可以是通過虛構、隱瞞事實騙取退稅而逃避繳納稅款。因此。本案中購房人采用虛構動拆遷戶身份的欺騙手段從財政局騙取已繳納稅款的行為,符合逃稅罪客觀方面的構成要件。
其次,購房人符合逃稅罪的特殊主體資格要求。購房人在房屋買賣關系中,向國家繳納了相關房產契稅,而在本案中,其偽造動拆遷戶的身份也是為了侵占已繳納的部分稅款,因此具有納稅人的身份。有觀點認為。購房人在繳納完房產契稅以后就喪失了納稅人的資格。筆者認為此種看法有失偏頗,對于納稅人資格的認定不能就事論事.而應該從整體角度進行把握。在本案中。購房人之所以能成功地騙取退稅款,一方面固然是因其偽造了動拆遷戶的身份,享受了其本不應享受的優惠條件,另一個重要方面則是因為其已經繳納了房產契稅,騙取的也是其繳納給國家的房產契稅的一部分。因此,在購房人申請房產契稅退稅時,整個稅收征管活動尚未完全結束,購房人還是以納稅人的身份實施騙取房產契稅退稅行為的,因而符合逃稅罪的主體要件。
再次,購房人的行為侵犯了國家稅收征管制度。國家稅收征管制度包括征稅對象、稅率、納稅期限、征收管理體制等內容。任何應稅產品、應稅項目不納稅,不按規定的稅率、納稅期限納稅以及其他違反稅收征管體制等行為.都是對我國稅收征管制度的侵犯。口’對本案的購房人而言,其在繳納房產契稅后,又冒充動拆遷戶意圖騙取已繳納的部分契稅款,以達到逃避繳納全額契稅的目的。因此購房人的行為侵犯的是國家正常的稅收征管秩序,而非國有財產的所有權。
(三)對購房人應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刑法修正案(七)》第3條4款規定:“有第1款行為,經稅務機關下達追繳通知后,補繳應繳納稅款,繳納滯納金,已受行政處罰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該條款的規定,使得行政機關的相關行政行為成為判斷是否予以追究刑事責任的基礎,對于犯罪嫌疑人意義重大。如稅務機關不能先行處罰,刑法修正案關于一定條件下可不予追究逃避繳納稅款刑事責任的規定就無法得到落實。換言之,這時不作行政處罰,對有關納稅人是極其不利的.不能體現刑法的平等原則。因此筆者認為,行政處罰前置程序是對納稅人有利的保護程序,是逃避繳納稅款處理的一般程序原則,應適用于所有的納稅人。本案的購房人都是初次逃稅,且在案發后已經補繳了全額稅款,接受了行政處罰,根據《刑法修正案(七)》的相關規定,當事人已受稅務行政處理與處罰,就無須移送司法機關,而應作不予追究刑事責任處理。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房產中介人員和購房人雖然都在非法占有的故意,共同通過偽造動拆遷戶的事實來騙取房產出口退稅,但是由于二者的主體身份不同,侵犯的法益亦有區別,因此不能以詐騙罪或逃稅罪的共犯對其進行處罰。此外,本案是由房產中介人員主動向多名購房者提出詐騙犯意。其主觀惡性程度相比較購房者而言更為嚴重,且購房人已經接受了行政處罰,所以筆者認為對本案中的房產中介人員應以詐騙罪定罪處罰,而對購房人則不追究其刑事責任。這種處理方式一方面打擊了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騙取國家房產契稅行為。保護了國家的稅收收益,另一方面通過非犯罪化的處理方式適當縮小了打擊范圍,也可以給予逃稅行為人悔過的機會,維護社會的穩定,鞏固穩定稅源,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