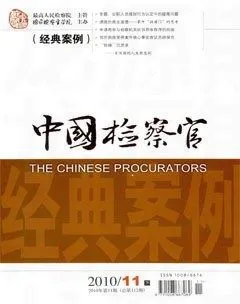國有資產與職務行為的性質認定
根據王某案定性的爭論,本文從以下四方面進行分析。
一、本案中經濟實體的財產是否屬于國有資產
1993年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國有資產產權界定和產權糾紛處理暫行辦法》第2條對“國有資產”作了明確定義,即國有資產是指國家依法取得和認定的,或者國家以各種形式對企業投資和投資收益、國家向行政事業單位撥款等形成的財產。1999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附則部分對國有資產界定為:“國家依法取得和認定的,或者國家以各種形式對企業投資和投資收益、國家向行政事業單位撥款等形成的資產。”2006年財政部《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的事業單位國有資產,是指事業單位占有、使用的,依法確認為國家所有,能以貨幣計量的各種經濟資源的總稱,即事業單位的國有(公共)財產。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包括國家撥給事業單位的資產。事業單位按照國家規定運用國有資產組織收入形成的資產,以及接受捐贈和其他經法律確認為國家所有的資產,其表現形式為流動資產、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對外投資等。”根據上述規定,國有資產主要有三大類:一是國家依法取得和認定的國有資產;二是國家以各種形式對國有公司、企業投資形成的財產和投資收益;三是國家向行政事業單位撥款等形成的財產。具體到本案中,既涉及到行政事業單位資產,又涉及到行政事業單位投資后所形成的經營性國有資產。我們認為,不管畜牧站收益能否滿足日常開支,畜牧站的資產屬國有資產無疑。這既可能是國家撥給,也可能是在按照國家規定卻有國有資產組織收入形成的資產,因此,畜牧站對實體的投資應屬于國有資產。但整個經濟實體并非國有性質,因為其中還有個人出資的參與,并且王某個人與畜牧站的出資也未分清,故實體的性質應認定為有國有資產成分的混合經濟組織。
二、王某處置經濟實體資產的權限與職務的關聯問題
王某是該經濟實體的發起人和經營者,是實體日常經營的負責人,也是事業單位畜牧站出資的具體代表者,當然有權處置經濟實體的資產。但處置資產前,依《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中第23條:“事業單位對外投資收益以及利用國有資產出租、出借和擔保等取得的收入應當納入單位預算,統一核算,統一管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第24條:“事業單位國有資產處置,是指事業單位對其占有、使用的國有資產進行產權轉讓或者注銷產權的行為。處置方式包括出售、出讓、轉讓、對外捐贈、報廢、報損以及貨幣性資產損失核銷等。”第25條:“事業單位處置國有資產,應當嚴格履行審批手續,未經批準不得自行處置。”第26條:“事業單位占有、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土地和車輛的處置,貨幣性資產損失的核銷,以及單位價值或者批量價值在規定限額以上的資產的處置,經主管部門審核后報同級財政部門審批;規定限額以下的資產的處置報主管部門審批,主管部門將審批結果定期報同級財政部門備案。”等的有關規定,必須要履行報批的有關手續,本案中有畜牧站系鄉屬事業單位、管理不規范這樣一個特殊情況,王某雖然向鄉黨委請求了處理資產,在鄉黨委做為管理者沒有給予回應,王某擅自處理資產后,將18萬元用于畜牧站開支,我們認為,在管理者沒有履行對國有資產管理的情況下,王某等在前期18萬資產的處理中,并無不妥。
分析全案,我們注意到王某在退休后仍向鄉黨委請示處理經濟實體資產,也就是王某主觀上仍認為,經濟實體中有畜牧站的資產成分,經2002年18萬元付畜牧站后,可以認為經濟實體中即使有畜牧站的投資,也已占很小的比例,經濟實體主要股東來自于個人,故王某之后對經濟實體資產的處理主要基于其大股東的地位,與其在畜牧站的職務已沒有關聯。故我們認為,退休后處理資產的行為是基于大股東的地位,而非利用了畜牧站站長職務。
三、“從事公務”的判斷標準
“從事公務”是國家工作人員的本質屬性,是構成國家工作人員和界定《刑法》第93條規定的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主體范圍的核心因素。所謂“從事公務”是指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社會團體中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務的行為。一般而言,國家工作人員從事公務的時間始于具備一定身份職責,終于退休離職。然而,實踐中,由于辦理退休手續和工作的實際交接完成均需要一定的時間。從而導致國家工作人員在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或者符合退休條件的,辦理退休手續與交接工作往往交叉進行:有的是先辦理退休手續后交接工作。有的是先交接工作后辦理退休手續,而交接工作與辦理退休手續的具體時間及其所用時間長短,各地、各單位,甚至不同的人也都不完全相同。有的已辦理退休手續但未實際交出工作,有的雖未辦理完退休手續但已實際交出原有工作,如果一律以退休時間為準來確定行為人的主體資格,就可能導致有的人雖已退休。但仍享有職權,對其瀆職腐敗行為不負相應的法律責任;而有的人雖然還未辦理退休手續,但已經完成了工作交接,實際沒有相應的職權,卻要承擔相應的職責、負相應的法律責任的現象。為準確懲罰犯罪防止放縱犯罪的發生。同時也要注意保障人權避免出現這種責權不對等而殃及無辜,我們認為,對處于離退休階段的人員是否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應從實際出發,從單純以身份本身來判斷主體性質的標準轉變為以職權和職責為主,兼顧身份作為判斷主體性質的標準,強調職權和職責對于主體性質的關鍵性。具體而言,應以行為人實際交接工作的時間為準,認定其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相應的職權和應履行相應的職責,確定其行為是否屬于“從事公務”,這樣才能準確地區分罪與非罪。2002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中“雖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在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時,有瀆職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關于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即體現了摒棄身份論,以“從事公務”作為認定國家工作人員本質特征的基本精神。
四、結論
我們認為,王某退休后變賣經濟實體資產的行為主體上不符合國家工作人員,原因前文已進行了分析,處理資產是基于其大股東的身份。而非畜牧站的職務,不存在繼續“從事公務”的情況,因此,不應將變賣資產的行為在主體上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其行為不應認定為貪污罪。
綜上,王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2009年其處置經濟實體資產的行為,國有資產在其中只占極小部分。即便造成畜牧站資產流失,也可依財政部《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第5l條的規定,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辦法,擅自占有、使用和處分國有資產的,依據《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條例》的規定進行處罰、處理、處分,并依此追討流失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