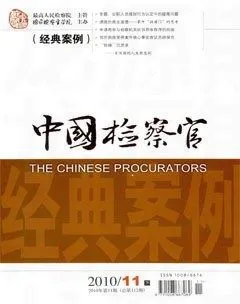劉某的搶奪行為能否轉化為搶劫罪等
[案情]劉某為無業青年,整日游手好閑,不務正業。一日,在路邊閑逛,看到一中年婦女趙某提名牌皮包走過,遂生奪取之念。劉某乃尾隨趙某走約:三米后,用力猛拽趙某提包,競然未予取得并被趙某發現后用力拉住提包,于是,劉某強拉硬拽將提包奪取。同時趙某摔倒在地。經鑒定,趙某的傷害程度為輕微傷,皮包價值人民幣3000元。
本案涉及爭議的罪名有搶劫罪、搶奪罪。
[速解]本文認為劉某的行為構成搶劫罪。
搶劫罪與搶奪罪的區分主要體現在:一、行為的暴力程度。搶劫罪的暴力是最狹義的暴力,即是指對人行使有形力,并達到了足以抑制對方反抗的程度。搶奪罪的暴力則并無此要求。二、行為侵犯的客體特征。搶劫罪的獨特性在于其侵犯的客體為雙重客體——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且從邏輯上觀察,雙重客體并非并列或等價關系,而呈現手段與目的的制約關系,由此決定搶劫罪的客觀行為分解為雙重行為——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手段行為是侵犯人身的“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的行為,目的行為是侵犯財產的非法奪財行為。換言之,對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的侵犯是由同一行為造成,則不能認定搶劫罪。對于搶奪行為而言,即使造成被害人傷害后果,由于并無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之分,只能按處理想象競合犯的原理在搶奪罪和故意傷害罪(或過失致人重傷罪)之間擇一重罪處斷。
本案中,劉某最初之行為的強制程度僅為奪取提包。并不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但隨著被害人趙某發現提包被奪進而奮力抗爭直到提包被奪的過程以及劉某造成趙某輕微傷的后果來看。劉某的行為顯然抑制了被害人的反抗。劉某的“奪包”行為表面而言只是一個行為或一個動作,但邏輯上其動作可以分解為雙重行為,首先,劉某在“猛拽”趙某提包未果后,趙某與劉某之間通過對提包的拉取必然對趙某的身體產生作用乃至傷害;其次,劉某之所以能夠取得提包是由于其強力致使趙某喪失對提包的控制。換言之,劉某是通過對趙某身體實施暴力進而獲取其財物,其雖非通過造成趙某輕微傷以取得財物但是通過使用可以造成趙某輕微傷之行為取得。劉某在看到趙某之初是有搶奪之“故意”,而在其搶奪過程中,其為了獲得財物行為暴力程度加劇,主觀犯意亦隨之轉化,對于犯意轉化而言,犯意升高者,從新意,故行文至此,可以看出劉某之行為屬于搶奪到搶劫之轉化,構成搶劫罪。
(作者單位: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檢察院[402260])
行政拘留期間如實交代犯罪事實不可認定為自首
宋 鵬
[案情]某年9月8日,某地發生兇殺案后,警方立即展開調查,通過技偵手段和對被害人相關聯系人的梳理和調查,發現沈某手機信號與被害人手機信號曾在案發現場出現過,認定其有作案嫌疑。隨即通知其到公安機關接受詢問。沈某無法講清其在9月8日的行蹤。在調查中,警方發現沈某有賭博的違法行為。即對其處以5日f后延長至10日)行政拘留的處罰,并進行獄偵,安排人員對其貼靠,促使沈某在行政拘留期間的9月20日,以自首書的形式向警方供稱被害人系其殺害。
本案爭議焦點,沈某的行為能否認定為自首。
[速解]本文認為,沈某不構成自首。
首先。偵查機關已經發現了犯罪事實,并且通過技偵手段確定了沈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通知沈某到公安機關接受詢問。這說明偵查機關已經掌握了一定的證據證明沈某有作案的可能。只是不能完全認定就是沈某作案。在調查中,偵查機關對其進行行政拘留是一種偵查手段,是在其有作案嫌疑的情況下采取的一種特殊偵查措施,是偵察機關偵察活動的繼續,而不是單純的行政處罰措施。沈某在行政拘留期間寫下自首書的時間是在9月20日。時間晚于其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的時間,況且已被控制人身自由,不是自動投案。
其次,沈某并非出于主動、自愿交代犯罪事實。自首要求犯罪分子主動、自愿投案,如實交代犯罪事實。偵查機關在掌握了沈某一定的作案證據后。通知其到公安機關接受詢問時,其并不能說清其在9月8日的行蹤,拒不交代犯罪行為,并且也沒有如實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在偵查機關采取進一步的偵查措施,通過在其身邊安排貼靠人員的情況下。才促使沈某被動交代其犯罪行為。由此看來,沈某存在僥幸心理,并不是自愿、主動交代犯罪事實,不具備自首要求的自動性要件。
2009年3月19日兩高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對職務犯罪嫌疑人認定自動投案進行了明確的規定:沒有自動投案,在辦案機關調查談話、訊問、采取調查措施或者強制措施期間,犯罪分子如實交代辦案機關掌握的線索所針對的事實的,不能認定為自首。參照該解釋的立法精神,沈某雖不是國家公職人員,但其行為也不應該認定為自首。
(作者單位: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檢察院[10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