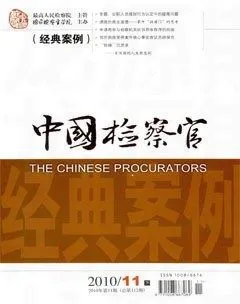當刑事法律遇上中國式改革實踐
霍姆斯法官曾經說:“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一直是經驗。”而當我們中國還不是非常健全的法律體系與中國前無古人的改革相遇的時候,我們不僅缺乏慎密的法律邏輯。甚至于更缺乏完美的經驗。
首先。任何刑事犯罪本身都是對于刑法所保護的法益本身的侵害。在犯罪的本質特征上,無論是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與應受刑罰處罰性的三特征說,還是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罪過性以及應當承擔刑事責任性的四特征說,甚至于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等等兩特征說。社會危害性都是刑事犯罪的本質特征。而社會危害性就是應受刑罰處罰程度的社會危害性。根據最基本的“誰投資、誰受益”以及“無義務。就沒有權利”的原則,在獸醫站收益狀況不能滿足日常開支的情況下。獸醫站實際上已經不具備任何投資的能力,王某、鄒某、陳某、張某、魏某等人出資興辦的經濟實體,其資產理所應當歸結于其投資人所有。而且,在該站其他職工由于考慮經營風險而未參與集資的情況下,按照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其他職工當然地不享有相應的經營權與利潤分配權。由于經濟實體本身的資產并非國有財產。所以作為貪污犯罪客觀方面的公共財物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客觀主義刑法理論又認為,刑法上的結果是指對法益的侵害與侵害的危險。因此,違法性的根據在于行為對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脅的結果,即結果惡才是違法性的根據。這便是后來被稱為結果無價值論的基本觀點。由于王某并沒有超越自己的投資范圍以及投資的權力非法取得任何國有資產,所以其對于國有資產的權益沒有發生任何侵害,也就不具備刑法規定的貪污犯罪的法益侵害性或者是符合定罪的結果無價值論。
當然,王某等在經濟實體經營過程中以及經濟實體的處置過程中,其贏利以及處置資產所得都曾經用于獸醫站這一國有事業單位,從資產的處分權上似乎可以得出經濟實體資產屬于國有資產的結論。2000年,王某請鄉黨委處理資產未果;2002年,王某出賣經濟實體資產所得款項18萬元用于獸醫站償還債務、購買辦公用品及職工家屬治病等開支。從獸醫站實際享有利潤分配權以及鄉黨委的資產處置權上,我們可能認為經濟實體應當是屬于國有資產,但是認定資產最重要的原則是經濟實體本身的投資主體。由于集資人簽訂協議約定分紅和風險承擔辦法,那么獸醫站與王某等之間并非借貸關系,也就是獸醫站對于經濟實體的資產沒有任何義務,也不承擔任何資產損失的風險,經濟實體的資產當然地不屬于國有資產。雖然盈利曾經用于獸醫站開支以及王某請求實質代表公權的鄉黨委處理資產。其本身并不影響資產性質的認定。
其次,王某自身的行為不具備主觀違法性,或者是不具備貪污犯罪這一目的犯的主要特征。作為非法占有的犯罪都是屬于目的犯,而目的犯都必然具備主觀的違法性。“主觀的違法性在考察行為之違法性時,納入主觀視角,可以說是一種更為全面的違法性理論。構成要件是一種違法類型,因此在構成要件的內容上,也不僅僅包含客觀要素,同樣也存在主觀要素。最初所指的主觀要素就是指目的犯之目的等特定的主觀要素。后來才擴及故意與過失等一般的主觀要素。”貪污犯罪的主觀方面就是追求對于國有財物的非法占有。王某為了自己投資資產的安全,在鄉黨委2006年嚴重怠于行使自己職權的情況下(實際上,鄉黨委也不應當行使資產的處置權),2009年王某賣掉經濟實體資產所得24萬元,分得11萬。既然王某當初投資進去,其收回自己投資的行為完全屬于對于自己資產的一種處分行為,而且從數額上講也沒有超越自己當初的投資范圍。其從客觀方面沒有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所以主觀違法性與客觀違法性結合認識分析,其行為不具備刑事違法性。
最后,王某的行為不具備職務行為的基本特征。根據《刑法》第93條,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王某2006年6月辦理了退休手續,其本人也就不再具備刑法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雖然其本身實際上對于經濟實體本身存在一定的管理權限,但是由于經濟實體屬于其為主體投資興辦的,其管理權限屬于投資者的民事權利;而且即使是經濟實體本身的資產屬于完全的國有資產,在并沒有得到鄉黨委授權的情況下,其對于經濟實體的管理最多屬于民法意義上的無因管理,而無因管理并不是職務行為。認定王某涉嫌貪污犯罪,完全忽視王某已經退休三年以及沒有任何委托授權的事實,所以是對于貪污犯罪的職務行為擴大化解釋。
中國社會三十年來在發生巨大的變化,中國的法律也在接受巨大的變化。如果其有過錯的話,那就是由于國家的改革導致當初興辦經濟實體的時候。對于經濟實體的相關法律規定不是非常清晰,以至于在經濟實體的盈利處理等方面造成一定意義上認定經濟實體自身資產性質的困惑。我們不能寄希望于法律能夠完全規范改革實踐,那樣的話實際上也就不是改革了,特別是當初鼓勵興辦經濟實體的改革。所以給予實踐以一定的空間,或者說是刑事法律在改革地帶留下一定的空白,那是我們必須接受的。也正因為如此,當刑事法律遇上中國式改革實踐時。我們既要堅持罪刑法定原則,也要堅持刑罰的謙抑性原則,促使刑罰權行使主體以及行使過程的內斂。我們不應當因為王某等沒有正確地行使自己的民事法律權利,將盈利用于國有事業單位而動搖罪刑法定的根基。畢竟貪污犯罪的對象是國有資產,犯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
王某職務犯罪案件對于如何強化公權和私權的劃分,以及動用不同的法律手段處理不同的法律關系也同樣有著重要意義。按照民法專家梁慧星教授的觀點:“權利首先區分為公權和私權,以與公法與私法相對應。其區分標準分歧,通說為‘法律根據說’。即以權利所根據的法律為標準,根據公法所規定者為公權,根據私法規定者為私權。民法為私法,民法上的權利屬于私權。”當然。對于財產權等私權的保護,在刑法有明確規定時也會上升到動用刑法的方式進行保護。具體到本案,王某本身是投資主體,其因為投資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顯然屬于我國民法所規定的,所以其產生的權利屬于私權,而私權的糾紛首先是民法這一私法調整的范疇。如鄉政府與王某等因為財產關系的處理糾紛,應當由民事糾紛的當事人之間協商處理,或者是以民事訴訟的方式請求人民法院以民事審判的方式進行裁決。
也許有一天我們中國的法治也需要法律邏輯,更需要法律經驗。但是在這個社會改革和轉型的時代,作為刑事司法,更需要嚴格的法律邏輯和可靠的法律經驗。離開法律邏輯和法律經驗,進入法律誤區就不遠了。
注釋:
[1]陳興良、周光權:《刑法學的現代展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98頁。
[2]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