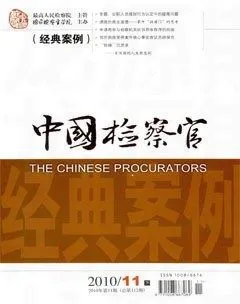幾種特殊情況下的自首認定
一句話導讀
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嫌疑人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的犯罪行為是否構成自首常常產生不同認識,本文針對這些情況,實例進行論證。
自首制度是我國刑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刑罰制度,是對犯罪分子犯罪行為的肯定,使罪犯內心產生變化,感到法律的公正,從而達到改造目的,還能有效地降低司法成本。正確認定自首對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準確適用刑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司法實踐中對是否構成自首常常產生不同認識。我們就近年來辦理的刑事案件遇到的涉及自首認定的若干疑難問題進行分析。
一、犯罪嫌疑人作案后為防止被害方報復而被迫報警,能否認定為自首
自動投案是自首的一個重要構成因素,犯罪嫌疑人必須具有投案意愿。犯罪人的投案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出于真心悔悟,有的是為了爭取寬大處理,有的是因為親屬勸說,還有的害怕遭到報復等等。而犯罪人犯罪后被抓獲或者被群眾扭送至司法部門而歸案的犯罪分子。因缺乏投案自動性,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而犯罪分子實施犯罪后,因害怕被害方的報復,無法脫逃而被迫報警,在迫于無奈的情況下投案,能否認定投案自首?
如崔某因瑣事從一工地撿一木板朝漆某腰部砸了一下。致漆某脾臟摘除,構成重傷。崔某打了漆某后,被漆某親朋好友堵在該工地一屋內,崔某害怕漆某等人報復的情況下,掏出手機拔打110報警。
我們認為,本案犯罪嫌疑人具備了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對于被迫向110報警的行為是否屬于投案。投案是行為人承認自己實施犯罪行為,自愿接受司法機關的審查。通常具有主動性,行為人一般有悔罪的意愿,自愿置于司法機關的控制之下。如果以是否悔罪來作為判斷嫌犯是否具有自動投案意圖的話,會大大縮小自首的范圍。背離我國刑法設置自首制度的初衷。不要將引起犯罪人投案的原因看成是犯罪人被迫的結果。不要因為出于爭取寬大處理或者生活所迫的動機而否認投案的自動性。本案中,崔某是因被害方人員圍堵而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報警的。但崔某打電話報警投案是基于其主動行為。這是事實。因此,從崔某實施故意傷害行為后報警、歸案、如實供述其罪行這一系列的行為來看,其行為應成立自首。
二、犯罪嫌疑人在醉酒昏迷狀態下被親友送到公安機關,蘇醒后如實供述。是否成立自首
司法實踐中,對于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動。而是經親友規勸、陪同投案的;公安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或者親友主動報案后,將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應當視為自動投案。可見,并非主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的,法律也認可其具有投案的自動性。但是,如果嫌犯在昏迷狀態下被親友送交司法機關、后如實供述的,能否認定為具有投案的自動性?
如王某強奸一案,王某酒后從窗戶爬到石某臥室內,用暴力將被害人石某衣服脫掉,企圖與其發生性行為,因王某酒精中毒而昏迷在被害人床上,被害人首先告訴王某的父親,王某的父親等人將王某送到派出所后蘇醒,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
根據我國刑法設立自首制度的宗旨和有關司法解釋規定精神,對“自動性”應當作廣義解釋,即對于那些并非主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帶有一定被迫性,均可認定為“自動性”投案,這樣有利于及時偵破案件、降低司法成本。同時,“自動性”只是認定自動投案的因素之一,在犯罪嫌疑人并非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歸案后。還要結合其歸案后的態度表現來認定是否成立自動投案。如果犯罪嫌疑人被親友送交投案或者被規勸投案后不愿被司法機關控制而反抗或逃走。同樣不能被認定為自動投案,因此即使對“基于犯罪嫌疑人本人的意志”做廣義理解,也不會背離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結合到本案,犯罪嫌疑人王某在未受到司法機關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以前,被其親屬送交公安機關,雖然處于昏迷狀態,但是其蘇醒過來后并沒有反抗或脫逃,而是自愿處于公安機關的控制下,其行為符合自動投案的條件,應視為自動投案,楊某歸案后亦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應認定為自首。
三、犯罪嫌疑人在被公安機關傳喚后采取強制措施之前,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是否構成自首
自首的自動投案通常犯罪分子犯罪后,犯罪事實未被司法機關發覺之前或者犯罪事實雖然已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以前,或者犯罪事實和犯罪分子均已被發覺,而司法機關尚未對犯罪分子進行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以前,主要看公安機關是否掌握犯罪人的事實。掌握指的是有一定的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有作案嫌疑,證據的證明力度不需要很強,也不要求證據之間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但是要求證據指向清晰,不能是僅憑猜測。往往公安機關發現有犯罪事實之后,所做的工作是排查,而不是鎖定。在這種排查中犯罪嫌疑人如果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應該認定為自首,若經排查后已鎖定了犯罪嫌疑人后如實供述,則另當別論。
如周某、韓桌放火一案,周某、韓桌預謀后攜帶汽油、斧頭等作案工具,將被害人韓某濤診所點燃后,逃離現場。公安機關在排查過程中,周某主動交待伙同韓某實施放火的犯罪事實。周某伙同韓某預謀后實施放火行為在公安機關并未掌握的情況下。只是因其家人與被害方以前有矛盾,公安機關對周某傳喚接受詢問時,僅僅是懷疑并沒有證據表明是周某所為,也就是說公安機關并未實際掌握周某的犯罪事實情況下,周某如實供述了自己伙同他人的犯罪事實,應當認定為自首。
如張某放火一案,張某當天中午因其小孩買東西不滿與被害人張乙發生爭執,當天下午,張某攜帶剪刀去被害人家找被害人。因被害人不在家而未找到,到晚上7點左右,張某翻墻進入張乙家院內,將自己隨身攜帶的氣體打火機打著火。用線拴住打火機保持打火機不滅的情況下,將打火機扔到張乙家的床上,致床上被子點燃后選離現場。案發后,公安機關在現場提取鞋印一對。偵查人員在偵查過程中,通過調查走訪,得知張某因其小孩買東西與被害人發生爭執,當天下午。張某攜帶剪刀去被害人家找被害人,因被害人不在家而未找到。村里人反映張某近兩天神情反常,時不時打聽案件偵破情況,另外,通過對現場鞋印進行比對。與張某鞋印基本吻合,偵查人員在排查中發現張某有作案時間、條件。遂后認為張某屬于重大嫌疑對象,決定對其傳喚,張某到案后,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本案中,張某是被公安機關作為犯罪嫌疑人進行傳喚。那就是說張某的犯罪事實已被公安機關發現,而且已經被公安機關確認為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已經通過現場勘驗、證人證言等掌握了張某犯罪的證據,張某不具有如實供述公安機關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實情節,所以其行為不能認定為自首。
四、前罪立案后犯罪嫌疑人被抓獲,但構不成犯罪,后主動交待與前罪同種罪行犯罪行為。是否構成自首
根據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于不同種罪行的,以自首論。構成特殊自首(準自首、余罪自首)。刑法理論界對刑法和司法解釋中關于準自首的規定尚有不同看法,認為余罪自首屬于坦白的范疇。但通說觀點主張,余罪自首具有自首的本質特征。刑法關于準自首規定,為司法實踐中對被采取強制措施后是否存在自首問題確定了一個認定標準,這使得已經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都獲得了自首的機會。該款規定最大限度地放寬了自首的對象、時間和條件,體現了我國刑法關于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
如2006年,郭某伙同他人盜竊一輛摩托車,價值8500元。銷贓時,同案犯當場被抓獲,供述出郭某(戶籍已滿十六周歲)的犯罪行為。當時郭某外遮。2010年因該盜竊被抓獲,經查,郭某當時實際年齡十五周歲。因戶籍登記有誤,依照刑法規定,不應追究其刑事責任。到案后,郭某又主動供述出伙同王某在某地盜竊一輛摩托車。價值7520元。
本案中,郭某被采取強制措施后,第一次盜竊行為因不滿十六周歲,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但后來,郭某又如實供述在滿十六周歲后某地盜竊一輛摩托車的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雖然郭某不是主動投案,但如實供述,有利于偵破積案,消除社會不安定因素。也有利于實現自首制度的社會保護功能。因此應當認定郭某的行為系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