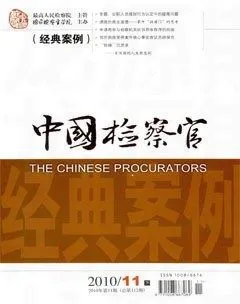再論盜竊罪的既遂標準
案名:那某·阿某曼盜竊案抗訴
[基本案情]2009年6月10日至7月3日,被告人那某·阿某曼先后3次實施盜竊,竊得現金200元及價值220元的手機一部。同年7月6日,被告人那某·阿某曼來到某某縣城團結路某某商店,見店內元人,遂從寫字臺抽屜里盜取3625元現金裝進自己的口袋,正欲逃走時,失主返回店內將被告人抓獲,從其口袋里搜出被盜現金后將其押送公安局。
本文以“再論”為題。是因為有關盜竊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分。早已經是學界研究得“通透”、“泛濫”的課題。現在本文重論這一話題,難免有“朝花夕拾”之感、“拾人牙慧”之憂。然而,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成熟的理論并非必然帶來正確的實踐。在抽象的理論與光怪陸離的個案之間,如果缺少了執法者的正確認知和經驗性判斷,仍將難以避免出現常識性錯誤裁判。本文以2010年某某縣人民檢察院成功抗訴的被告人那某·阿某曼盜竊案為例,探討如何正確區分盜竊罪的既遂與未遂。因此,對法律理論和司法實踐的經常性“回頭看”。有時并非重復勞動或者浪費性思考。
一、本案訴訟經過
本案經某某縣公安局偵查終結后,移送某某縣人民檢察院。縣人民檢察以盜竊罪提起公訴,縣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檢察機關認定被告人最后一次盜竊為既遂不合適,被告人雖然實施了盜竊行為,但因還沒有離開盜竊現場時被受害者發現并抓獲。被盜的錢財已退回受害者,應當認定為盜竊未遂。”因此,縣人民法院認定被告人犯有盜竊罪,并適用《刑法》第23條未遂條款,判處被告人拘役六個月,罰金1000元。收到判決書后,縣人民檢察院認為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遂向某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并獲市人民檢察院支持,經開庭審理,二審法院終審改判,認定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認定被告人的行為系盜竊既遂,同時維持一審量刑。
二、對學界觀點的回顧
劃分盜竊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理論上有接觸說、轉移說、藏匿說、控制(取得)說、失控說、“失控+控制”說、損失說等七種觀點。日本學者大琢仁認為,“所謂竊取,是侵害他人對財物的占有、把該財物轉移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為,因此,認為在取得了其占有的時點是既遂的取得說是正當的。所以,雖然僅僅接觸到財物尚不足以成立既遂,但是,既然行為人把財物轉移到了自己或者第三者的事實性支配內,就不需要進而將其拿到能夠自由處分的安全位置。”“必須針對各種情形,考慮屬于客體的財物本身的性質和狀態、被害人對財物的占有形態以及竊取行為的形式來判定。例如,把形狀小、能夠容易攜帶的財物裝在身上時,就立即達于既遂,對那些財物的容量相當大或者難以就那樣搬出的財物而言,應該認為制造出能夠搬出的狀態時才成為既遂。”…學者大谷實也贊同取得說,但其觀點稍有不同:“在既遂的判斷中,和實行的著手一樣。也必須考慮財物的性質、形狀,他人迄今為止對財物的占有狀況,以及竊取行為的形態,進行具體的判斷。如在住宅、店內竊取的場合,因為占有人對財物的支配力量很強,即便目的物很小,除了是很容易設定對該物的占有的場合以外,原則上必須將物搬出屋外才算是占有。與此相對,在支配力較弱的無人的住宅的場合。只要有搬出的準備。就是既遂。”學者張明楷的觀點則與日本學者大琢仁完全相同。王作富也主張“應以盜竊犯是否已獲得對被盜財物的實際控制為標準,盜竊犯已實際控制財物的為既遂,盜竊犯未實際控制財物的為未遂。”“這種實際控制并無時間長短的要求,也不要求行為人實際上已利用了該財物。”…綜上可以看出,在盜竊罪既遂標準問題上盡管說法多樣,但主流觀點基本一致,形成通說。
三、本案一審判決錯誤成因分析
通過上述觀點回顧,本案究竟應定既遂還是未遂實際上已經一目了然。但問題是,既然在盜竊罪既遂標準問題上學界已形成通說,那么本案一審判決為什么還會出現適用法律錯誤?本文認為根本原因在于一審裁判者完全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而沒有站在法律人的角度進行思維。完全依循普通人的常識而沒有運用法律人的經驗。作為一個普通人,很容易依據表象認為,被告人偷錢后未逃出商店就被抓獲是犯罪未得逞。那么,同樣是未出門就被抓獲,為什么被盜財物的形狀體積就能決定既遂與未遂之分?通說并未給出直接答案。本文認為關鍵涉及被害人對其占有財物控制力的強弱與被告人攜帶被盜物品逃離現場的成功率大小。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人對其財物的控制方式多種多樣,其中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手“拿持”。此外,還有一種常態化方式即用目力或者視線進行控制。比如,我們坐在候車室等車時,不可能始終將行李緊緊抓在手中,大多數時候是將行李就近放置,運用目力進行看管,脫離視線范圍就可能使控制力減弱甚至喪失。在本案中,被害人對其商店財物控制力的減弱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被告人行竊前。被害人在未鎖門的情況下離開商店。盡管時間短暫,但造成店內財物無人看管,為被告人行竊提供了絕佳機會;二是當被告人竊得現金,正欲逃離而被失主攔在店內時,被告人已經將現金裝在口袋里,控制力較強地取得了該筆現金,而該筆現金也已經通過藏匿脫離了被害人的視線看管范圍,使得被害人的控制力極度減弱,因此認定盜竊既遂是妥當的。如果被告人的盜竊對象是冰箱等大宗物件,在同樣情形下,一方面被害人一眼就能看到自己的財物,其控制力較強:另一方面在被害人攔截的情況下。被告人搬著冰箱逃離現場比起攜帶現金而言,要困難的多,成功率極低,因而認定為盜竊未遂是妥當的。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盡管有通說觀點可供參考,但執法者作為法律人的經驗性判斷仍必不可少。正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前任大法官卡多佐所言:“正是在色彩不相配時,正是在參看索引失敗時,正是在沒有決定性的先例時,嚴肅的法官工作才剛剛開始。”
四、對本案抗訴必要性的附帶性思考
在本案的審查抗訴期間。檢察機關內部最大的爭議是抗訴的必要性問題。很多人認為一審判決盡管定性存在錯誤。但量刑適當。故沒有必要抗訴。其依據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刑事抗訴工作的若干意見》第3條第2款之規定,即刑事判決或裁定認定罪名不當,但量刑基本適當的,一般不宜提出抗訴。對此規定。本文始終存有不同看法。所幸最高人民檢察院后來頒布的一些規范性文件中,對此已有修正。如最高人民檢察院[2005]9號《關于進一步加強公訴工作強化法律監督的意見》第3條第3款規定:“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或者適用法律錯誤,量刑雖然未致畸輕畸重,但社會影響惡劣的;因重要事實、法定情節認定錯誤而導致錯誤裁判,或者因判決、裁定認定犯罪性質錯誤,可能對司法實踐產生不良影響的,應當認為有抗訴必要,依法提出抗訴。”對照上述規定,本案一審判決出現的常識性錯誤。作為先行判例,顯然可能對司法實踐產生不良影響。本文認為,從定罪與量刑的關系看。定罪是根本與前提,量刑是附隨與結果,根本性的定罪問題都出了錯,即使結果適當,仍屬錯誤裁判,甚至其錯誤程度比前提正確而結果畸輕畸重還要大。也許很多人會認為對如此小案小錯進行抗訴是對訴訟資源的浪費。本文認為,小案未必不疑難,小錯未必不典型。動輒以節約訴訟資源為由放棄法律監督,實際上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
注釋:
[1][日]大琢仁著:《刑法概說(各論)》,馮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96頁。
[2][日]大谷實著:《刑法講義各論》,黎宏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195頁。
[3]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734頁。
[4]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1100頁。
[5][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過程的性質》,蘇力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版,第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