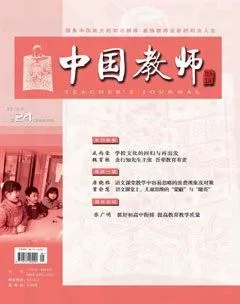學校文化的回歸與再出發
正如有人所說,盡管我們每天都生活在文化之中,但是傾我們自己所知,也未必能說出什么是文化。也許,這就是一種文化的魅力、文化的魔力。
學校文化的回歸與再出發,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什么叫“回歸”?什么叫“再出發”?古羅馬的馬可?奧勒留曾說,就算人可以活幾千年,哪怕能活數萬年,那又怎么樣呢?你始終應該記住,任何人失去的不是別的什么東西,而是他現在所過的生活。任何人所過的也不是別的什么生活,而是他時刻正在失去的東西。生命的起點和終點其實是時時刻刻合為一體的,失去的過往,也正是現在的時刻。人的生命,起點和終點總是時時刻刻合為一體。那么,文化呢?那么,學校文化的回歸與再出發是不是也應該合為一體呢?回歸是為了什么?回歸是為了再出發,回歸是一種抵達,但是在抵達以后它必須有新的出發。回歸本身也應該是一種再出發。因此,就在不斷的回歸與再出發的過程當中,就在回歸與再出發的結合之中,學校文化就這樣建設起來了。
那么,學校文化的回歸與再出發,究竟應該聚焦在哪里,回到哪里去,又該從哪里出發呢?問題很多,但其中一個重大的問題與梁文道先生寫的一本書《常識》有關。當今時代,社會在不斷發展,不斷向前,不斷制造出許多看似深刻的問題,許多貌似復雜的現象,那么學校文化的回歸與再出發到底要回到哪里去?要回到常識上去,正如梁文道先生所講的“常識”一樣,就是要回到問題最初的印象上去,回到問題的基本規定性上去,所以,學校文化的回歸與再出發,不能忘掉文化的基本規定性。文化的基本規定性正是文化需要回歸的地方,文化的基本規定性也正是學校文化建設再出發的地方。
《道德經》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這個東西不好下定義。最近,中國政法大學的一位張教授認為“道”的問題應該是一個“生命力”的問題。而且,他對“生命力”做了一個非常好的解釋。他說,“道”就是一種創造力,就是一種更新的能力,就是最初的內驅力、原動力。“道”具有最巨大的包容性。因此,就像張文質先生和江蘇省南通市二甲中學合作進行生命化教育一樣,我們不妨把生命化的教育回到文化的常識上面去,就是關于文化的生命力的問題,尋找學校的文化,尋找學校文化建設的一個道德問題。
文化的實質是什么?文化的實質應該是“人化”。討論文化的問題,討論學校文化建設的問題,不能不談到“人”。文化建設,沒有人,則免談。所以,文化是“人化”,討論文化,需要與人、人的價值,人的發展緊密聯系。文化是“人化”,說的是要用“文”來“化”人。文化可以影響人,文化可以改變人,文化可以塑造人。所以,討論學校文化的回歸與再出發,必定要研究文化如何影響人。人是文化的享受者、體驗者,更是文化的創造者。二甲中學這些文化建設,它的最高境界在哪里?應該是二甲中學在校長的領導下,教師們、同學們、家長們一起去創造最好的文化。當然,文化可以傳承,文化也應該發展,文化的發展就是創造出最適合學校發展的文化。同時,學校文化的回歸與再出發,就是讓學校成為精神家園,成為學校教師和同學們的一塊文化憩息地。這塊文化的憩息地安全嗎?這塊文化的憩息地營養豐富嗎?學校的這塊文化憩息地有根有源嗎?它的根須究竟伸向哪里?就像劉鐵芳先生所講,不要追求那些華麗的、五彩斑斕的、詩意的學校文化建設。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對荷爾德林的“讓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句詩進行了最好的解釋,“人是要抽離大地的”。人抽離大地,透過艱辛,仰望神明,來到半空之中,俯視大地,俯察人間,這時,你就具有了創造的激情,或者說是創造的靈感。但是海德格爾也說,“最終人是要回到大地上去的”。因此,“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所描繪的是一個創造的過程,一個永遠不離開大地,但是又超越大地的過程。如果學校文化的建設,忽略了人創造文化,體驗文化的特性,離開了文化是學校的精神園地,那這個學校的文化回歸與再出發,就沒有意義。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審視一下二甲中學的文化建設,我認為二甲中學已經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主張”,積蓄了一定的“文化能量”,初步構建了學校的“文化體系”,形成了學校的“文化坐標”。用時尚的話來說,就是已經開始初步繪就二甲中學的“文化地圖”。譬如,二甲中學的文化主張就是“文化發展學校,對話創造思維”,努力實現“人文關懷,文化立校,潤澤生命,啟迪智慧”。同時,他們對學校的文化進行了梳理、甄別,而且有傳承、有發展,確定了學校的校訓“行于天地,止于至善”。二甲中學的這個校訓,就是讓我們知道二甲中學的一個個人、一個個教師和學生都有最好的道德追求,而“至善”又是一切追求的出發點和回歸點。二甲中學又形成了自己的辦學追求。這個辦學追求非常有個性,就是“今天第二”。凌宗偉先生和張文質先生,包括許錫良先生,都對“今天第二”做了非常好的解釋:“今天第二”是對今天的肯定,但是,又是對明天的一種更加積極的、更加樂觀的期待。“今天第二”就是要讓二甲人做最好的自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二甲中學正是因為有“今天第二”的辦學的追求,有二甲的精神,所以二甲中學才不斷前進。
“教育是一種提醒”。許錫良先生對“教育是一種提醒”做了比較好的解釋,“教育是一種提醒”是因為每一個人生命的內在規律,存在一種生命的密碼,隱藏著生命中無限巨大的可能。這種可能性的開發,潛能的開發,不是靠訓練得到的,而是通過“提醒”。學校的文化建設,其起點與終點都應該是學生,時刻關注學生的發展。另外,二甲中學創造的學校文化,具有本土特點。只有適合的,才是最好的。學校文化的回歸與再出發,就是要為學校尋找最適合的文化。英國哲學家奧菲說:“當鞋子和腳合腳的時候,就把腳忘掉了。”這就是說,這種教育、這種文化是最自然的,最貼近學生的,它沒有教育的痕跡,它不是刻意的,它是一個非常真實的、自然的,陽光雨露下的滲透行為。中國古訓還說,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腳最知道。二甲中學創造的這個文化好不好,要由二甲人自己說了算。
人可以創造文化,人的最偉大之處就在于人的可能性。文化建設,文化建設的回歸與再出發,它的目的就是要去激發人的這種可能性,把教師的和學生的可能性變成一種現實性。二甲中學的曹樂旻教師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道:“今天,我終于站在這年輕的戰場上,請你給我一束愛的光芒。今天,我想要走向這勝利的遠方,我要把這世界為你點亮。”這個年輕的戰場充滿了文化,充滿了生命,充滿了巨大的創造力。人的可能性正在變成一種現實性。而且這種可能性往往就隱藏在現實性中。
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文化的核心就是價值觀。文化建設就是在核心價值觀的形成和形變上下更大功夫。但是,什么叫價值?對此有著各種各樣的解讀。其中,我們可以把價值和意義聯系在一起,把價值和創造聯系在一起。歌德說,你擁有價值嗎?如果你要擁有價值,那么你就去創造吧。因此,價值也是來自于創造。著名教授魯潔也解釋了價值:“價值就是理想中的事實。”價值存活于事實之中,就在我們的現實當中,就在我們的行動當中,就在我們的教育行為、管理行為當中。然而,價值并不等同于事實,它超越了事實。追求理想,就要從事實出發,在事實當中,發現理想,追求理想。一個地理學家寫的小說《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里說“我們要去追求一條地平線,要永遠去瞭望這條地平線”,“我們向地平線邁進兩步的時候,地平線總是向后倒退兩步,接著我們再向地平線邁進十步,但是你又會發現,地平線向后倒退了十步。于是地平線似乎是永遠夠不著的,地平線似乎是永遠到達不了的。但是,有追求的人,總覺得地平線存在,他總是要去追尋這條地平線,因為他們知道地平線存在的最高價值就在于:讓人不斷地向前、向前、再向前”。也正像左宗棠所說“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一樣,人總是要想著向高的地方站立,站得高,才看得遠。但是,你又不能虛空,你要想著一塊平地,就平地而坐,才感踏實。而就平地坐,你又不能畫地為牢,要向寬處行。
目前,價值觀、核心價值觀的建設顯得尤為緊迫。多元文化帶來了多元的價值,容易使人產生一種迷惑感,甚至會迷失方向。美國人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一種“價值澄清理論”。這種理論的提出,首先是一種進步,它的進步就表現在:把所有的價值,都呈現給學生。它是開放的,讓學生去探究,去體驗。但是,美國人后來進行了反思并對這個理論作了調整和改進,認為教師的價值引導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如何發揮教師的價值引領作用顯得尤為重要。
二甲中學的文化建設,在這方面對我們仍有啟發。
第一,二甲中學在進行文化建設時,把價值觀聚焦在如何對待利益的問題上,尤其是如何對待眼前的利益上。這種定位,無疑是非常可取的。
第二,價值觀涉及到教師的發展問題。張文質先生曾談到這樣一個例子,有一位教師,他考取了公務員,好多人問凌校長,你放不放他走?凌校長回答說:“我放。我們走掉一個陳老師,我們還擁有李老師、張老師、陸老師……我們還有同樣非常優秀的老師。”尊重教師的自由,就要解放教師。要在解放教師、讓教師獲得自由的狀態下,去更多地創造,更好地創造,生活質量更好一點。這種對教師發展的管理,也是可以借鑒的。
第三,學生價值觀的取向。“學生要散養,不能夠圈養”。李勇老師認為,“不要打著喂著吃,不要抱著喂著吃,不要急于去催肥,把學生真正當做一個生命來對待,要回歸生命,回歸教育的本質”。一位教師的文章中曾這樣描述:“在寒假以后,有一個學生在非常個性化的簽名中,寫下了這么一句話,90后不是壞,只是墮落。”該教師回復到:“90后是善良的,只是習慣享受;他們也想好好學習,只是恒心不夠。因此,在教育過程中,教師要更多的作為一個引路人。”
文化的回歸與再出發,必須關注一個重要的陣地,那就是眾所周知的課程和課堂。二甲中學的生命化建設,二甲中學的文化意象,如果不是建立在課程上,如果不是在課堂教學改革的基礎上,是根本觸發不了的,也是走不遠的。課程、課堂同樣離不開文化。亞斯?蓋斯說:“教育原則是通過現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導向人的靈魂覺醒之本源和根基,而不是導向由原初派生出來的東西和平庸的認識。”課程應該也是一種文化。課程、課堂教學,它的原則就是用文化的力量,導向人的靈魂,找到人發展的根本和人發展的一種根據。這個根據和本源絕不是平庸的知識。而且,文化為知識的學習提供了底蘊,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文化是學習知識的動力。艾克茄?洛夫說:“文化滲透到各種知識中,塑造各種知識,有時也管理各種知識”。所以,我們應該把課程、課堂教學,當成文化對待。但是在什么條件下,課程才是一種文化?在什么條件下,課程、課堂教學才應該是一種文化?比如說,在“應試教育”下,課程、課堂已經不是文化,它已經被異化。要使課程、課堂成為一種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課程展開的方式。課程展開的方式,愛德華?霍講得非常好,他說:“文化像一座監獄,除了你一個人知道有一把鑰匙可以打開它”。文化是一座監獄,很神秘,你不能了解它,但如果這時候,我們手上有一把鑰匙,就能打開這個監獄。因此,你就發現了文化,你就了解了文化。“的確,文化以很多不為人知的方式把人們聯結在一起”。文化是有方式的,而且文化的這種方式常常是不為人知的。我們并不知道這個方式,但其實這種方式應該類似于約瑟夫?奈所講的“軟實力”,它的方式是謙卑的,是吸引人的,所以,要使課堂、教學、課程變成文化,教師必須謙卑,教師在課堂上使用的方式,也應該是吸引人的。當然,這種吸引人的方式,往往是一種學生自主學習的、探究的、體驗的、對話的方式。
(作者單位: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所)
(責任編輯:趙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