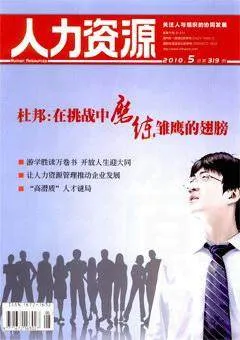復制未來企業家
“富二代”粉墨登場
不久前,《福布斯》發布的2010年十位最年輕億萬富翁的排行榜可謂引人深思。與排在首位25歲的“現代版比爾·蓋茨”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不同,在上榜的中國年輕富豪中,無論是碧桂園的楊惠妍,還是山西海鑫的李兆會,均非白手起家的創業天才,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坐擁過億身家的“富二代”。
然而,這個令人羨慕不已的“富二代”群體卻也一直飽受爭議和質疑。杭州鬧市飆車撞人的胡斌還未走出風口浪尖,在相親節目中炫耀存款和跑車的劉云超旋即又成為輿論炮轟的焦點。“富二代”似乎總是跟迷失、炫富、享樂等詞匯聯系在一起,而“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和“富不過三代”的古語仿佛魔咒般緊緊箍在即將老去的第一代創業者心頭。
無論有多爭議,“富二代”這一人群正在諸多復雜的目光中粉墨登場,在此眾多家族企業處于兩代人財富、權力交接的脆弱關口,他們的傳承路徑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
家族企業也有生命力
美國布魯克林家族企業學院研究表明,約有70%的家族企業未能傳到下一代,88%未能傳到第三代。只有3%在第四代及以后還在經營。麥肯錫的研究結果也證實,所有家族企業中僅有15%的企業能延續三代以上。
據全球最大投行之一的美林集團統計,我國內地僅千萬富翁就已接近24萬,在所有民營企業中家族企業占據了八成。隨著第一代創業者逐漸退居二線,“富二代”正在或將要挑起守成家業的重擔,家族企業也將逐漸進入財富和權力的交接過程,而傳承與轉型正是家族企業成長進程中最脆弱的關口。
從表面上看,那些手握巨資的“富二代”儼然是十足的成功者,然而光環之下不應忽略的是,在享受那些并非由他們親手創造的財富之時,他們很容易迷失自我。財富在帶來榮耀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壓力。是在財富中坐享其成,還是將壓力轉為動力,成為“富二代”能否走向成功的分野。此外財富和權力交接的過程中,家族企業的“先天不足”也逐漸凸顯,制度建設不完善、產權經營之間難厘清、裙帶關系難處理等弊病,最終使“富不過三代”的魔咒頻頻奏效。
或許這只是因為我們沒有找到更好的解決之道。慧聰網CEO郭凡生就首先為家族企業正名,稱其并非落后的代名詞。沃爾瑪、豐田等也都是家族企業。任人唯親、弊端叢生等負面現象即便在非家族企業中也同樣存在。相反,家族企業的資本盈利率、資本推動率和資本就業率都是國有企業的十多倍、國外資本同期的數十倍。“跟非家族企業相比,家族企業中存在的血緣關系,能有效解決管理層的約束和激勵問題,降低監督難度和交易成本。天然的家族文化還能增強企業的凝聚力。”郭凡生給出一個驚人的數字:中國民營企業中絕大多數是家族企業。晉商中時間最長的家族企業傳了二十多代七八百年,同樣還有著很強的生命力。
未來企業家能否批量生產
如今,“富二代素質”的話題越來越頻繁地出現于各大媒體和互聯網上。繼江蘇建議由政府出資培訓“富二代”引發輿論質疑不久,順德企業家也隨之響應,溫州人事局舉辦的“民企二代”研修班學費由政府補貼三分之二。山西甚至專門舉辦了“富二代”晉商守成與發展論壇,因為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山西的“富二代”產業大多集中于能源領域,他們的教育問題不僅關乎家產的接力,還關乎整個社會財富的傳承。
如果說“富一代”存在炫富的A面和內斂的B面,那么“富二代”顯然充滿了更多另類的多面性:他們可能紙醉金迷,好高騖遠,也可能特立獨行,桀驁不馴;他們可能躺在父輩的輝煌和金錢堆里高枕無憂,也可能發憤圖強,壯大家族企業,或者獨成大事。不過在長江商學院戰略學教授滕斌圣看來,“富二代”總體歷練機會有限,工作領域狹窄,管理經驗不足,很少人擁有在跨國公司工作的經歷和管理經驗。
而看看眼下的各類培訓班,雖然名頭各異,但實際上內容卻基本相似,除了聯手歐美名校講授頂級管理課程外,還會培養馬球和高爾夫等富人運動。在專家們看來,一個企業家的成長和成材在于個人的努力和修行,在于他經歷的歷練與磨難及從中得到的領悟。“富二代”領導力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更需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除了一般意義上的領導力和執行力之外,北京和君創業管理咨詢集團合伙人胡奎提出,對“富二代”的培訓并不限于此,還有關于幸福、關于心靈、關于生命本身的教育。“富二代”表現出來的眾多問題。歸根結底是內心的不和諧.是自我價值感的缺失。“看得見的身體就像是個房子。而看不見的心靈才是房子的主人”。關注人格教育,給他們以內心的自在、自由、自主,以此來化解他們對長期壓力的不滿與抗拒,接受自己的價值,進而創造更大的價值,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境界。
從“打工者”到“企業家”
除了家族企業繼承人這些純正的“富二代”,各大公司及企業中,還有一批一進公司便分享著第一代創業者帶來的豐碩果實、拿著高薪享受優厚的福利、過著輕松無憂生活的“準富二代”。雖然這樣的稱呼略有泛化,但他們沒有經歷過打天下的風餐露宿,卻坐享著江山無限的大好風光,也是不爭的事實。
凌雁管理咨詢首席咨詢師林岳認為,“準富二代”缺乏創業精神的問題在很多創業型企業發展五到十年之后尤為突出,這是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瓶頸。然而如何實現“準富二代”從“打工者”到“企業家”的轉型呢?
首先,培養與第一代創業者一致的價值觀。讓“準富二代”了解企業最初創業時候的艱辛及歷史,從價值觀上與第一代達成一致,形成共同的價值觀。
第二,營造良好的團隊協作文化。團隊協作的培養可以通過對“準富二代”的培訓實現,也可以通過休息日的戶外拓展或其他團隊活動進行,以此達到消除“代溝”的目的。先從下班后能玩在一起人手,再達到上班時能有效協作的效果。
最后,上下級之間保持及時有效的溝通。溝通是企業管理中極其重要也極易被忽視的環節。上下級之間、同事之間不溝通,或者溝通得少,都很容易造成人才流失和人才錯位。只有有效的溝通,才能充分利用人才,使每個人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發揮最大的價值。
“富二代”與前朝元老
父輩的財富是祝福,也是負擔。“富二代”從出生那一刻起,就被安排好了今后的每一步。他們看似飛揚跋扈,其實是活在父輩的庇護或陰影之下,內心渴望被認可。他們渴望自由,卻常常妥協于對家族的責任和義務。目前,國內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家仍然對家族之外的人缺乏信任,更希望自己的子女繼承衣缽、延續香火。
一般來說,“富二代”接班后要經過五個階段的考驗,即學習期、成長期、交接期、成熟期和完全執政期。在父輩完全執政時,“富二代”還在學習,在企業中有一定職位,但執政程度很低。等到父輩逐漸放權,“富二代”的執政程度在迅速上升,不過這個時候他們對決策只起著影響而非決定作用。在父輩移交權力后,“富二代”步入執政成熟期,此時,父輩們一般退居二線出謀劃策,只有少數仍在幕后指揮。而成熟期過后的“富二代”才能進入完全執政期。還沒真正掌權時,“富二代”千萬不要破壞原有的企業文化,更不要和前朝元老發生沖突。
對于前朝元老的去留問題,“富二代”往往在妥協中做出了自己的選擇。碧桂園2007年在港上市時,財富開始從第一代創始人楊國強向第二代楊惠妍轉移。時年26歲的楊惠妍得到了父親59.5%的股權轉讓,一度成為中國首富。事實上,有內部人士透露,早在七年前楊國強去美國治病時,管理團隊就由楊惠妍全面接管。當時只有22歲的楊惠妍帶來了全新的美國管理團隊,在很大程度上接替了楊國強時代的原有創業團隊。
在2008年的胡潤百富排名榜上,山西海鑫董事長李兆會以1.25億元的財富成為山西最年輕的首富。而在2002年,其父李海倉首次上榜時,資產僅為16.14億元。在其父因意外身故后,年僅23歲的李兆會不得不結束在澳大利亞的學業回國接班。有10余位李海倉的老臣操持著海鑫的日常運作,打算對李兆會“扶上馬,送一程”。但在李兆會決定拋出巨資進入資本市場,成為民生銀行大股東之后,他才開始真正掌握起了海鑫的實權。
方太集團的茅忠群在26歲時和父親茅理翔一起創立了方太品牌,在久經沙場的父親“帶三年,幫三年,看三年”的扶持下,最終將方太經營得卓有生氣。他上任之初便提出了不用父親原班人馬的要求,重新搭建自己的管理團隊。除董事長、總經理仍由茅氏父子擔任外,方太其余中高層管理者都是外聘人員。由此,茅忠群也在對方太進行一系列變革的同時,最終確立了自己的領導地位。
“富二代”從小耳濡目染,對商業的敏感度比同齡人略勝一籌,也有自己的本領和創造財富的能力。走近并了解“富二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研究未來中國的經濟走向。如果“富二代”能夠像前輩那樣吃苦耐勞,富有創業精神,再加上大智大慧的現代企業的經營理念,將是中國民營經濟的一大突破,也是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發展的一種希